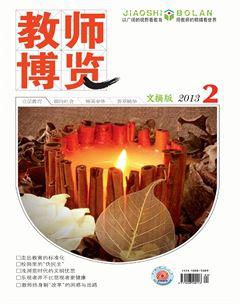走出教育的標準化
鄭也夫
反省教育的標準化
現代學校教育的一大特征是標準化,或許是受工業化中標準化的影響,或許是大規模、可持續運作一件事物的內在邏輯使然,筆者說不好,反正說標準化是其特征應該無誤。標準化不僅體現于考試,還有教材、年級。現代教育中,學校一家獨大,其他教育形式高度式微,學校之外的教育機構多是學校教育的附庸,于是教育的標準化覆蓋了全社會,嚴重抑制了多樣性。
我們先討論年級。嚴格的年級制抑制個性才能的發育:接受快的受約束,其抑制和耽擱是顯然的;慢的受挫折——其中或許有大器晚成者,但長期遭催促、受挫折恐難成大器。就是說,進度一刀切不好。參加工作的時間也不該一刀切,工作中未必不包含學習。我們且舉兩個人的例子來看看。
顧準,1915年生人。5歲入私塾,7歲轉入小學讀了三年(加上私塾共計5年),10歲考入中華職業學校初中商科(二年制)。12歲未參加畢業考試就進入潘序倫的會計事務所做實習生,很快學會了中英文打字。13歲加入該事務所辦的會計夜校,讀了半年的簿記,主要做文書工作。15歲承擔了五口之家的全部生活負擔。16歲是因夜校學生太多,潘要他任教,因學生嫌他年輕只好找他人替代,但第二年(17歲)再次上任并站住腳。業余自編講義,為此閱讀銀行學、會計學、銀行實務和經濟學,讀過馬凌甫的《國民經濟學原理》,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自言“英文勉強能讀會計書,又初步學了日文”。1934年(19歲)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編寫的《銀行會計》。顧準說:“1932年(17歲)以后……我已經跨過了我的啟蒙時期了。”
我和周孝正兄曾同老友丁學良聊天。周問丁小學讀書情況,丁說不記得讀過幾年,當時幾個年級的同學同在一個大教室里,老師一會兒給這個年級的同學講講,一會給那個年級的講講,“小丁”稀里糊涂地就都明白了,被送進中學,日后由工科轉文科,最后拿到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
二人的經歷當然都是當時的條件所迫,但是如果正規起來,按部就班,顧準還是后來的顧準嗎?丁學良還是日后的丁學良嗎?都頗成疑問。正規的教育最適合的是中庸者,捷足者和晚成者的發育軌跡都將被迫改變,不能充分展開他們的潛力。而能力低于中等水平者一定會受挫。大面積的少年受挫,后果難料,但大多不會是福音。蓋托說:
你們也一定知道,我們的計算機產業是建立在一批輟學者的遠見卓識之上的……我們所有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都是輟學者。
這些輟學者成功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有一點或許是共同的,他們需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自己的興趣上。蓋托還說:
破壞連續的時間是大規模教育的一個重要武器……沒有連續的時間,你無法總結整理扔過來的知識碎片。
每天的時間被分割成不同的課程,對很多人未必不合適。問題在于人是不同的,讓所有的孩子就范于時間分割化的程序中,大約會扼殺一些天才少年的創造力。
再談教材的標準化
在我心目中,汪曾祺的文筆絕對在為數不多的國手之列。他幼時受教的路徑如何呢?他有部小說《徙》,他說過小說主人公高先生就是他的啟蒙老師。小說中這樣寫道:
他要求在部定課本之外,自選教材。他說教的是書,教書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讀,真懂,我所喜愛的文章,我自己為之感動過的,我才講得好。”他強調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統性,要有重點。他也講《苛政猛于虎》《晏子使楚》《項羽本紀》《出師表》《陳情表》,韓、柳、歐、蘇。集中講的是白居易、歸有光、鄭板橋。最后一學期講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磨坊文札》。他好像特別喜歡歸有光的文章,一個學期內把《先妣事略》《項脊軒志》《寒花葬志》都講了。他要把課堂講授和課外閱讀結合起來。課上講了《賣炭翁》《新豐折臂翁》,同時把白居易的新樂府全部印發給學生。講了一篇《濰縣署中寄弟墨》,把鄭板橋的幾封主要的家書、道情和一些題畫的詩也都印發下去。學生看了,很有興趣。這種做法,在當時的初中國文教員中極為少見。他選的文章看來有一個標準: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這些文章有一個貫串性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人道主義。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個教師一個樣。物質食糧于身體如是,文化營養于精神何異?
鼓勵多樣的學習方式
學校壟斷了教育的最大弊病是滅絕了教育方式的多樣性,中國現行的教育模式是從西方過來的,因此中西都存在這一問題。西方的學校的大系統之中還存在著多樣性,而中國學校之間則差異甚小。因此可以說,在教育方式與風格的單一性上,中國首屈一指。
學校壟斷教育的問題是顯然的,但改革的思路卻大相徑庭。毛澤東推行不破不立,他破得痛快,最終一無所獲,只好任由后人復辟和回歸。教育改革的思路應該是不立不破。如果我們建立不起有生命力的教育方式,何必急于打碎舊的制度呢?如果我們建立起這樣的方式,破舊還是需要操心的事情嗎?立的思路不是實驗,實驗有自上而下的計劃的味道。它是自下而上的真實的教育活動。如果我們的社會寬容了這樣的教育活動,就將慢慢形成了一個非單一的生態。讓多樣的教育形式在共生中對比,由受教者用腳來投票。別樣的教育方式可以是現行方式的小的改變,也可以是全新的異類。
南方科技大學企圖開創一種新的教育方式,最近聽說有進展了,我不知算不算好消息。我的看法是,他可以選擇一條更為決絕的、特立獨行的道路:索性不加入教育部的招生系統,完全是自主招生。發授不被教育部承認,因而暫時接受范圍極其狹窄的文憑。自己努力培養人才,爭取早日讓用人單位青睞他們的學歷。首要的難題是招生,有沒有學生和家長愿意和他們一道去承擔風險。應屆的高三學生中總分不理想,但真實潛力優秀的分子一定不乏其人。重要的是如何打撈他們,說服他們走上風險之旅。初創期必是投入產出不成比例,因此道路一定坎坷。在現行系統外,肯定要比系統內,更有望成就異類。中國的教育需要異類。
當代私塾與讀經的小學校的新聞,幾年來不絕于耳。讀經的爭論也曾熱鬧過。我對讀經的方式不置可否,但我愿意看到這類教育機構的成長發育,因為我們沒什么可丟的。我們現行的教育系統是令人絕望的。即使從功利的角度看,一個孩子加入到無數人參與的競爭中,將自己打造得和別人一樣,有什么前途?還不如學點同齡人中稀缺的東西。日后他自然還要到社會中補充生活的必要技能,說不定早期的經文和后來入世的知識會發生某種融合。
自西學進入中國后,中國的學校就有男校、女校、混校三種形式。文革后期終結了男校、女校的歷史,以后統統是男女混校。近年來又有呼聲成立女校。我贊同這一主張,也贊同恢復一些男校。我不是贊同一統的性別分校,而是希望看到三種學校共存:男校、女校、混校。人的性格天生就是不一樣的,這是一筆重要的社會資源。如果大家的性格開始趨同,這意味著某種資源的枯竭。好的教育應該寬容而不是抑制各種性格。每一種性格都不意味著優點或缺點,而是特點。不同的人在社會上有不同的用場。龔自珍說: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國的教育拘于一格,晚清如此,民國好了很多,今天在這個維度上連晚清都不如。教育要從多方面“破除一格”。三種學校并存,是維度之一。
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村莊學校中的學生數量銳減,同齡人數常常很少。以往的辦校方式受到挑戰。面對這種新局面,教育部出臺了“撤點”“中心校”的政策,即撤消了一些村莊中的學校,將學生統統轉移到鎮里的中心校去讀書。于是出現了交通問題,交通費基本是家庭自己買單。孩子太小,家長常常不放心,有些母親便放棄了原來的工作,到鎮里租房陪孩子讀書。對“中心校”的政策我不敢茍同,不僅因為這違背了義務教育的宗旨(這宗旨是不允許增加家庭受教育的成本的),破壞了很多村民原有的生活方式,還因為它在提升教學質量的大旗下,強化單一的教育方式。人民的居住、生活的方式從來是不一樣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個職能部門,不能為了提高自己工作上的某一指標,就改變公民的生產方式。孩子不能離開父母,如此安排恰恰是最不懂得教育為何物。超小型學校沒什么不行,沒什么不好,師資的困難可以靠輪轉來解決。超小型學校是一種風格,此中成長的人別有一種性格。我們不是為了追求多一種性格而為之辯護,是反對人為地、強行地改變公民的生存方式,教育方式是附著在生存方式之上的。
我們總是將初中以下的輟學行為污名化。西方社會強制實行義務教育,不學習是犯法的。我覺得強制義務教育是雙刃劍,其積極面是促使政府保證各地教育條件的落實,其負面是強化了學校對教育的壟斷,催化了現代社會的單一化。理想的狀態是,保證教育條件的提供,愿意的人在初中以下的學校讀書沒有任何顧慮,但是不愿意的人可以不參加,在社會上他們同樣可以增長才干。我不信一個不愿意在學校讀書的人,能夠在那里學到好多東西。我愿意將必學的時限從初中畢業提前到小學畢業。
我們社會中虛假的東西太多,不可能不捆綁學習。只有當大家開始真實的學習后,人方有才干性情,社會才非泡沫虛構。
(采桑子摘自《上海采風月刊》2012年第9期)
責編:向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