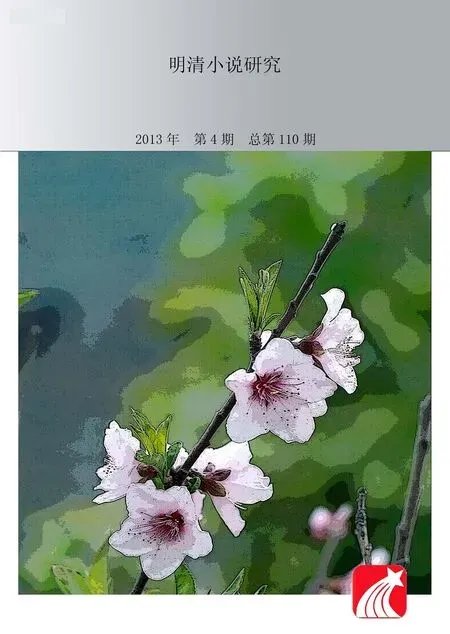重讀《鸞坡居士紅樓夢詞》
· ·
熱愛《紅樓夢》的讀者之所以知道清朝有個叫潘炤的人,差不多都是基于《鸞坡居士紅樓夢詞》,而研究者重視它,卻并非因為這些題詠的藝術(shù)性多么突出,而是因為潘氏《釣渭間雜膾》中附有一些序、跋,以為它們可以提供解決“《后紅樓夢》作者”問題的線索。然而,他們的重視并未真正到位,以至于語焉不詳。關(guān)注紅樓題詠的研究者每每論及《鸞坡居士紅樓夢詞》,多是未及目驗就遽下定評,甚至多不知道那些詩是題仲振奎《紅樓夢傳奇》的;提到潘炤其人,更是少有人肯花時間研究這個紅學(xué)里的普通人,基本以“生平無考”一筆帶過,清末的吳克岐于此著墨最多,也還是概而未詳。實際上,在潘炤《烏闌誓傳奇》的序跋及題詞中,關(guān)涉他行跡性情的描述已有不少,加上《釣渭間雜膾》所附序跋題詞,潘炤的身影雖非呼之欲出,感覺亦頗堪勾畫——雖不是完整的生平、行跡,但其一生的性情與精神、格局與風(fēng)范、交際與才情,大略可見矣。從《烏闌誓》為補恨之作也可見出,它與仲振奎《紅樓夢傳奇》有著共同的“大團圓”取向。本文試圖通過為潘氏《烏闌誓》撰序題詞的人群來了解潘炤,并及他朋友圈里的讀紅現(xiàn)象;通過解讀其《鸞坡居士紅樓夢詞》,了解部分紅樓戲的改編特色,并及仲振奎《紅樓夢傳奇》與《后紅樓夢》的關(guān)系。
一、關(guān)于《鸞坡居士紅樓夢詞》
一粟《紅樓夢卷》選錄了潘炤《鸞坡居士紅樓夢詞》中的十八首,即:原情、前夢、聚美、合鎖、私計、葬花、釋怨、禪戲、扇笑、聽雨、補裘、試情、花壽、誄花、失玉、焚帕、鵑啼、哭園。讀者一般將之籠統(tǒng)地稱為詠紅詩。在論及詠紅詩時,著名紅學(xué)家林冠夫認為此《紅樓夢詞》“是對小說情節(jié)的吟詠。凡《紅樓夢》的主要情節(jié),幾乎都有詩作吟詠之”;且進一步評曰“其中有的詩作,詩人還把自己也擺進去,但并不高明”,并例舉《葬花》、《誄花》以為證。其實,《鸞坡居士紅樓夢詞》并非直接題詠小說《紅樓夢》,而是為仲振奎《紅樓夢傳奇》而作的。所題共三十二首,一粟在匯編《紅樓夢卷》時將其中基本貼近小說情節(jié)的擷取錄入,而舍棄了他們認為離小說情節(jié)頗遠的詩作,棄而不取的十四首是:后夢、逃禪、拯玉、還魂、煮雪、贈金、寄淚、坐月、見兄、花悔、剖情、仙合、玉圓、勘夢。這十四首,只需看詩題,即知絕非對小說情節(jié)的吟詠,況且潘氏自序也已說得非常清楚。之所以錯認它是題小說《紅樓夢》的,究其因,一般人當是因了《紅樓夢詞》這個題目而望文生義,而多數(shù)研究者大約是只粗看了一粟選錄的那十八首之故吧(若細看,即便忽略第一首“原情”中的“金魚煉去不容光”句,從第二首“前夢”后兩句“見說游仙須補恨,烏絲紅豆且偷窺”亦可知題詩非記曹著情節(jié))。如果能像吳克岐那樣目驗全部,是絕對不會出現(xiàn)此類只可能在耳食的情況下才會出現(xiàn)的錯誤的。
民初吳克岐《懺玉樓叢書提要》記潘炤《紅樓夢詞》時這樣寫道:
潘,號鸞坡,清嘉慶間官給事中,工吟詠,解音律,好游,足跡遍天下。名公巨儒悉推重之,錢塘袁隨園稱為多才子。著有《釣渭間雜膾》、《烏闌誓傳奇》。行市是卷,乃題仲云澗《紅樓夢傳奇》之作。原題《鸞坡居士紅樓夢詞》,疑落一“題”字,茲特改題今名(云按:吳氏題為《紅樓夢傳奇題詞》)。
此處所謂《釣渭間雜膾》,是指潘炤詩、賦、曲等的合集,今天還可見到甲戌年即嘉慶十九年(1814)小百尺樓藏版的《雜膾羹》(即《釣渭間雜膾》),中收有《海喇行》、《涑水鈔》、《從心錄》、《小滄桑》、《西泠舊事百詠》,合集卷首有秦基《釣渭間合序》及淡士濤、龍汝言兩人的題詞。《從心錄》卷中有《鸞坡居士紅樓夢詞》三十二首、《溫柔鄉(xiāng)詞十八章》、《曲兒頭詩》四十首。如此三部分,看起來較為駁雜,之所以被合成一卷,應(yīng)是因了它們的格調(diào)一致故。它們均具宮調(diào)色彩,多擬代體,言辭溫婉。《從心錄》卷前有廉塘居士、吳鼒、吳云、張問陶等人的題詞。《西泠舊事百詠》前有潘世恩、吳云、葉新豐等的題詞,后有吳鼒跋文和潘炤自志。
《從心錄》卷首,廉塘居士、吳鼒和張問陶的題詞都沒有關(guān)乎《紅樓夢》的內(nèi)容,只有吳云(玉松)的題詞值得關(guān)注:
二十年來士夫幾于家有《紅樓夢》一書,仆心弗善也。惟閱至“葬花”嘆為深于言情,亦雋亦雅矣。是集“一弄花飛”一什亦最佳。
讀此題詞感覺玉松對《紅樓夢》的認識前后似有不小的變化,而這變化或許就開始于他對潘炤《紅樓夢詞》的批閱。實際上,他對潘炤的三十二首詩讀得很仔細,曾留下十一處的眉批。如他在《私計》詩旁批道:“香奩聯(lián)詩,如此方是雅聚”,針對的當是詩中關(guān)涉的情節(jié);在被他“嘆為深于言情”的《葬花》詩旁,批的是“說杜老一片花飛減卻春,脫胎便爾,高超!玉松”,此批稱許的是潘氏化用杜甫詩句的高妙,雖以杜詩作參照,但其潛在的互文之詩,自仍是原書之《葬花吟》,因為只有與之相較才能產(chǎn)生恰切與否的感覺。吳云在《失玉》詩旁批的是:“君真情種,乃皈依釋乘致”,此批所針對的自然是以“懸崖撒手”來告別紅塵的賈寶玉。
題詞里的“仆心弗善”,表達的顯然是對當時家置一編這種“紅樓熱”現(xiàn)象的不以為然。而從吳云對潘詩所加的評語來看,他非但不反感《紅樓夢》而且對其情節(jié)還很熟悉。故此,筆者萌生出一個大膽的推測:吳云此前當是熟讀小說《紅樓夢》的,受潘炤之托作題詞時,他又進行了重溫,至少題詞之舉勾起了他對紅樓故事的聯(lián)想。或許經(jīng)過了“閱至《葬花》,嘆為深于言情”似的反芻過程,他越來越體悟到《紅樓夢》的藝術(shù)魅力了呢。當時,在他周圍有不少友人都在把玩《紅樓夢》,張問陶即是顯例。他接觸多了,認識在漸趨改變也是有的。嘉慶十五年為潘氏《紅樓夢詞》題詞之后,時隔九年,吳云又在嘉慶二十四年為石韞玉《紅樓夢傳奇》寫了序。此序劈頭就稱《紅樓夢》為“稗史之妖”,自是認可它的不同尋常。他在序中寫到那么多的關(guān)涉《紅樓夢》的現(xiàn)實事件,說明他對紅樓的傳播及影響有持續(xù)的關(guān)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及“譚七子受”編寫《紅樓夢曲》在京城搬演卻被“冬烘先生”禁演的事。“譚七子受”是指字“子受”的譚光祜,那個呵禁譚劇的“冬烘先生”,則是指王大經(jīng)。關(guān)于毀禁《紅樓夢》及紅樓戲的情況,非本文題中之義,為免旁逸斜出,暫不多論。
上邊就潘炤詩題說了不少并非本文題外的話,現(xiàn)在來看《鸞坡居士紅樓夢詞》。關(guān)于詩作緣起,潘炤自序中說得清楚:
惟巨卿逍遙子者索詩于余,視其目,黃粱也,仙枕也。原夫雪芹外史,曾傳樓角裁紅;云澗歸樵,復(fù)奏池頭凝碧。
顯然,潘炤此題是為“巨卿逍遙子”索詩而作的。研究者曾據(jù)此序考辨了《紅樓夢》的首部續(xù)書《后紅樓夢》的作者問題。但是,研究者緊盯逍遙子索詩這個實事,卻未去探討逍遙子為什么為仲振奎《紅樓夢傳奇》索詩,而不是直接為自己的《后紅樓夢》求題。事實上,為《后紅樓夢》題詞者甚夥,不計重出,得二十五人。如此陣容,可謂濟濟一堂,卻獨未得潘炤為之題詞,就現(xiàn)有材料來看,最大的可能是彼時潘炤尚游幕遠方,傳遞信息亦頗不方便。潘炤的行跡將在下文試作追蹤。
我們知道,仲振奎《紅樓夢傳奇》取材于《紅樓夢》和《后紅樓夢》,乃“合兩書度曲”而成,共五十六出,分上下兩卷,全劇的劇情編排、位置角目、安頓排場,多依托于逍遙子的《后紅樓夢》。上卷演“離恨”,敷陳《紅樓夢》中寶黛釵的戀愛和婚姻之發(fā)生、發(fā)展到幻滅的過程,并及寶玉與襲人、晴雯的糾葛;下卷則是對上卷所記離恨的反轉(zhuǎn),是“補恨”,鋪演黛玉、晴雯還魂,與寶玉共結(jié)連理。全劇先悲后喜,完成了寶黛等下凡經(jīng)世且實現(xiàn)“緣自天合”的循環(huán)。
嘉慶四年(1799)綠云紅雨山房初刻本《紅樓夢傳奇》,在紅豆邨樵自序之后,附錄了以“都轉(zhuǎn)賓谷夫子題辭”為首的十五人的題詞。賓谷夫子即曾燠,其他十四人中不少是他幕府中的幕賓。
曾燠的題辭是:
夢中死去夢中生,生固茫然死不醒。試看還魂人樣子,古今何獨《牡丹亭》?
不解冥冥主者誰,好為兒女注相思。許多離恨何嘗補,姑聽文人強托辭。
底事仙山有放春,爭妍逐艷最傷神。真靈亦怕情顛倒,人世蛾眉不讓人。
櫳翠怡紅得幾時,葬花心事果然癡。一園盡作埋香冢,不獨芙蓉豎小碑。

《紅樓夢傳奇》下卷寫補恨,寫黛玉和晴雯還魂,超越了生死,曾燠比之于《牡丹亭》,其評價不可謂不高。這首詩基本能夠代表卷首所附題詩對仲劇的認識與評價。

潘炤的這些題詩,大致貼近仲劇情節(jié)。如第一首《原情》:
夢里紅樓接大荒,晴天色界兩茫茫。芳齡永繼何離棄,仙壽恒昌那失忘。

仲劇第一出“原情”,旨在統(tǒng)領(lǐng)全劇,而此詩也基本將寶黛釵三人的標識物及特質(zhì)全部點到,從中讀者大致可預(yù)測到三位主角的歸屬。三人的婚戀關(guān)系也正是仲劇的中心情節(jié)。詩中“金魚煉去不容光”,寫的是黛玉故事,是仲劇依照《后紅樓夢》而設(shè)計的重要關(guān)目。寫黛玉在入殮時口含神奇的“練容金魚”而保得肉身不壞,后得以原體還魂。這條金魚兒據(jù)《后紅樓夢》第七回的描寫,“原不是金子打的,是生成的一件寶貝”,“是什么安期島上玉液泉內(nèi)長出來的。但凡亡過的人,口內(nèi)噙了它,千年不得壞”。而金魚“身上還有赤金的兩行字。一面是兩行:‘亦靈亦長,仙壽偕臧’;一面是三行:‘一度災(zāi)劫,二貫福祿,三躍云淵’”。此物原系黛玉動身進京前告別兄長(仲劇為下卷黛玉長兄良玉進京入仕提早做鋪墊,特將曹著的別父改成別兄)時,良玉送給妹妹的寶貝。正是賴此寶貝護佑,黛玉才得原體還魂,寶黛釵的故事才得順利往下發(fā)展。
下面再看備受吳云好評的《葬花》:
一弄花飛春不成,傷心偏爾有顰卿。東流西泛都非計,淺掃深埋自有情。
試卜香泥最香處,愿攜閑鍤此間行。憂開惜落癡如許,卻使鯫生淚亦傾。
此詩在藝術(shù)性上確實很難跟《紅樓夢》之《葬花吟》比肩,但它描述的是黛玉葬花的行為及此舉之情感寄托,屬另立格局,自有不同于曹著“葬花”的其情其境在。
潘炤題詠《紅樓夢傳奇》下卷的詩作,雖只取了劇本一半的內(nèi)容,但他認同仲振奎對《后紅樓夢》的依傍,故特為黛玉嗣兄林良玉——這個曹著中根本不存在的人物,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只是此詩并不直接寫良玉其人,而是寫因為他的存在,林家后繼有人及由他帶來的既富且貴的復(fù)興。《后紅樓夢》中的良玉本是黛玉的叔伯哥哥,因其父母雙亡,林如海夫妻“血抱長大,恩若親生”,如今要公車北上,帶著近二千萬的家產(chǎn)進京置業(yè)待考,黛玉因此不再孤苦無依,所謂“故家留得舊梅根”是也。
《見兄》題曰:
自從杞菊聚寒溫,又合朱陳兩姓村。鷺序池邊覘玉友,雁行天際識金昆。
千鄉(xiāng)遠送云遮榻,一宅平分月到門。莫訝暗香都引入,故家留得舊梅根。
黛玉還魂后頗思念遠在家鄉(xiāng)的兄長,正巧林良玉欲進京趕考,先派了家人王元進京,買下賈府間壁早已被賈府抵押出去的大宅子,這樣林賈兩府就只一墻之隔了。后還特為黛玉兩府行走方便,破墻開了一個小門,所以詩中有“一宅平分月到門”之詠。黛玉與長兄京中團圓,這林良玉還很快中了探花。仲劇設(shè)有“見兄”一出,潘氏便尊題寫了這首《見兄》。
最后來解讀最末的那首《堪夢》:
醒迷花謝是何緣,慧業(yè)文人覺后先。恨補蒼穹原有闕,情填碧海本無邊。
一痕青埂通靈障,半枕黃粱警幻權(quán)。從此歸來甘露外,不妨還爾太虛天。
要解讀該詩,首先須了解“醒迷花”的由來。《后紅樓夢》第十八回設(shè)計了一個頗具魔幻色彩的情節(jié):《紅樓夢》中那個寶黛葬花的花塚之上長出一樹奇花,寶玉深情地稱作“黛梅”、“如意梅”。此樹忽然長出,瞬間開滿各色奇花,忽又一夜落了個干凈,連花瓣都了無蹤影。這一筆,無非旨在標舉寶黛愛情的奇異與仙緣,《紅樓夢傳奇》則大加利用,不吝筆墨大加渲染與發(fā)揮。最后一出稱“勘夢”,即以此花點題,說該花乃是警幻仙姑特上蓬萊借來的“醒迷花”,為的是點醒“異常眷愛恐誤前程遲了飛升時日”的黛玉。史真人(湘云)受命帶領(lǐng)仙女布花散花,創(chuàng)造神跡以“破癡人情夢早乘槎”。這個不折不扣的借題發(fā)揮,就明旨點題而言,是成功的再創(chuàng)作。從上引所詠可見,潘炤對醒迷花之點題明旨的設(shè)計很認可,對改編自《紅樓夢》和《后紅樓夢》二書的仲氏《傳奇》可說是非常的熟悉,對仲劇的改編特色也把握得頗為到位,同時亦可看出他對原書《紅樓夢》更是熟悉。當然,他認可仲氏對《后紅樓夢》團圓結(jié)局的選擇,并不足以令我們蘧下他不喜歡原書《紅樓夢》悲劇描寫的斷語,因為喜團圓還是認悲劇,那是閱讀習(xí)慣問題,非關(guān)審美。而就“言情書”層面的解讀而言,我們還是可用靈心慧性稱許他的。
二、《烏闌誓傳奇》、《釣渭間雜膾》與潘炤其人

水到吳江平望橋,曾聽翻曲幾吹簫。不堪卒讀人間誓,自許重傳天上謠。

熊女史很有真性情,本著一份可愛的天真,她可以因為作家潘炤為霍小玉安排了還魂再生并成就小玉的美滿姻緣而感謝他的“筆下超”。讀者喜歡大團圓的結(jié)局,改編者便趨之若鶩。單就紅樓戲而言,仲振奎《紅樓夢傳奇》而外,還有萬榮恩同樣取材于前后《紅樓夢》的《醒石緣》。類似于熊璉這樣的閱讀訴求,首先來自于補恨書和團圓戲的引導(dǎo),而它又反過來促生了更多喜劇作品的創(chuàng)作,而且同好們總能找到自己的方式來表達這種頗具普遍性的認同——或直接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戲曲譜寫,或是對之進行評批和題詠。
仲振奎因為逍遙子《后紅樓夢》“大可為黛玉、晴雯吐氣”而欣慰,至于合二書譜曲以傳;潘炤因為寫補恨戲的名聲在外,故引來作補恨書的逍遙子為取材自《后紅樓夢》的仲劇索詩同賀。這個人事鏈接,顯見的是以趣味相投而致惺惺相惜的以文會友。在文化發(fā)達的吳下諸地,文人們因為喜歡、為了炫才或是借人酒杯澆我塊壘,形成了閱讀、品評、題詠和改編《紅樓夢》的風(fēng)尚,這從上文述及的《后紅樓夢》、《紅樓夢傳奇》及《鸞坡居士紅樓夢詞》聚焦的文人圈子即可窺見一斑。他們因為《紅樓夢》有了更多的話題和交流的機緣,在為生活而辛勤勞作之余,可以小小地實踐一下為人生而藝術(shù)的別樣體驗。在生存和理想之間,有部閑書《紅樓夢》可以把玩,借以抒情、炫才,確是閑趣、樂事、雅集,令浮躁的我輩好生羨艷。
以下結(jié)合潘炤《烏闌誓傳奇》及其他各類著作的序跋、題詞,對潘氏生平、交游等略作考辨。
關(guān)于潘炤,一般的介紹是:字鸞坡,江蘇吳江(今屬蘇州)人,生卒年不詳,大致活動于乾嘉時期。希望通過我們下文的探尋,對他的認識能有所增益。

潘炤《烏闌誓》“自序”記述了該傳奇從起意、構(gòu)思到幾年后歸里方正式寫作完稿的經(jīng)過。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正在上黨李月槎幕中的潘炤受七夕節(jié)慶氛圍所感,寫詩記霍小玉事。第二年,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試為度曲。自廣陵歸家后,潘炤回顧自身的蹉跎歲月頗多感傷,復(fù)因其妻的督促,全劇“不數(shù)日而成”,而作序的時間已在甲寅,即乾隆五十九年(1794),距離創(chuàng)作之初起已過去了十二年。


潘炤雖倍感蹉跎,但對于自己的“貴游四方,名碩所許”,還是頗為自豪的。這從他樂于在名人題詞之后隨處以“跋”“志”數(shù)語自相標榜即可見一斑。
袁枚為《烏闌誓》題詞:
彩毫夫擅作非難,紅豆妻拈課且寬。料得曲終雙叫絕,烏絲闌下并肩看。
醉月騷人能慕色,簪花美女會憐才。若非割愛成長夢,那得傳情到劫灰。
很明顯,袁枚深悉潘炤撰作傳奇的起因,“烏絲闌下并肩看”設(shè)想的當是潘氏夫妻共讀《烏闌誓》的情景。譜寫此劇,正如潘氏自序所道,乃是“以諾細君”。袁枚詩下小注說:
嘉慶丙辰夏五,隨園老人袁枚于廣陵鹺署(云按:即兩淮鹽運使府署)借讀一過,并題為詩友鸞坡主人翻曲弁首也。
之后又書七絕并題跋道:
七才子外多才子,子本多才勝才子。少已衡量非斗石,老其狡獪奈何哉?
昔次后七子已定,而君適至,因戲謂多才子云。子才又跋。
被袁氏許為“多才子”,潘炤很是得意,所以特識記一筆,曰:
袁子才先生,昔在錢塘,為余畏友。丙辰春,復(fù)悟(晤)于廣陵,公已八十有一。言越二歲可再赴瓊林,因為《烏闌誓》弁首并及同學(xué)少年舊話,有多才子之稱,戲跋此也。炤識
在錢塘?xí)r,潘炤自認袁枚是其畏友,可知關(guān)系頗近。嘉慶丙辰(1796)又在廣陵會面,題詞即在此時。
“嘉慶丙辰”字樣,使筆者不禁聯(lián)想起隨園老人為后世津津樂道的一件逸事。嘉慶元年(即丙辰年)二月花朝,袁枚為《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yè)圖》題跋,跋文中憶及乾隆壬子(1792)三月于西湖寶石山莊帶領(lǐng)女弟子們作詩雅會之事,所跋之圖即記此類問學(xué)場景。丙午(1796)春,潘、袁再會于廣陵,潘炤得袁枚題詩,似有共話當年錢塘之會的聚談。只不知潘氏在錢塘可曾有幸趕上寶石山莊之詩會盛典否?為何袁枚是潘之“畏友”,所稱何來?發(fā)生過什么故事?二百余年后的我們自是無從知曉了。
刻本上署名“石君姻弟珪”的題詞也提供了潘炤的一些信息,詩云:
琳瑯著作等身奇,江左風(fēng)流素所知。名士河陽傳奕葉(稼堂先生從孫),長安又見柳枝詞。靈槎那便渡銀河,彩筆輕翻五色波。料欲正聲驚玉茗,不教人艷雪兒歌。
其下小注是:
鸞坡先生,吳下名士。其仲為余襟倩。文章學(xué)業(yè)迥越,尋恒所素念也。今出填詞下問,乃有感寓言非真,倚曲者知音然不(否)?石君姻弟珪拜手

另有石韞玉的題詞:
粲然璧玉齒,殘絲遂成綺。癯然一名士,多情乃若此。
水樂自宮徵,雅奏恰所委。斷腸花孰取,為摹兒女爾。
用“癯然”來形容潘炤,說明潘氏此刻已是個清瘦的老叟了。可惜石韞玉沒留下什么有助于勾勒作者生平的詩注。石韞玉(1756~1837)乾隆五十五年(1790)狀元及第,從潘炤自序?qū)懹谇∥迨拍?1794)可推知,石氏看到《烏闌誓》時已躋身新貴,潘氏能索到石的題詩,二人又是同鄉(xiāng),想來是相熟的。石韞玉年逾五十后解甲歸田,在家鄉(xiāng)開始其講學(xué)生涯,歸里之后還創(chuàng)作了十出的《紅樓夢傳奇》,并于嘉慶二十四年己卯(1819)刊行。該劇晚出,但完全異于仲振奎《紅樓夢傳奇》和潘炤《烏闌誓傳奇》的大團圓取向,遵從小說《紅樓夢》的旨趣以悲劇收結(jié)。
潘炤曾為仲振奎《紅樓夢傳奇》題詩三十二首。潘炤一生好與名宦賢士交誼,卻未見他為石著《紅樓夢傳奇》寫點什么。難道上蒼未給他看到石劇的時間嗎?此處不好妄加猜測。
為潘炤《烏闌誓》題詞的,石韞玉之外還有個同為吳縣人的狀元潘世恩(1769~1854)。潘世恩系乾隆五十八年(1793)狀元,嘉慶二年大考一等,擢侍讀,偕紀昀經(jīng)理四庫全書事宜。他的題詞是:
摩人摩墨一《烏闌》,千古傷心語亦寒。慕色十郎癡未已,憐才小玉夢方殘。
矢懷自許臺能望,息意誰知井不瀾。多謝情絲閑組織,青天碧海重回還。
其下詩注道:
鸞坡老人學(xué)薰班馬,賦艷齊梁,既體骨之徵仙,亦宮商而托夢。玉茗應(yīng)妒,楚蘭不騷矣。甲子仲春,弟世恩題
甲子是嘉慶九年(1804),潘世恩還在偕紀昀經(jīng)理四庫全書事宜,處在朝中為官的第一階段。自稱“弟世恩”,按常規(guī),或因彼此年歲相差不多,或因同姓而排輩論之。世恩自己當年不過三十有五,但題詞小注中卻稱潘炤為“鸞坡老人”,由此推測,此處的稱兄道弟當不是因歲數(shù)相近之故,應(yīng)當是同姓兼平輩吧。
潘炤好像并未做過官,《西泠舊事百詠》的跋中,吳鼒稱他為“給事”,是否真做過給事中,待考。但他做過幕僚,這倒是有據(jù)可依的。言朝標為《烏闌誓》題詩曰:
前輩風(fēng)流又在茲,楚襄一夢記髫時(先生在先大夫襄陽幕中,仆尚束發(fā))。
不堪重聽《烏闌》曲,鏡里蕭騷鬢已絲。
言朝標,字皋霎,江蘇昭文(今常熟)人,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4月29日生,言如泗次子。言如泗(1716~1806),字素園,乾隆二十九年(1764)任襄陽知府,三十四年曾一度因失察下屬罷官,尋即因之前政績頗豐而復(fù)出(言氏曾任山西垣曲知縣及保德州知州,素“以愛民教士為先務(wù)”,且曾主持興修兩地水利)。《清史稿》對他的評價是“愛士恤民而治盜嚴”。

在潘炤的各類著作的序跋或題詞中,吳鼒的名字出現(xiàn)頻率最高,給我們的感覺是他與潘炤的關(guān)系很密切,他提供的信息量相對也最大。

吳鼒在《西泠舊事》跋中提及的這位梁相國,就是梁國治(1723~1786),字階平,會稽(今浙江紹興市)人。乾隆十三年(1748)狀元,三十四年為湖北巡撫,并代理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三十六年(1771)移任湖南巡撫,三十八年進京,命在軍機處行走,代理禮部侍郎,次年授戶部右侍郎,四十二年(1777)升為戶部尚書。
據(jù)吳鼒跋文,潘炤在湖南待過多年,梁國治任湖南巡撫期間(乾隆三十六、三十七年),潘仍在湘,并且有機會和巡撫的弟弟郊游、與巡撫唱和。潘炤何時離開湖南,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吳鼒為《西泠舊事》的題跋寫于何時,因缺頁也已看不到了,所以他與潘炤在都中相遇的時間也無從知曉。幸運的是,我們尚能看到《鸞坡居士紅樓夢詞》前的吳鼒識語,所謂“有仙語有佛語有英雄語有才子語,鼒所賞皆雅人語,愿與誦金經(jīng)人印證”,至少說明那次兩人“遇于都”時,潘炤將《紅樓夢詞》給吳鼒賞鑒還是有收獲的。
潘炤《西泠舊事》自志云:“己巳(嘉慶十四年,1809)歲暮,巨卿逍遙子者,招余于梅花香雪齋中,左圖右史,鍵戶圍爐,頗征閑適。”有心人據(jù)以將逍遙子與梅花香雪齋作勾連,推斷《后紅樓夢》為袁枚所作——因為袁枚有個梅海。對此說,這里不作辨析,要說的是,潘炤與袁枚如上所述確有不淺的交往,潘氏還深為堪稱前輩的袁枚所器重。吳云和潘世恩都為潘炤的《西泠舊事百詠》寫過序,吳云記于嘉慶辛未(1811),世恩未署年月。
潘炤的其他著作中還有一些他人所作的序文和題詞,因基本未提供本文所需的信息,此不贅。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秦基,他對潘炤的描述應(yīng)該相對到位些。從《烏闌誓》、《釣渭間》都由秦基作序來看,潘炤與他的關(guān)系應(yīng)當非同尋常。

且看秦基《釣渭間合序》對潘炤的描述:
鸞坡先生名宿東南,家聯(lián)于虎阜平山之麓;浮蹤西北,荊班于鳳城潞水之郊。遠跡公卿,而公卿自下;放懷泉石,而泉石是高。有“一生酒興追撈月,半世詩情夢浣花”句。吳藹人殿撰為書座聯(lián),可想也。白眼看人,帽檐常側(cè);赤心赴友,囊里時傾。五岳游探,群羨長生;有箓七襄,組織咸夸。……
這一長段之后,又述及潘炤遍布“關(guān)隴”、“塞邊”及“謫仙祠畔”之類的仙游歷程,因系韻文風(fēng)格,難免夸飾之譏,此處無需多引。上引之文,實則已描繪出一位四海為家有些桀驁又為人仗義的江南才子的生動形象來了。
龍汝言為潘炤《釣渭間》題詞時曾言“先生少為袁簡齋、畢秋帆兩前輩重”,他自己署名時又自稱“愚弟”,故可斷言,潘炤應(yīng)該比袁枚、畢沅年輩低。這袁枚是進士,告歸得早,是非常有影響的大名士,畢沅則是乾隆二十五年狀元,學(xué)術(shù)上亦享盛名。而這位龍汝言則在小百尺樓出版潘炤《雜膾羹》(《釣渭間雜膾》)的甲戌年,高高地中了頭名狀元。

重讀潘炤《鸞坡居士紅樓夢詞》時,為了更好地知人論世而翻閱了他的其他作品,不意竟帶出這么多與其有文字交往的官宦文人及名士,堪稱意外之喜。雖說潘炤沒有直接評點、題詠過《紅樓夢》,但紅學(xué)史上該當記住這類具有特質(zhì)的紅樓愛好者。有這樣一個性情中人,手書無體不備,喜歡《紅樓夢》及據(jù)此改編的作品,自己題詠《紅樓夢傳奇》,還樂于廣為索題,于《紅樓夢》的深入人心,確是功不可沒,請記住這個四海為家的鸞坡居士吧。
注
:① 林冠夫《紅樓詩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頁。
② [民國]吳克岐《懺玉樓叢書提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52頁。影印本,筆者自作標點。
③ ④ [清]潘炤《從心錄》卷首,見《北京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十三冊,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69-70、第71頁。下引《失玉》詩批語,見72頁,不另注。
⑤ 吳云為石韞玉《紅樓夢傳奇》所寫的“敘”是:“《紅樓夢》一書,稗史之妖也,不知所自起,當《四庫》書告成時,稍稍流布,率皆抄寫,無完帙。已而高蘭墅偕陳(云按:應(yīng)為程)某足成之,間多點竄原文,不免續(xù)貂之誚。本事出曹使君家,大抵主于言情,顰卿為主腦,余皆枝葉耳。花韻庵主人衍為傳奇,淘汰淫哇,雅俗共賞。《幻圓》一出,挽情瀾而歸諸性海,可云頂上圓光,而主人之深于禪理,于斯可見矣。往在京師,譚七子受偶成數(shù)曲,弦索登場,經(jīng)一冬烘先生呵禁而罷。設(shè)今日旗亭大會,令唱是本,不知此公逃席去否?附及以資一粲。”[清]石韞玉《紅樓夢傳奇》見《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學(xué)苑出版社2010年版。
⑥ [清]潘炤《鸞坡居士紅樓夢詞·序》,見《北京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十三冊,第70頁。
⑦ 蘇興《〈后紅樓夢〉作者為“常州某孝廉”辨》,《紅樓夢學(xué)刊》1983年第2輯。關(guān)于逍遙子《后紅樓夢》的作者問題,還可參見葉舟《〈后紅樓夢〉作者之我見》,《明清小說研究》2010年第4期;許雋超《呂星垣作〈后紅樓夢〉考》,《紅樓夢學(xué)刊》2012年第6輯。
⑧ 乾嘉間刻本《后紅樓夢》,正文三十卷,附錄二卷。卷三十一為“后紅樓夢附刻詩第一種”,附刻的是吳下諸子和大觀園菊花社原韻詩。卷三十二是“后紅樓夢附刻詩第二種”,是吳下諸子為大觀園菊花社補題詩。兩卷題詞的作者,不計重出,得二十五人,依次為李子仙(名福)、吳春齋、蔡鐵耕(名云)、翁春泉(名義海、號退翁)、江云墀、蔣賓嵎(名寅)、楊梅溪(名舫)、王豫庵、高頗愚、李四香(名銳)、吳養(yǎng)亭(名慶孫)、顧南雅(名莼)、周石菭(名鶴立)、吳藹人(名信中)、顧朗山、胡湘南(名鼎衡)、金向亭、張銀槎、邵勤齋(名南熏)、孫二顛、蔣于野(名莘)、陶香疇、顧書巢、董琴南(名國華)、張白華(名思孝)。
⑨ 可參見拙著《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xù)書研究》第五章第二節(jié)“仲振奎《紅樓夢傳奇》:合二書而成”,中華書局2013年版。
⑩ 如鉛山蔣知讓(藕船)、清江黃郁章(賁生)、丹徒郭堃(厚庵)、儀征詹肇堂(石琴)、吳州俞國鑒(澂夫)、吳州陳燮(澧塘)、甘泉張彭年(涵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