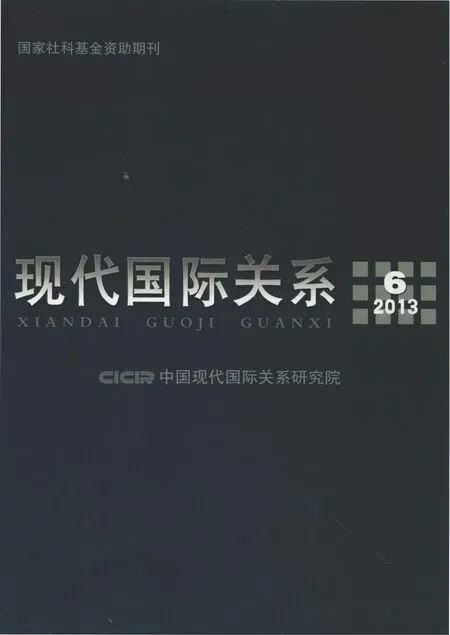國際海運減排博弈及中國面臨的“碳陷阱”
肖 洋
為了應對海洋氣候變化,國際海事組織(IMO)正在擬訂航運碳減排機制,以促進國際海運的綠色化。新機制將帶來更嚴格的檢驗標準,這無疑會對世界及中國航運業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尤其對于尚未完成復興大業的中國來說,參與國際海運減排是一把雙刃劍,中國必須在保持經濟增長與構建負責任大國形象之間保持平衡,尤其須防范國際海運減排中的“碳陷阱”。
一、國際海運減排規制的構建進程
國際海事組織是聯合國系統中負責航運安保、防治海洋污染的專門機構,其宗旨之一就是在有關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問題上鼓勵并促進普遍采用可行的最高標準,并有權制定相關法律。①“Introduction to國際海事組織”,http://www.國際海事組織.org/About/Pages/Default.aspx.(上網時間:2012 年11 月24 日)國際海事組織具有較高的國際公信力,國際海運減排的相關規制主要由其負責制定。
《京都議定書》是最早提及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海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的國際條約,并就制定海運減排規則問題對國際海事組織進行了授權。《京都議定書》第二條第2款規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附件Ⅰ國家應通過國際海事組織力求限制或減少海運燃油消耗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②United Nations,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1998,p.2.這就為國際海事組織開展海運溫室氣體減排工作提供了法理依據。從1998年起,國際海事組織開始關注國際海運減排問題。隨后幾年,國際海事組織下屬的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MEPC)始終圍繞國際海運減排技術和方法展開討論。③國際海事組織,“Review of Regulations to Prevent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http://www.國際海事組織.org/blast/mainframe.asp?topic_id=1484.(上網時間:2012年11月24日)由于《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MARPOL)側重防止船舶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未涉及大氣污染及氣候變化問題,因此在《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Rio Declaration)通過后,國際海事組織開始著手對《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進行修訂,增加了標題為“防止船舶造成大氣污染規則”的附則VI,并于2005年生效,從而把國際海事組織在環保方面的工作擴展到大氣領域。①Resolution MEPC.203(62),“Amendments to the Annex of the Protocol of 1997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1973,As Modified by the Protocol of 1978 Relating Thereto”,15 July 2011,p.3.
2008年,海洋環保委員會第57次會議批準溫室氣體排放工作組編寫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短期及長期措施計劃,原則上確定了國際海事組織未來船舶溫室氣體減排的法規框架,如對于新造船舶,要推行強制性的新船二氧化碳設計指數;對于現有船舶,在《船舶二氧化碳排放指數自愿試用臨時守則》下先試用收集數據,進而強制性應用于所有船舶,并根據試用數據制訂全球效率基線;對所有船舶征收全球船用燃油稅或推行排放交易機制和/或清潔發展機制。②“國際海事組織,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MEPC),57th Session”,31 March –4 April 2008,http://www.國際海事組織.org/blast/mainframe.asp?topic_id=109&doc_id=8870.(上網時間:2012年12月2日)2009年,海洋環保委員會第59次會議通過了包括《能源效率的設計指標》(The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EEDI)、《能效營運指數》、《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計劃》(Ship Energy Efficiency Management Plan,SEEMP)等五份技術、營運方面的重要文件,以提升船舶能效的方式推動綠色航運的進展,并制定了利用市場機制進行減排的工作計劃。2010年,海洋環保委員會第60次會議上關于《國際航運業全球排放貿易框架的應用領域》提案,提出以“碳交易”(Emission Trading Scheme,ETS)方式推動國際船舶減排進程。③國際海事組織,Practical Aspects of a Global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Shipping ,MEPC 60/INF.8,18 December 2009,p.1.而在2011年海洋環保委員會第62次會議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附則VI締約國一致通過了國際航行船舶溫室氣體(GHGs)減排措施,這標志世界首部行業性的具有強制實施效力的全球溫室氣體減排規定就此誕生。這也是國際海事組織首次通過適用于所有國家船舶的強制性能效標準。2012年10月海洋環保委員會第64次會議詳細研究了基于市場機制的國際航運減排措施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諸多影響,并依據《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附則VI修正案第四章第23條“對需要技術援助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直接幫助”的規定,要求相關締約國對發展中國家成員國進行技術援助與技術轉讓。④國際海事組織,Implementation of Energy-efficiency,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and Ship-recycling Rules on Busy Agenda for國際海事組織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September 27,2012,http://www.國際海事組織.org/mediacentre/pressbriefings/pages/39-mepc-preview.aspx.(上網時間:2012年11月25日)至此,國際海事組織針對海運減排問題構筑了技術、營運、市場機制三條路徑,其中技術與營運措施已經完成制度設計,并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在市場機制方面的討論也將取得突破性進展。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個多邊協商平臺,國際海事組織通過的強制能效標準只針對船舶而不問船舶所屬國,表面看似高效,實質卻有失公允,特別是其為發展中國家設定了強制性的量化技術指標,違背了“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這一現象形成的重要原因是“方便旗船”現象的存在。“方便旗船”是指在船舶登記開放或者寬松的國家進行登記,從而取得該國國籍,并懸掛該國國旗的船舶。簡言之,“方便旗船”是指懸掛非船主國家國旗的船只,而選擇掛方便旗的船舶,普遍船齡較大,能效較低,減排難度較大。
“方便旗”現象導致船舶的實際控制國與登記國不一致,這使得“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適用存在很大技術困難。依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統計資料,世界56.1%的船舶都在全球十大開放登記國巴拿馬、利比里亞、馬紹爾群島、安提瓜與巴布達、巴哈馬、百慕大、塞浦路斯、馬恩島、馬耳他、圣文森特與格林納丁斯(它們皆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登記。目前,最大的方便旗國是巴拿馬,其掛旗船舶噸位占世界船隊的21.9%;其次是利比里亞(占11.9%)和馬紹爾群島(占7.1%)。擁有“方便旗船”的船東則主要來自發達國家或地區。截至2011年初,世界商船隊噸位達到13.96億載重噸,排名前35位的船主國控制著其中的95.57%,其中66%又由發達國家船主控制。全世界總噸位中有68.3%懸掛外國國旗,其中發達國家懸掛外國國旗的百分率高于發展中國家,約占懸掛外國旗船舶的74%。⑤UNCTAD,P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1,UNCTAD/RMT/2011,pp.43-44,45,46,49 .低廉的注冊費、低稅甚至免稅以及可隨意雇傭廉價勞動力是船主選擇懸掛他國國旗的誘因。工資水平較高的歐美國家公司對此尤其感興趣。可以說,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更愿意發展“方便旗船”。這就是說,盡管大多數船舶被發達國家所控制,但其在名義上卻屬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果僅要求發達國家的船舶承擔減排義務,則發達國家本國船籍的船舶只占全球船舶的一小部分,因而減排壓力較小,并可以通過“方便旗”制度逃避減排義務。雖然有些國家建議參照“國際獨立油輪船東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Tanker Owners)等一些專業組織的做法,以實際控制人為標準確定船舶的國別屬性,從而建立起區別對待不同船舶的減排制度,卻因美歐等發達國家的激烈反對而難以達成共識。
二、國際海運減排的博弈態勢
氣候談判的實質是各國為搶奪低碳經濟控制權展開的博弈,涉及世界各國的切身利益。從歷次氣候會議博弈的結果不難看出,各方基于不同的利益訴求,已初步構成國際海運減排博弈的攻守格局。根據各方在海運減排責任問題上的主張差異,博弈各方可分為以歐盟為代表的“無差別責任”派、以中國為代表的“有區別責任”派以及以美國為代表的“有條件責任”派。
“無差別責任”派包括歐盟、小島國聯盟等,其核心主張是,突出減排責任的強制性與減排標準的普適性。“無差別責任”派認為,船舶溫室氣體排放是全球性的,區域性減排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與效果,只有采取全球范圍的目標減排,并輔之以市場機制(碳排放交易),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減排。歐盟因具有在節能減排立法、政策、行動和技術等領域的優勢,而將自身視為氣候議題的領導者,并在海運減排規制構建中當起了急先鋒。在歐盟的推動下,國際海事組織下屬的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第57次會議通過了國際航行船舶溫室氣體控制框架的基本原則,由于其中“強制、平等地適用于所有船旗國”的條款,違反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所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引起了中國、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大國的激烈反對。①國際海事組織,Environment Meeting Approves Revised Regulations on Ship Emissions,MEPC 57th Session,31March-4 April 2008,http://www.國際海事組織.org/blast/mainframe.asp?topic_id=1709&doc_id=9123.(上網時間:2012年11月25日)2011年7月15日,歐盟等發達國家利用國際海事組織獨特的“簡單多數”表決機制,在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第62次會議上強行表決通過《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附則VI修正案,該修正案對船舶能效方面作出了規定,使《能源效率的設計指標》(已于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和《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計劃》具有強制力,②國際海事組織,Technical and Operational Measures,http://www.國際海事組織.org/ourwork/environment/pollutionprevention/airpollution/pages/technical-and-operational-measures.aspx.(上網時間:2012年11月25日)適用于全球400載重噸以上的海運商船,并將于2015年起開始實施。這必將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海運減排壓力。面對發展中國家的反對,歐盟等國采取“技術與市場相分離”的兩步走策略,先在技術措施上達成一致,再逐漸引入市場機制,引導船舶節能減排的實施,最終構建海運減排的制度體系。歐盟堅持嚴格的船舶登記制度,將出入其成員國的船舶納入其碳排放交易體系,并以港口國監管的方式拒絕減排不符合標準的外籍船舶、特別是“方便旗船”入港,支持使用各種市場手段特別是征收全球航運燃油稅、引入排放交易機制等來推行海運減排。歐洲實施單方面區域減排規制的做法,帶來了域外管轄的合法性等問題,引起中美日等國的反對,使得國際海運減排的博弈平臺風急浪高、暗流涌動,將世界各國的海運戰略、安全、經濟利益都卷入其中。
“有區別責任”派包括以新興大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其核心主張是,堅持將《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作為海運減排責任分擔的法理基礎,反對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強制性減排的約束范圍。這些國家認為,國際海事組織出臺的任何措施,都不應當有悖于“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在制定強制性排放標準前,發展中國家需要一個過渡期,國際海事組織減排措施應適用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不應與發達國家同等承擔船舶減排義務。由于“有區別責任”派的國家在國際碳減排問題上存在話語權缺失且內部意見分歧較大等不利條件,因此它們的目標在于維護發展中國家的集體發展權以及在國際碳減排議程中的參與權,主要表現為反對西方國家在構建國際減排規制的壟斷化趨勢與歧視性條款。例如在海洋環保委員會第57次會議中,中國從“發展及消除貧困是首要與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發展中國家的履約程度取決于發達國家承擔的有關資金和技術轉讓承諾的履行程度”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制定排放標準不能帶來新的技術門檻”的附加要求,反對建立適用于所有國家的強制減排機制,堅持國際海事組織的有關減排安排對其他談判不構成先例的原則。①國家氣候中心:“黃磊參加國際海事組織船舶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組第一次會間會的總結”,http://ncc.cma.gov.cn/Website/index.php?NewsID=3332.(上網時間:2012 年12月2日)
“有條件責任”派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歐盟之外的其他發達國家,其核心主張是,以新興經濟體國家作出減排承諾作為本國承擔減排責任的先決條件。它們大多為傳統海運大國,因此常常將海運減排議題作為排擠新興大國、增強自身實力的工具。在國際海運減排問題上,美日等國支持“無差別責任派”將發展中國家納入減排對象的基本主張,但由于這些國家改造本國船隊能效的花費巨大,因此在減排標準的強制執行方面態度有所保留,同時也支持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必要的減排技術援助。
根據上述分析,作為國際海運大國的中國、美國和歐盟所面臨的海運減排壓力較大,因此將是國際海運減排博弈中的重要棋手。為了獲取構建海運減排規制背后的話語權與海緣政治經濟及安全收益,世界各國圍繞海運碳減排規制構建的話語權之爭將日益激烈,均力圖在即將出爐的國際海運減排規制中盡可能地維護本國利益。從以上各方的現有力量對比和發展趨勢來看,在國際海運減排問題上已經基本構成了以歐美為代表的既有強國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正面博弈。美歐集團仍屬于強勢方,中國及其他新興大國的利益訴求則缺乏實質性的安全保障,發展權與履約能力受到極大約束,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前工業化階段,因各自利益訴求的差異而不斷分化,在國際海運減排談判中日益被邊緣化,長期處于失語狀態。這種階梯型的角力態勢,使國際海運減排博弈處于變革前的萌動期。
三、中國參與國際海運減排面臨“碳陷阱”
在政府不干預的前提下,一國經濟增長同該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呈正比。由于大多數國家仍然采用高碳經濟增長方式,其履行碳減排承諾必將以減緩經濟增長為代價。因此,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碳減排問題上堅持“雙軌制”,即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反觀美歐等發達國家,則試圖淡化“歷史責任”,鼓吹“減排面前無優惠”,在碳減排目標上實施單軌制。中國海運業“船多、量大、面廣”與造船業“大而不強”的客觀現實,使得中國在接受并履行海運減排規制后,必將面臨海運貿易滑坡引發國內產業鏈不斷惡化,從而導致國內不穩定因素激增的嚴重后果。目前,出口導向型經濟仍是維持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減排能力薄弱的國內海運業則是其中的短板。在日益苛刻的國際減排標準面前,中國必須小心規避某些“環境正義”幌子下的“碳陷阱”。具體而言,“海運減排履約陷阱”、“既有大國的低碳制度陷阱”與“追隨戰略的碳交易陷阱”共同組成了復合式海運減排“碳陷阱”。
所謂“海運減排履約陷阱”,主要是指所有400載重噸及以上的國際航運新船,必須符合《能源效率的設計指標》要求,在目前階段將能效指數降低10%,2020-2024年間再降低10%,2024年后要達到減排30%的目標;已下水的國際航行船舶,亦要符合《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計劃》中列明的準則。②Zabi Bazari,Assessment of國際海事組織Mandated Energy Efficiency Measures For International Shipping,MEPC 63/INF.2,Annex,31 October 2011,pp.1-2.中國龐大的海運船隊普遍船齡較老,設備陳舊,必將為此投入巨額改造資金,并將減緩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按照《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有關船舶《能源效率的設計指標》數值分階段折減的要求,中國有近50%的現有船舶符合能耗基線標準(《能源效率的設計指標》折減率為0),還有50%以上的船舶需要采取船型優化等措施來滿足標準要求。當《能源效率的設計指標》正式生效時,船運界不得不為這50%的“不達標”船舶而恐慌。此外,中國規定在國外購置船舶、建造船舶回國內登記注冊的船舶,需繳納稅率為9%的進口關稅和17%的增值稅,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http://www.gov.cn/zwgk/2008-11/14/content_1149516.htm.(上網時間:2012年12月2日)這使得中資企業為節省船舶投資成本,紛紛選擇國內造船國外注冊,或者國外造船、購船,國外注冊,而這些新船的船齡較輕,能效較高,大多符合《能源效率的設計指標》和《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計劃》等標準。
這種狀況無疑將增大中國的履約難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維持較大規模的海運船隊,溫室氣體排放因而成為生存和發展的剛性需求;另一方面減排履約有助于彰顯中國的大國責任,但必將改造與淘汰大量超齡船、小運力船,而這些又占中國籍船隊的較大比例。這樣做不僅耗費大量資金,而且會在一段時期內削弱中國整體海運競爭力。因此,一面是持續發展的市場需求,一面是步步緊逼的減排標準,中國海運界舉步維艱。
所謂“既有大國的低碳制度陷阱”,主要是指發達國家憑借在國際海事組織等國際組織中的優勢地位與話語權,推行有利于西方的海運減排制度,對中國等新興大國進行經濟洗劫與市場排擠。例如美歐主導的國際海事組織從成立之初就確立了“簡單多數”的議事規則。這一規則大大提高了議事效率,避免了審議事項久拖不決。另外,為使重要公約的修正案能盡快實施,國際海事組織在20世紀80年代初還創制了一種“默示接受”(Tacit Acceptance Procedure)修正程序,②國際海事組織:Adopting a convention,Entry into force,Accession,Amendment, Enforcement, Tacit acceptance procedure, http://www.國際海事組織.org/About/Conventions/Pages/Home.aspx(上網時間:2012年12月2日)大大加快了公約修正案的生效速度。這種看似高效的議事與表決程序,在維護西方大國主導權的同時,剝奪了廣大貧弱國家的議政權,使其處于“被動接受”的尷尬境地。特別是環保技術發達的歐盟急于將“低碳標識”拓展到國際海事組織減排制度的方方面面,意圖讓依賴高碳發展的中國等新興大國在遵循低碳制度的過程中逐漸“自廢武功”。低碳制度陷阱的可怕之處在于,既有大國一旦樹立起低碳經濟的制度標識,就會迫使國際社會出現政見分野:順之者可向既有大國討要減排資金與技術,但須默認歐美制度霸權;逆之者即使經濟崛起也會被扣上“破壞人類共同家園”的罪名,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更無法改變現有國際秩序。對于經濟崛起與大國形象并重的中國來說,這不僅是一個要面子還是要里子的經濟問題,更是一個關乎中國崛起能否成功的戰略問題。中國海運界的榮衰與低碳規制緊密相關,這決定了中國的首要任務是爭取海運減排規制的參與權與決定權。由于這種爭取仍在現行國際秩序范圍之內,中國在國際海事組織之中又長期處于劣勢地位,從一開始就阻力重重,并面臨被西方國家利用制度優勢聯合打壓的風險。
此外,中國還面臨所謂“追隨戰略的碳交易陷阱”,即既有大國掌握著國際碳交易市場的主導權與發展方向,并為每一個對國際減排規制實施“追隨戰略”的博弈者預設了碳交易陷阱,借此吸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由于碳交易機制存在買賣雙方信息獲取不對稱的缺點,進入市場的碳配額頗受國際政治經濟大環境的影響,極易導致碳交易價格訊號扭曲。中國作為炭配額的賣方卻無定價權,在碳交易過程中極易蒙受經濟損失。
目前關于溫室氣體減排的討論,大都假定減排與經濟發展存在兩難。“碳陷阱”的出現是氣候問題政治化的必然結果。國際海事組織推行強制性減排措施,展示了國際組織在全球善治中握緊的雙拳,但其背后隱藏著既有大國制度性霸權的陰影。目前,國際海事組織在國際海運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進展與其終極目標還有一段距離。然而,海運業的“國際性”是不爭的事實,所以無論面對怎樣的結果,中國都需要為新一輪國際氣候談判作好充分準備,承擔海運減排責任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如何承擔海運減排責任更需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