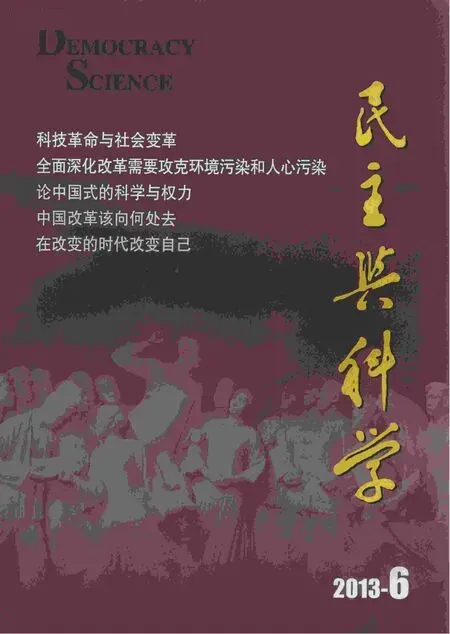用歷史眼光理解法治——讀《法治是什么——從貴族法治到民主法治》
■丁國強
李貴連《法治是什么——從貴族法治到民主法治》(廣西師范大學2013年版)對中國法治的歷史軌跡進行了重新詮釋。他沒有簡單用“人治”來概括中國古代社會的治理形態,這一概括不僅掩蓋了中國法治歷史進程的復雜性,而且也使得中國法治的源頭和傳統流變變得模糊不清。法治形成與發展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任何一種法律制度、法律思想都有其歷史基因和歷史脈絡。法治理性也是歷史理性。歷史法學代表人物薩維尼認為,法律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法律只能是歷史存在中的、在歷史中展開的法律。從語義分析上,中國古代的“法治”與西方RuleofLaw的法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古代社會完全與法治不相干。
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形態。法治的發展與人類文明的變遷緊密相關。法治是由民族生活創造的。沒有耐心用歷史眼光考察民族生活的人,是難以發現法治真諦的。中國的法治發展有著不同于西方的自我路徑。正如美國學者德克·博德所說:“中國法律的發展在許多方面都與其他文明的經歷大相徑庭。”“與其他大多數文明的成文法自豪并賦予其神意起源不同,中國法從一開始就是純粹世俗化的。”由此可見,通過梳理中國的文明過程來探尋中國法治的精神和治理經驗是有意義的。
李貴連這本書在從考察中國法治的歷史演變入手,對中國的法治形態進行了細分,從周代的貴族法治到現代的民主法治,中間經歷了君主法治、帝制法治、專制法治、官僚法治。這種探究對于發現法治的歷史邏輯是有意義的。貴族法治的實質是別親疏、殊貴賤、斷于禮。周禮是貴族的行為規范,禮治的核心是維護宗法等級制,用血緣鞏固統治,用族權加強政權,體現了用禮法和道德約束權力的精神,這是法治的初始形態。在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社會制度背景下,禮就是必須遵循的規則,是權力運行的依據。薩孟武說:“古代之所謂‘禮’乃包括‘法’在內。”可見,法學研究者大可不必諱言禮治。禮治是中國法治的源頭。建立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的西周“禮治”對于鞏固西周王朝發揮了歷史作用。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通過納仁入禮,以尋求新的治道。孔子并沒有用禮治來排斥法治,在他看來,禮治是法治的前提。“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儒家的仁學思想對于提高執政者的政治道德、執政藝術的強調,對于實施法治而言是必要的。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儒家重視禮治與法治的結合,兩者無法分離,互為因果。“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在從分封制向郡縣制過渡的時代,禮法并用確實不失為一種治理智慧。這也構成了中國法治最初的書寫方式和精神格局。
法家反對貴族特權,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法律應當體現平民的意志,打破貴族對土地、權力的世襲壟斷。法家把法律比作度量衡,具有平衡利益、規范行為、統一尺度、定分止爭的作用。法家消除了西周以來的天命神權、君權神授思想,法律是“吏民規矩繩墨”,是富國強兵、維護秩序的統治工具。法家重視法律的強制力,而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認為“賢人之治”、“圣人之治”是靠不住的,“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法家雖然正視人性中“好利惡害”、“趨利避害”的一面,但是將法治與禮治、德治對立起來,主張“以力服人”、“不務德而務法”,貶抑道德教化的作用,這實質上抽空了法治的道德基礎。僅僅靠嚴刑峻法樹立法令的絕對權威是缺乏精神資源的支持的。法家的法治主張是對分封和貴族宗法世襲制的修正和改造,也是郡縣制和官僚委任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貴族法治逐步解體的表現。韓非的“法不阿貴”思想閃爍著平民法治的光芒。但是,法家思想堅持法律工具論,將法、術、勢三者并論,過于強調國君的權勢,所謂“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從而忽略了法治的獨立價值。靠權術而維持政治權威,難以夯實政治根基。法家法治的重心是治吏治官,但是治官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治民。說到底,法家的法治只治臣民,不治君主,這使得其難以解決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只能埋下大澤鄉起義的種子。
秦漢以后以文治武功為目標的帝制法治/官僚法治逐漸形成。沒有規則之治,中央集權制大帝國的運轉是無法想象的。李貴連認為不能簡單將秦漢以后的中國古代社會稱為人治社會。與過去的貴族法治相比較,秦漢以后的帝制法治是一種相對進步的秩序構建。中國古代社會的官僚法治包括官員的選任、監督等都有獨到之處,并非乏善可陳,也不能用“法律儒家化”簡單概言。法家的治吏傳統一直貫穿秦漢以來的社會治理,維持著龐大帝國的運轉。把君主專制等同于人治顯然是忽略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運用法律治理國家的經驗。許倬云說:“秦始皇統一中國,將秦國已實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國,漢承秦制,大體未改,但是經過三四代的逐漸改革,專業的文官構成統治機構的主體。從此以后,中國的皇帝不得不與龐大的文官集團共治天下,內廷與外朝的區分,頗同今日企業組織董事會與公司抗衡相似。”中國古代政治運作中限制權力的方式與西方思維迥異,顯示著政治的復雜性和法治的歷史淵源。法治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而不是邏輯演繹的結果。考察中國法治歷程,要把法治作為歷史現象、歷史事實來對待。正如薩維尼所言,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法治演變的過程也是一個民族自我發展的理性過程。
中華帝國的官僚法治在明清之際就顯露出危機。黃宗羲主張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將批判的矛頭對準君主專制,希望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以使得天下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王夫之則認為皇帝視天下為一己一姓之私,只能陷入專制的怪圈,對官吏的制約也難以真正實現:“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要想真正管住權力,就必須把帝國變為立憲國。
李貴連認為,將法治的源頭歸為西方的觀點是錯誤的,法治不是西方的傳統,而是他們對傳統加以反省、批判和改造的產物,中間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弗朗西斯·福山說:一方面說“古代帝制中國沒有法治”,一方面又說“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發明了好政府。他們設計的行政機構是理性的,按照功能而組織起來,以非人格化標準進行招聘和晉升,這絕對是世界第一”。可見,在中國法制現代化道路上,概念引進、法律移植并不是唯一的路徑,如何融合中西法治思想,建構中國法治的思想體系,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像沈家本這樣的法律改革家強國救國的角度接受西方法治,當時的歷史條件使他無法擁有成熟的法治理論。李貴連認為,“這是20世紀初年法律改革者追求西方法治的死穴”。
今天我們建設法治中國,有必要好好回顧一下中國法治的歷史,用歷史眼光理解法治,以歷史素養把握法治規律,將法治理想建構在厚實的中國歷史和活生生的中華民族日常生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