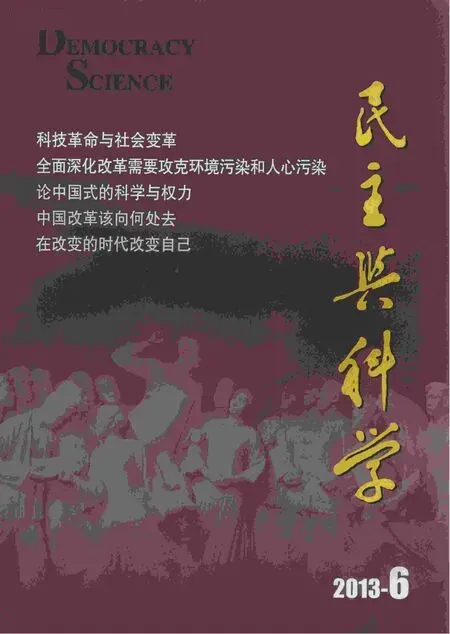是管理教學還是管制教師
■丁 輝
是管理教學還是管制教師
■丁 輝
在中學工作的朋友來跟我講了一件讓我啼笑皆非的事。他所任教的那所學校的教務處在每個班“安插”兩名所謂的“教務信息員”,直接定期不定期向教務處反映教師的教學情況。讓人匪夷所思的是,肩負這項特殊使命的兩個學生連班主任都不知道是誰,每學期末對“成績突出”的信息員進行精神和物質獎勵,也只公布所在班級不公布名單,實行嚴格的保密制度。
這是什么教學管理?
我在中學里工作有年,后來通過研究生考試,才結束了我的中學語文的教學生涯。說來也許會令世人錯愕:有相當多的中學老師其實是長年累月地在屈辱感中“討生活”。至于屈辱的緣由,千頭萬緒,我也不知從何說起,這里只能擇其要者而言之。教師的屈辱感一方面來源于良心或情感上的羞愧。在中學里任教七年,我為當地造橋修路等基礎設施建設“貢獻”了近3000元,而七年期間我的平均月收入不到500元。面對這樣的紛至沓來的以行政命令面目出現的不法侵害,教師們早已習慣了逆來順受。教師固然是軟弱的一類人群,同時也是道德意識強烈的一類人群,在為生存計不得不對行政權力低首下心的同時,難為人師的羞愧和屈辱像蔓草一樣在心里生長——如果教師在自己遭受不法侵害時甚至無力維護自身的權利,還能為文明社會培養出合格的公民嗎?光明網上一位中學老師的留言讓我幾欲淚下:“從教十余載,每過一個教師節,就會羞愧多一分!”
造成教師屈辱感的更為日常化的原因則是文章開頭提到的這種“非人性化”的教學管理,其實就是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馬格利特所說的“制度性羞辱”。
2001年,就是我在那所省重點中學、國家級示范高中工作的最后一年,學校不惜巨資為全校一百多間教室安裝了攝像頭。高科技使校領導只需坐在總控制室里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任何一位老師的教學全過程盡收眼底。說這樣就可以使“教育教學上一新臺階”,鬼才會相信,加強了對教師的人身控制(管制)倒是真的。即使真的能使教學呈現新氣象,如果這樣的“新氣象”竟然是以侵犯教師的尊嚴、剝奪教師的權利換來的,不也值得商量?可是領導有領導的道理。一個副校長說,只要你心里沒鬼,勤懇教學,你還怕人看?坐在前面講話的是領導,我們老師卻覺得是“秀才遇見了兵”!為了寫這篇小文,我特地聯系了原來的同事,得知教室里的大多數攝像頭還在,是不是還在使用,老師們也不得而知。但愿這些攝像頭現在只是個擺設。
我寫這篇小文的最近的緣由說來讓人喪氣,時隔十多年后,我再一次領教了高科技攝像頭的威力。我現任職的高校的每一個教室也裝上了攝像頭。原本因為“標準化考場建設”而安裝的攝像頭,卻如我們當初預料的那樣,果然附加了對教師和學生的上課進行全程監控的功能。好在學生和教師的抵制情緒已經引起校方重視,此事或會有一個圓滿的解決也說不定。
馬格利特的《正派社會》被稱為繼羅爾斯的《正義論》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有關社會正義的著作,正是在這本書里他提出了“制度性羞辱”的概念。馬格利特區分了文明社會和正派社會:“在文明社會里,人與人之間互相不羞辱;在正派社會里,制度不羞辱人。”很顯然,“制度性羞辱”比日常的人際羞辱對社會肌體的危害更大。人際羞辱帶有偶發性和暫時性;而制度性羞辱帶有長期性、一貫性。長期處于“制度性羞辱”的淫威之下,社會整體的羞恥感就會漸趨麻木,遭受羞辱也就沒有人會在意。我個人覺得,普遍存在的針對教師的“非人性化”的教學管理,勢必會使教師這一群體的靈魂漸趨麻木與冷漠。前文提到了教師“良心或情感上的羞愧”,這種以“羞愧”形式存在的理性和良知的自責和追問,恰恰是教育發展的希望所在。等有一天,連這種“羞愧”如果也不存在了,試問,我們的教育還有希望嗎?
我以前在中學的一位同事現在做了某民辦中學的校長,此君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其中“一把”是對教師“一天六次點名”,如此“加強教學管理”還讓不讓老師活?什么“辦學理念”,什么“管理經驗”,在主席臺上講起來“一二三四”,冠冕堂皇,其實業內人士都心知肚明,所謂“經驗”,就是兩個字:死揪(應按江淮方言讀qiu,上聲),不僅“揪”學生,而且“揪”老師!
前總理溫家寶說:“要讓中國人活得更有尊嚴。”我相信,如果一個國家,連教育和教師都沒有尊嚴,說這樣的國家在國際上多么有尊嚴,乃是欺人又自欺的徒作大言而已。世界人民也不會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