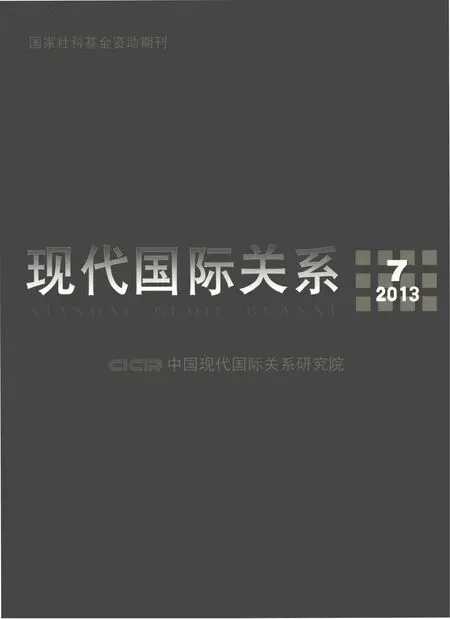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與戰略回應
王 輝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崛起”效應日益體現在中美關系當中。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系跌宕起伏,主要是由于美國對華政策前后不一而導致的。美國對華戰略呈現較大的不確定性,與美對中國的認知有關。對美國而言,“中國崛起”既是一個客觀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主觀認知的過程。無論這種“認知”是否與現實情況相符,都是其判斷和行動的基礎。冷戰后美國內圍繞“中國崛起”的主要爭論集中于:中國是否能夠崛起?中國崛起后是否會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事實上,中國能否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并不是中國政府單方面能夠決定的,需要美國的理解和國際社會支持。美國對中國的認知是中國崛起的重要外部環境,因此了解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對于準確把握美國對華政策的戰略意圖以及認識制約著中國能否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環境極為重要。
一、“中國威脅論”與對華“接觸戰略”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關注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國威脅論”興起之后。防止歐亞大陸出現一個挑戰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一直是二戰以來美國對外戰略的核心。冷戰時期,美國長期關注的是來自蘇聯的威脅,中國并不是美國關注的首要對象。冷戰結束后,美國把中國當作蘇聯意識形態的替代者,兩國在人權和政治制度上的分歧迅速上升為美中關系的主要問題。當時,認為中國只是個“過渡性政權”的“崩潰論”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①Winston Load,“China and American Beyond the Big Chill”,Foreign Affairs,Fall 1989,Vol.68,No.4,p.6.1992年以后,中國不但沒有步蘇聯后塵走向解體,而且保持了經濟高速增長,這種出乎意料的發展使美國精英陷入了認同上的“情感沖突”。1992年9月,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羅斯·芒羅發表題為《醒來的龍:亞洲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堅定地走上了一條經濟飛速發展、軍事上顯露鋒芒的道路,這將在整個亞洲和全世界引起反響,將對美國基本的經濟和戰略利益提出重大挑戰。在可預見的將來,美中關系必將經歷艱難、復雜和危險時期。②Ross H Munro,“Awaken Dragon: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Policy Review,Fall 1992,No.62,p.15.此后,“中國威脅論”思潮在美國逐漸興起。1996年,中國在臺灣海峽舉行的軍事演習被美國視為以武力挑戰其霸權,不僅對“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而且對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提出了挑戰”。①Minny Roy,“The‘China Threat’Issue:Major Arguments”,Asian Survey,August 1996,Vol.36,No.8,p.769.1997年,伯恩斯坦和芒羅出版《即將到來的中美沖突》一書,認為中國的目標是取代美國成為亞洲的首要大國,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價值觀少之又少,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沖突將是中美關系中最可能呈現的狀況。②[美]伯恩斯坦和芒羅著,隋麗君等譯:《即將到來的中美沖突》,新華出版社,1997年,第17頁。“中國威脅論”的消極立場由此擴散到整個美國社會,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構成了壓力。
在美國,也有質疑者認為“中國威脅論”夸大了中國的潛力。他們指出,盡管中國擁有核武器和運載火箭,但其科技仍落后世界平均水平10-20年。即使中國以兩倍于美國的速度持續增長,到2010年達到美國 GNP的一半,但人均水平也只及美國的1/10。③“So That the Sky Won’t Fall Down”,The Economist,June 18,1988,p.33.1996年沈大偉在《華盛頓季刊》發表題為“中國軍事:真老虎還是紙老虎?”的論文,提出在評估中國軍事實力時要采取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幻想中國善良和夸大中國威脅的憂慮都會歪曲現實和破壞局勢的穩定。他認為,“時下針對中國現代化作出的估計欺騙多于現實,中國威脅論既不準確,也是不負責任的。中國軍隊現在和可預見的將來都不具備直接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挑戰的能力。”④David Shambaugh,“China’s Military:Real or Paper Tige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1996,p.20.約瑟夫·奈也指出,“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能成為挑戰美國霸權的力量,取決于其經濟增長和政治凝聚力。即使幸運之神眷顧,中國仍將任重而道遠”。⑤[美]約瑟夫·奈著,劉華譯:《美國注定領導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3頁。
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尤其成為克林頓政府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克林頓任內,美國決策層內部也出現了“遏制派”和“接觸派”兩種不同聲音,“中國威脅論”并沒有轉化成美決策層的認知。當時中美實力差距巨大,克林頓政府整體上對“中國崛起”持懷疑態度。美沒有把中國視為首要安全威脅,但傾向于認為中國是一個對現狀“不滿”的大國,并認為中國是美霸權的潛在威脅。“中國崛起”后是否會挑戰美國霸權并不是美關注的焦點,采取什么方式使中國變成一個對現狀滿意的國家才是美國的主要關注。⑥[美]江憶恩:“中國參與國際體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7期,第25頁。克林頓政府最終選擇了較為務實的對華“接觸政策”。然而,單純的“接觸”并不能確保美國利益的實現,采取適當的“遏制”也是必要的。美日兩國政府首腦1996年發表《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宣布美國在日本保持10萬人的駐軍;1997年9月發布《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臺灣海峽被列入“周邊事態”防衛合作的范圍。至此,克林頓政府形成了“接觸加遏制”的對華政策框架。
克林頓政府在解釋對華政策時指出,接觸戰略所帶來的風險是微小的,美國對中國的實力優勢巨大,在未來幾十年中國不可能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⑦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2,Vo1.81,No.4,p.20.“沒有中美之間的合作,亞洲安全和穩定面臨的任何威脅都不可能得到全面解決。維持地區穩定是中美合作的任務,也是中美關系的戰略基礎。”⑧Secretary of Defense William Perry,“The Sino-U.S.Relationship and Its Impact on World Peace”,Adress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Beijing,China,October 18,1994.“設法孤立中國顯然是行不通的,我們無法切斷中國與外界的經濟聯系,反而會使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政策受到孤立。最重要的是,選擇孤立中國而不是同它接觸的做法會使世界變得不太安全,會使世界變得更加危險,會削弱美國安全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⑨Samuel R.Berger,“A Foreign Policy Agenda for the Second Term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Speech on Foreign Policy at CSIS,March 27,1997,http://clinton2.nara.gov/WH/EOP/NSC/html/speeches/032797speech.html.(上網時間,2012 年12月10日)美國在“臺海危機”之后強化美日同盟關系,運用戰略優勢同中國進行一種基于實力地位的接觸,并謀求最大限度地鼓勵中國采取合作政策對待地區秩序。
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美,中美關系得到重新定位,雙方“致力于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1998年克林頓政府先后出臺《東亞太平洋安全戰略報告》和《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兩份安全戰略報告。這兩份報告是克林頓政府對華安全戰略比較完整的闡述。隨后,中美雙邊交流迅速升溫。1998年6月克林頓總統訪華,就臺灣問題發表了“三不”講話,兩國還簽署了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協議。克林頓政府任期最后一年,美與中國達成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
二、“利益攸關方”與美中反恐合作
受“9·11事件”的影響,小布什執政時期,美國對中國的認知經歷了從“戰略競爭對手”到“利益攸關方”的轉變。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實力上升,“中國崛起”所引發的“不確定性”再次成為美國關注的焦點。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提出,如果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增長中心,它幾乎肯定會將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力量。隨著中國力量的增強,中國和美國勢必成為對手。①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p.4.
小布什在競選時就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認為中國是美國在亞洲的關鍵挑戰。②“George W.Bush Foreign Policy Speech”,November 19,1999,http://www.pbs.org/newshour/shields&gigot/november99/sg_11-19_bush.html.(上網時間:2012 年12 月12 日)2001年4月,美國EP-3軍用偵察機與中國軍機在南海海域上空相撞。美國軍方認為,中國的真正意圖是要否定美國進入從西朝鮮灣到南中國海這一大片海域的權力。撞機事件進一步強化了小布什政府對中國的判斷,認為美國面臨的首要威脅就是像中國這樣“擁有可怕資源的軍事對手”。③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2001,p.1.與此同時,美國智庫出臺多份戰略報告,主張加強對中國的遏制。2001年5月,蘭德公司在《美國與中國:美國新戰略和軍事力量》的報告中指出,目前一個重大的變化是中國正在崛起為一個大國,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計劃和它在東亞地區的作用得到加強,這將對美國的戰略和軍事力量產生重大影響。④RAND Corporation,“America and Asia:American New Strategy and Military Forces”,May 15,2001.
2001年小布什上臺初期,把新保守主義的實力外交理念作為其對華政策的出發點。美認為,實力是美國國家安全和利益最可靠的保障,也是美國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的主要手段,因此無論中國如何崛起及崛起的意圖是什么,美國都必須保持對中國的絕對實力優勢。小布什醞釀調整對華戰略,目標是確保中國沒有能力挑戰美國霸權,因而提出了“預防性遏制”對華戰略構想,旨在防止中國成為美國的戰略對手。⑤吳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戰時代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5頁。2001年美國政府《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提出,美國的目標是促進國際和平、維護自由和鼓勵繁榮。維持國際和平必須依賴美國的領導地位。要確保美國領導地位不受挑戰,美國需要在東亞、波斯灣和歐洲等關鍵地區維持有利均勢,通過無可比擬的軍事優勢阻止其他國家展開與美國的軍事競爭,在必要時候將美國的意愿強加給任何對手。⑥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2001,p.15.不久小布什政府批準了大規模對臺軍售。⑦Shirley Kan,“Taiwani Major:U.S.Arms Sales since 1990”,CRS Report RL30957,September 25,2008,http://www.fas.org/sgp/crs/weapons/RL30957.pdf.(上網時間,2012 年12 月15 日)
然而,“9·11事件”后美國對安全威脅來源的認知發生轉變。美國國內迅速形成共識,即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最緊迫威脅不是來自日益強大的中國,而是來自猖獗的國際恐怖主義。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優先目標。2001年10月,小布什在上海舉行的APEC領導人會議上,把中國稱為反恐伙伴,提出把致力于發展“坦誠的、建設性的合作關系”作為中美關系的基本框架。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我們歡迎強大、和平與繁榮中國的出現”。⑧The United States,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September 2002,p.26.這表明美實際上放棄了以中國為美戰略對手的立場。反對恐怖主義和防擴散成為中美關系新的戰略基礎。在此之后,兩國在反恐、朝核、經貿等諸多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國對于“中國崛起”的關注被全球反恐戰爭所取代,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也讓美國把關注重點轉向了中東地區。
到2005年,受“新帝國主義論”和伊拉克戰爭的影響,美國在全球戰略格局中的影響力下降,中國崛起速度“超出預期”,在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尤其明顯上升。此間,中國與東盟2003年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歐盟開始討論對華售武解禁問題,中國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臺海問題的主導權正從美國轉向中國。①袁鵬:“中國崛起:美國的評估及戰略應對”,郝雨凡、趙全勝主編:《布什的困境》,時事出版社,2006年,第185頁。這些因素明顯刺激了美國。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中國威脅論”在美重新抬頭。美國有學者提出中國崛起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美國政府必須重視,呼吁美國的亞太戰略應有所調整,并主張美國必須在政治、經濟和安全方面付出雙倍的努力來淡化中國的影響。②Dana R.Dillion,John J.Tkacik,Jr.,“China and ASEAN:Endangered American Primacy in Southeast Asia”,Backgrounder,No.88,October 19,2005,http://www.pdfio.com/k-708394.html.(上網時間,2012年12月16日)美國將會因對東亞合作進程的無動于衷而承受高昂的代價。③Bronson E.Perciva,“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Hearing on“China’s Global Influence: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July 22,2005.但這一時期美國仍然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美國在全球和地區層面的諸多問題上不能沒有中國合作。
2005年9月21日,美副國務卿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關于中美關系的講話中提出:今天的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中國雖未實行民主,但也不認為自己正與全球民主制度進行最后搏斗;中國雖實行重商主義,但并不認為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斗爭;最重要的是,中國認為自己的前途并不取決于廢除現行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中國應成為現存國際體系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與美一起構建未來國際體系。④Robert B.Zoelliek,“A Resurgent China:Responsible Stakeholder or Robust Rival?”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09th Congress,May 10,2006,Serial No.109-225.這一提法明確了美國希望與中國合作以共同應對挑戰的期待。此后,“利益攸關方”被美國政要不斷引用,并且寫入了2006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和《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美國政府的正式文件。⑤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ce Review Report,February 6,2006,p.29;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rch 2006,p.39.這意味著“利益攸關方”成為美國官方認識“中國崛起”的關鍵詞。
“利益攸關方”的提出,表明美國對中國融入國際秩序的承認。美國認為中國已經融入了由美主導的國際秩序,因而表示要“鼓勵”中國在現有秩序框架內追求國家利益,美并謀求盡力影響中國崛起的進程和結果。由此,“中國機遇論”和“中國責任論”隨后在美興起,中美雙方努力構建“建設性的合作關系”,2005年啟動年度中美戰略對話,2006年啟動年度戰略經濟對話,開啟了中美對話機制化的大門。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美國對其在東亞的角色和地位較為滿意,因為中國擔任東亞地區領導角色的意愿不強,東亞地區大國之間仍存在相互戒備和猜疑心理,大部分東亞國家“歡迎”美在亞洲安全中的角色。美國還是東亞國家產品的最終市場。
三、中國崛起與亞太“再平衡”戰略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導致了美國對自身衰落的過度擔心。美國精英普遍認為中國GDP總量將在21世紀前半期超過美國,這是自19世紀末美國經濟規模超越英國以來,從未面對過的狀況。金融危機將使美國在未來幾年甚至十年內都難以為其與中國越來越激烈的軍事競爭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⑥Aaron L.Friedberg,“Implications of the Finacial Crisis for the US-China Rivalry”,Survival,August/September 2010,p.48.美國及其盟國面對的將會是一個越來越富有、技術上充滿活力和軍事上強大的中國,而中國政府依然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⑦Michael Green,“Get Asia Right”,Asia Policy,No.7,January 2009,p.5.2009年9月,美國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演講中提出“戰略再保證”概念,指出“美國歡迎中國作為一個繁榮昌盛的大國的出現,但中國必須向其他國家保證,中國的發展及其在全球日益增長的作用將不以他國的安全與福祉為代價”。⑧James 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September 24,2009,http://www.state.gov/s/d/2009/129686.htm.(上網時間,2012年12月18日)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標志著美國將中國“鎖定”為主要戰略對手。然而,“戰略再保證”的概念卻未在美國取得廣泛共識。
2009年以來,隨著美國民眾對自身經濟增長和失業率的日益關心,美國越來越關注中國崛起對美國經濟的沖擊,指責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國際經濟不平衡的根源;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正在導致美國就業崗位的流失,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使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在對外貿易高順差、匯率管制、知識產權等方面給美國造成了重大損失。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在2010年的年度報告中甚至認為,“中美經貿關系的不平衡給予中國增強和促進其經濟、軍事和政治權力所需要的金融資源和技術能力”。①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0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November 2010.一個由威廉·佩里和斯蒂芬·哈德利領導的獨立專家小組認為,中國的崛起是未來20年可能出現的對美國持久國家利益最嚴重的潛在威脅之一。②Joint Statement of William J.Perry and Stephen J.Hadle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 on“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Independent Panel”,Washington,DC.,July 29,2010,p.2.關于中國崛起的討論,還從國家關系層面上升到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層面,認為中國經濟的成功削弱了美國發展模式的影響力。奧巴馬總統在2010年1月的國會演講中表示“美國絕不接受世界第二”。奧巴馬政府在同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高度強調實力建設的重要性,美國要重振全球領導地位,就必須從源頭上重建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報告指出,美國必須重振經濟,經濟繁榮是“美國實力的源泉”,是美國軍事、外交和發展援助的支撐,更是美國發揮影響力的關鍵;美國國家戰略的重點必須放在“重振美國領導地位上,以使我們能夠在21世紀更有效地促進美國的利益”;美國國家安全取決于軍事實力、經濟競爭力、道義領導力和對國際體系的塑造力。③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p.7.
2010年“天安艦”事件后,中美在一系列安全問題上分歧加劇,中國在界定核心利益問題上表現出更加堅定的姿態,美國據此認為中國的戰略轉向已經開始,將改變過去30年來以維護中美關系穩定為軸心的大戰略,并認為“基于中美間的實力差距正快速縮小的判斷,中國可能采取一種更加主動和自信的外交政策。”④Bonnie S.Glaser,“A Shifting Balance:Chinese Assessments of U.S.Power”,Craig S.Cohen,ed.,Capacity and Resolve:Foreign Assessments of U.S.Power,Washington,D.C.:CSIS,June 2011,p.8.美國卡內基基金會中國問題專家史文在“解讀過于自信的中國”一文中稱,中國經濟越來越成功,經濟實力日益擴張,特別是在全球衰退之中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中國據此認為全球重心從西方轉到東方、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強國也隨之衰落,所謂的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只是一種掩飾,中國的實力強大之后改變了對外行為的基本原則,擴大了利益范圍。⑤Michael D.Swaine,“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4/04/china-s-assertive-behavior-partfour-role-of-military-in-foreign-crises/a6is.(上網時間:2012年 12月18日)約瑟夫·奈也認為,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誤判國際形勢,拋棄了“韜光養晦”。⑥Joseph Nye,“China’s Century is Not Yet Upon Us”,Financial Times,May 18,2010.一些學者更是對美國對華政策提出深刻質疑,認為美國決策層長期以“融入”的思路來應對中國崛起,其結果是促進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卻沒有導致中國政治體制“民主化”。日益強大的中國越發自信,開始尋求取代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美國的亞洲盟國高度關注美國在東亞的投入。對美國的盟國而言,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意味著一個削弱的美國不能繼續維持前沿軍事存在,不再是地區和平穩定的最終保障者。為阻止戰后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及其秩序的瓦解,美國必須回應中國的挑戰,展現強大實力,持續介入東亞地區事務。⑦Michael D.Swaine,“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4/04/china-s-assertive-behavior-partfour-role-of-military-in-foreign-crises/a6is.(上網時間:2012年12月18日)
以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為標志,美國開始將其戰略重心重新轉向西太平洋地區。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指出亞太地區是美國的未來關注重心,美國將在東盟、亞太經濟合作論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及東亞峰會等地區多邊框架內尋求發揮更大作用。⑧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p.10.自美國宣布“重返”亞太以來,美國綜合運用經濟、軍事、外交、援助等手段,與中國展開有關亞太主導權的全面競爭。美國通過外交表態、聯合軍演、軍事援助等多種形式逐漸加強了對南海問題和釣魚島問題的介入力度。美公開要求中國和東盟集體談判解決南海領土爭議,接受東盟旨在約束中國的“南海行為準則”;認為中國設立三沙市是謀求對南海強勢擴張。①Oriana Skylar Mastro,“The Sansha Garrison:China’s Deliberate Escal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_ESCA_bulletin5.pdf.(上網時間:2012年12月18日)美并把中國的海上維權解讀為中國在利用強大實力“恐嚇”周邊其他國家,中國的“野心”是要控制西太平洋海域。美國國防部在2013-2017年度的戰略預算指導文件中稱,盡管美國的國防預算將會大幅削減,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依然會繼續保持并得到加強。②DepartmentofDefense,“DefenseBudgetPrioritiesand Choices”,January 2012,p.5.2012年1月發布的“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新軍事戰略文件提出了針對中國“反介入”戰略的“空海一體戰”概念。③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 2012,p.4.隨著中美在東亞地區競爭的日益激烈,戰略較量、第三方的不確定性等因素使中美爆發直接沖突的風險增大。
結 語
綜上所述,冷戰后美國內部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充滿爭論,大體上經歷了從懷疑到警覺,從警覺到焦慮的過程。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整體上偏向消極,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是挑戰者和競爭者,擔心中國走非和平崛起之路,對中國和平發展憂心忡忡。這主要源于美國根深蒂固的戰略文化和意識形態偏見。在戰略文化方面,美國主要是根據對手的實力而非意圖作為判定威脅的標準。作為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家,美國要防止以任何形式崛起的挑戰者出現,以確保其支配地位不受挑戰。從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演變中可以看到,美國實力的優勢地位是一定時期內中美關系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冷戰后中美關系整體穩定很大程度上與兩國實力存在較大差距密切相關。隨著兩國實力差距的接近,美國越來越明確地把中國“鎖定”為唯一的競爭對手。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始終是美國外交政策追求的長期目標。冷戰時期,與蘇聯多年的意識形態競爭進一步強化了美國人對不同意識形態的偏見和敵視。美國始終“從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勝利這一角度來認識中國”,本能地支持向中國輸出美式民主。④[美]韓德著,項立嶺、林勇軍譯:《中美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國與中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第65頁。兩國在價值觀念和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美國對中國進行客觀認知。“中國威脅論”在美國長期存在較大影響,并非是出于事實的觀察,而主要是出于主觀認知的偏見。
從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與對華政策的關聯來看,“認知”并不能簡單地決定政策。美國的外交行為、政策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除了外部國際環境的變化,內部的認知差異、黨派競爭和民意取向等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縱觀冷戰后以來的美國對華政策,克林頓政府對華接觸政策是以中美實力差距為前提的,小布什的對華政策明顯受到美國反恐戰略需求的影響,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則與中國崛起效應密切相關。從美國對華政策的實踐看,美國整體上缺乏遏制中國的有效手段。這主要是全球化的時代特征所決定的,中國已經深度融入了國際體系,中美利益高度相互依賴限制了美國完全用傳統方式應對的戰略選擇。中美關系已不是單純的“零和”博弈關系。
盡管美國宣稱其亞太“再平衡”戰略并非針對中國,但美國面臨的挑戰是,在加強在亞太的軍事存在、鞏固同盟體系、建立新的伙伴關系的同時,如何消除中國方面對美國謀求戰略包圍和遏制中國的擔憂。美國的戰略調整使中美兩國陷入一種“負向認知循環”的危險,造成雙方戰略猜疑日趨嚴重。美方雖然口頭承諾歡迎中國和平崛起,卻無法真正做到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從未來的趨勢看,美國不得不與中國分享權力,這是一種難以避免的戰略走勢。中美在未來能否對對方的地位形成較為一致的認知,是中美關系發展的關鍵。正如基辛格所言,世界秩序有賴于每一個參與者都支持的結構,在“世界重新平衡的時代”,美國是否應該考慮建立奠基于各國共同利益的“太平洋共同體”?“太平洋共同體”顯然有別于冷戰時期面對直接威脅時,奠基于共同文化與價值觀的“大西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