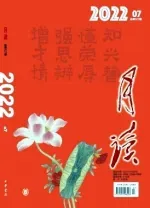說癮道戒
□ 阮直
一般認(rèn)為人們心里最難戒的“癮”應(yīng)該是毒癮,所以才有強制戒毒一說,其他的癮再大也不必用外力強制去戒。比如酗酒成性升格為酒鬼了,喝多了就耍酒瘋,傷了朋友關(guān)系,傷了家庭和睦,可從有酒那天起,無論酒鬼、酒仙、酒神多么成群成伙,哪朝哪代也沒成立個戒酒所。唯獨毒癮難戒,就算要臉、要尊嚴(yán)的人一旦染上毒癮就不再要臉了。如果他還想要命,就需要強制戒毒。戒毒所在我看來就如被監(jiān)禁、管制、雙規(guī)了,即便這樣強制戒毒,毒癮也難戒成。
有人為官也有官癮,但還沒聽說有人在戒官癮的,更沒見到戒官癮的人被弄到一個集中的“所”里,被管制,被改造,當(dāng)官癮消退之后再回歸自由的。所以,毒癮讓人恐怖,而官癮就沒人懼怕了。甚至還有人把“官癮”誤讀為“進取心”,是有志者的行為方式。
想當(dāng)官只要不成癮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成癮。就像被稱為毒品的可卡因、大麻,用到藥品與醫(yī)學(xué)上還是良藥呢。當(dāng)官更是如此,當(dāng)人民公仆那樣的官就不會成癮,今天可以為官,明天可以為民,不當(dāng)官還可以干別的,甚至比當(dāng)官干得還優(yōu)秀,就不會染上官癮。
當(dāng)官就怕成癮,染上官癮的人,就不愿意干事,愿意“干人”了。以古代當(dāng)官的最大舞臺——宮廷為例,凡是往父子、兄弟、叔侄種種親情的兩肋上插刀的人都是官癮發(fā)作時惹的禍。中國古代宮廷的“中心任務(wù)”,要我概括那就簡單了,無非是按宗法接班的規(guī)則,分官癮發(fā)作期與官癮不發(fā)作期。接班人官癮不發(fā)作,等待最高首長的自然死亡,順理交接班就是老百姓之福;接班人一旦官癮發(fā)作,就想提前“取而代之”,或不該接班的人覬覦了皇位,那就是百姓之禍。
毒癮的“毒性”是揮霍了自己的積累,毒垮了自己的“身體設(shè)備”,再鬧大了,就是偷、搶,最后成了犯罪分子被抓進監(jiān)獄。可官癮發(fā)作的人,麻煩就大了。他們總是在暗算別人,利用別人的權(quán)力,借用他人的背景,使出卑鄙的謀略,投入巨額的金錢,自己墮落還不算,更會拉一大串人下水。當(dāng)下的腐敗分子之所以腐敗,就是有人要花錢買官,有人就收錢賣官了。
官癮大的人幾乎都有腐敗意識,他們看中的是當(dāng)官的權(quán)力與待遇,如果當(dāng)官也像北歐諸國那樣“官不聊生”時,人們就不會有官癮了。之所以那么多的人有官癮,就是當(dāng)官的權(quán)力還沒有被關(guān)到籠子里,公權(quán)可以私用。當(dāng)一個國家里的公民都是官癮極大的人,這個民族離墮落就不遠(yuǎn)了。就像清王朝后期,只要讀了幾年書,家里有幾個閑錢的都想買個官來當(dāng)當(dāng),即便是虛職,也視若稀世珍寶。

1843年西方版畫《華府中的晚宴》。畫中清朝官員們大吃大喝,后面還有人在表演節(jié)目,極盡鋪張,難怪清朝有錢人都愿意買個官做。但正是因為“官癮”的大,導(dǎo)致了清朝的衰落和滅亡。
另外官癮大的人也不會是大智慧的人,把自己的價值都托付給一個強者的“授封”,要么是自身的無能,要么就是強者太強了。就像專制獨裁時代能讓李白和杜甫那樣的天才也未能免俗,他們也半輩子都等待皇帝的召見、下旨,也想弄個一官半職,無奈官癮蓋不過他們的才氣與智慧,在皇權(quán)面前他們表現(xiàn)不出媚態(tài)與臣服,以為皇帝崇拜了自己的才智,就能給個官當(dāng)當(dāng),這其實還是官癮不夠大,心中最上癮的還是自己的智慧與才華。那就沒辦法了,你以為皇帝不知道你真正上癮的是什么嗎?手持毒品的人永遠(yuǎn)知道要把毒品賣給那個上癮最大的人才會“利益最大化”。
戒毒癮自有戒毒所,戒官癮就要打造能把大大小小的公權(quán)力關(guān)進去的籠子。當(dāng)為官這件事兒成了苦差,誰還上癮,如果僅僅為了祖國榮譽、為了民族驕傲、為了人們的幸福為官上癮,那就是一件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