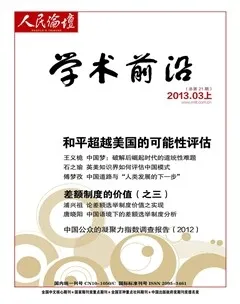中國夢:破解后崛起時代的道統性難題
摘要 中國與世界關系的主題,正從“崛起之中”向“崛起之后”轉變;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本質,正從“世界的中國”向“中國的世界”轉變。中國外交的難題從回答崛起過程中“我不是什么”、“我不做什么”,向崛起之后“我是什么”、“我要什么”轉化。對中國崛起的質疑,滋生層出不窮的“中國威脅論”,揭示了中國崛起的道統性挑戰。應對挑戰的關鍵是,中國與世界在互動建構中以中國夢實現世界夢,通過自身文明轉型引領人類文明轉型。
關鍵詞 崛起 復興 中國威脅論 道統性 中國夢
盡管中國崛起是正在進行時,但是我們的思維必須超越崛起,及早規劃崛起之后的國際訴求。從有形力量的關鍵指標GDP總量看,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趕超的目標便集中于美國。中國的發展態勢很難再用“崛起”這一外來感受來描述,尤其是不久的將來超過美國的GDP后,中國與世界面臨的大國關系集中于中美關系,主要挑戰集中于因應美國霸權,主要目標是從“世界的中國”向“中國的世界”轉變,即中國被世界塑造向中國塑造世界轉變。超越崛起,聚焦復興,進入后崛起時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邏輯從融入世界、與國際接軌,轉變為中國與世界互動建構。這就要求中國積極去建構世界的中國觀,并在此過程中再塑中國的世界觀。
中國的崛起與世界的轉型相伴生。國際輿論擔心中國崛起后如何使用崛起的實力,美國則擔心自身的老大地位被中國超越。一些國內輿論也將中美關系列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認為其本質是“老大”與“老二”的關系。其結果,導致國內外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質疑聲音頻起,“中國威脅論”從未來時變成進行時。其實,中國的發展態勢,只有超越崛起,才能超越威脅。超越崛起,聚焦復興,為時代所呼吁。中國的復興,如何為人類永續發展之所需,世界各國之所期,國際社會之所愛,成為崛起之后對中國的巨大考驗。
本文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解讀中國崛起的世界使命,剖析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根源,提出中國崛起之后的道統性時代命題,提倡以中國夢實現世界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位一體”。
解讀中國崛起:歷史使命源于崛起的特殊性
對于中國崛起,國內外視角不一,中國與世界的誤解往往由此產生。中國人往往從崛起過程看問題,并歸因為崛起不足所致——將強未強;外界多從崛起結果看問題,并推測崛起之后的情形——擔心中國威脅。中國崛起,既具有歷史上大國崛起的共性,比如崛起的硬實力滋生下滑的軟實力,更具有中華民族復興三方面的獨特個性:
其一,中國崛起,是唯一非宗教國家的崛起,不以西化為目標,且是非基督教國家的崛起。這就是近代九個大國崛起案例的反例,引發“中國威脅論”泛濫于世,本質上圍繞中國是否為他者、另類而展開。因此,指望通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邏輯應對,不能有效解答此難題。正如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從基督教著手,西方世界的身份認同聚焦于所謂的民主國家,起源于基督教、形成于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普世價值觀,帶給當今西方話語霸權下中國國際身份的悖論:轉型與普世價值接軌,成為所謂國際主流社會的一員;對抗普世價值,成為國際社會的他者。如何打破這一悖論?
其二,中國的崛起,是唯一未被西方殖民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傳統上是文化共同體,而非歐洲式的民族國家。中國崛起是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不是民族國家的邏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能解釋的。這是西方難以理解中國和平崛起的邏輯、產生各種“中國威脅論”的認識論根源。正因為中國歷史上未被西方成功殖民,導致西方既搞不懂也搞不定中國,這是“中國威脅論”的現實根源。
其三,中國的崛起,是唯一既要復興古老文明,又要復興“西方另類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思潮的崛起。這樣,在美國有“共產黨中國”崛起威脅論,在歐洲有中國人權問題的糾纏。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看,中國崛起事關世界社會主義事業之最終興衰,并集中體現為對形成中的“中國模式”的可持續發展的檢驗。
這樣,中國崛起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崛起的復雜性、艱巨性,也預示著中國崛起的歷史使命。中國崛起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大國崛起,更是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正在顛覆“西方中心論”世界觀。其結果是,普世的成為地方的,神圣的變成虛偽的,自我變成他者。過去,西方人認為,中國力量上(GDP)、技術上(R&D)乃至制度上(中國模式)都在趕超西方,但道義上無法企及西方,因為不能提出像西方那樣的普世價值體系。現在,“中國軟實力威脅論”又在西方蔓延,認定中國威脅的真正源泉是走出西方之外的替代選擇之路,集中體現在對西方普世價值神話的挑戰上。融入、拒斥還是包容西方普世價值觀,成為中國崛起的歷史性挑戰;剝去“西方中心論”神話,還原世界多樣性,成為中國崛起的時代考驗;以自身文明轉型推動人類文明轉型,成為中國崛起的偉大歷史使命。
解讀中國威脅論:崛起為何與威脅劃等號
老子在《道德經》中寫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來,一切事物效法的對象,最后的指向是“道”,而“道”則無所效法,它以自身為法則。老子這句話給人最大的啟發在哪?就是說你不能用理念的、名稱的一套東西來代替世界本身。所謂“天”,是一種空間概念——基于現實,折射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所謂“地”,是一種時間概念——基于歷史,折射事物存在的合法性;所謂“道”,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概念——基于未來,折射事物存在的合目的性,即事物的自身本質與存在形式的匹配性。老子的思想在近代歐洲思想家中得到了呼應,只不過少了一個“合理性”維度。比如,康德指出:“就其當然而論,人類歷史就是合目的的;就其實然而論,人類歷史就是合規律的。”①可見,東西方理念相同,只是形式有所不同。
受此啟發,筆者認為,和其他領域一樣,國際關系也存在明顯的“二律背反”,對應三種矛盾律:狀態律——無序—有序;力量律——分與合(平衡與失衡);意志律——同化與異化(同質性與異質性)。②對照這種“三位一體”式的分析框架,中國威脅論有三個典型。
狀態:中國威脅現行秩序,妨礙既得利益。典型的表現是,周邊國家擔心中國成為其第一大貿易伙伴后,會導致全方位地對中國依賴,產生不安全感,因此請美國重返亞洲對中國崛起予以平衡。一些周邊國家甚至擔心中國將來恢復朝貢體系,自己成為中華帝國的依附。
力量:中國威脅地區與全球勢力均衡。典型的表現是,鄰居大國的中國軍事威脅論,擔心中國威脅地區與全球勢力均衡,導致地區、國際體系失衡和不穩。這種擔心,為美國重返亞洲提供了借口。
意志:中國威脅其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典型的表現是,歐洲人很擔心中國消耗太多的能源、資源,影響全球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故而通過氣候變化、節能減排約束中國的生產方式,同時擔心中國會成為又一個美國,思維方式與歐洲不合拍,很難相處,擔心中國傲慢。
具體而言,由于歐洲將自己定位為一種觀念力量,歐洲人心目的“中國威脅論”有三種不同版本。
中國威脅論I:中國發展不可持續,因為中國沒有像歐洲那樣的核心價值。因而對中國的人權、民主甚為關心,希望通過接觸中國而塑造、輸入核心價值體系。
中國威脅論II:中國存在自己的核心價值體系,但是不能普世化,并且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中國于是成為西方普世價值的公敵。歐洲對華接觸,就是要將中國納入西方普世價值體系。
中國威脅論III:中國提出類似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如“中國模式”所概括的,并且極力推廣,取代歐洲的統治地位。正如彭定康所言,中國的潛在威脅,不在于其廉價的出口貨物,而在于民主的滅亡,在于中國宣揚著不需要西方的民主也可以致富的理念,這是對西方最大的威脅。③歐洲人于是擔心“中國統治世界”,主張西方須自強,繼續占據道德高地。④
在這種話語霸權體系下,中國便處于“三元悖論”困境:無論有無核心價值,無論如何對待普世價值,都成為歐洲的威脅。
與此對應,合理地崛起、合法地崛起、合目的地崛起,成為中國崛起的三大挑戰。中國如何從狀態、力量與意志三層面給亞洲乃至全球帶來秩序、平衡、和諧,成為對中國崛起的三大考驗。
從說“不”到說“是”:中國崛起的道統性
中國崛起的三大考驗,折射出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本質正從“世界的中國”向“中國的世界”轉變。由此,中國外交的難題從回答崛起過程中“我不是什么”、“我不做什么”,向崛起之后“我是什么”、“我要什么”轉變。這是中國積極建構世界的中國觀以及中國的世界觀的過程。一言以蔽之,國際上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和國內流行的“中國老二論”,都深刻表明,國內外的質疑集中于中國崛起的道統性。
道統者,認同、正統、弘道之謂也。如何對待自身歷史,如何對待當今霸權,如何引領人類未來,是中國崛起亟待解決的三個難題。換言之,如何反省中華原生文明從而實現中華文明復興與創新型崛起并舉,如何因應美國權力霸權與歐洲文化霸權從而開創新型中美權力關系及中歐文明關系,如何應對世界未來挑戰從而開創人類文明新范式,直接考驗中國崛起的合理性、合法性、合目的性。這就是中國崛起的道統性。
中國之崛起,已經到了一個坎兒。中華文明從起源與思維方式上講是大河文明,從形態與生活方式上講是內陸文明,從本質與生產方式上講是農耕文明。因此,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是復古——恢復大河文明、內陸文明、農耕文明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而是轉型——作為傳統內陸文明,如何走向海洋?作為農耕文明國家,如何培育海洋文明思維,實現海洋文明崛起?在建設海洋強國的征途中,如何避免歐洲海洋文明的陷阱?
早在1920年,哲學家張君勱曾談及面對西方刺激的亞洲人處境。他指出,亞洲人的傳統原則是“順其自然,而非西方的銳意進取;精神滿足,而非力求物質優勢;自給自足的農耕主義,而非逐利的商業主義;推崇道德感化的友愛與諒解,而非種族隔離政策。以農業立國者,雖乏工業技巧,卻也無物質需求;所以,盡管國家歷史悠久,卻能一直在清貧中保持公正,于匱乏中維持和平。但從今以后,這樣的國家將何去何從?”⑤
張君勱的憂慮依然值得當今中國警醒。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國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大國,歷史上卻從未成為真正的全球性國家。歷史上中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的兩到三成,與今天占一成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后者發生在中國與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不同于此前獨立、封閉的“天下體系”。農耕文明不適應全球化時代中國崛起之態勢。
農耕文明的生產方式,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早已隨著鴉片戰爭所開啟的西方工業文明之入侵而逐漸解體,當今中國已成為全球制造業產出最高的國家,但仍未從根本上改變產生于資源稀缺時代的內斂式外交哲學,對外關系善于做加減法而非乘除法,鐘情于平衡、和諧,擅長應對“亂中有序”而非“序中有亂”,難以擔任全球化時代的領導者。
農耕文明的治理方式,重防御輕進攻。無論是老子的“無為而治”,或孔子的“恢復周禮”,或孫子的“兵法天下”,或墨子的“兼愛非攻”等諸子百家思想,都不能解答中國面臨的全球化困境。中國外交新思維,應兼收并蓄東西方文明、歷史與現代模式,與國際社會共同探索引領世界未來發展需要的外交哲學理念和制度安排。
農耕文明的思維方式,如“天人合一”理念,與當今以理性和私域為基礎的民族國家體系反差明顯;應對當今以氣候變化為重要關切的世界挑戰,也非回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并非普世觀。中國現為“世界工廠”,要成為“世界實驗室”,如何超越地域、文化邊界為人類做出普世性價值貢獻,提供全球思維的公共產品?
世界領導型國家應提出一整套“源于自己而屬于世界”的外交構想和超越民族特色、尋求世界最大公約數的制度安排。中國成為世界領導型國家,面臨的是文明轉軌與身份轉型:從傳統內陸文明走向海洋文明,從地區性國家轉變為全球性國家。當中華文明走向海洋,才能塑造包容歷史、包容西方的全新文明,為世界探索超越西方的發展模式與文明形態。
今日之中國,身份有三:一是“傳統中國”(Traditional China),即傳統農耕文化、內陸文明孕育的“文化共同體”。二是“現代中國”(Modern China),即近代以來隨著“天下”觀破滅后被迫融入西方國際體系而塑造的現代“民族國家”身份。由于國家尚未統一,“現代中國”身份仍在建構中,民族融合與核心價值觀建構挑戰尚在。三是“全球中國”(Global China)。它是指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那些利益和觀念國際化、全球化的部分,即堅持傳統文化,又包容價值普世性,而處于初級階段的全新國家身份。比如,五億網民越來越多地擁有“全球公民”身份,而非“中國人”之單一屬性。
傳統中國,經歷“夷夏之辨”而形成;現代中國,經歷“中西之辨”而塑造;全球中國,因為“走向海洋”而胎動。走向海洋的中華文明,不得不再次面向西方。不過,這次是民族自覺行為、自主選擇。它要解決的是鴉片戰爭以來近兩百年的問題,面對的是“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華文明的復興,是注定要繼承、發展、創新當年將“西天”的佛教變成華夏之佛學、神州之禪宗相類似的壯舉,將歐洲的普世價值內化為中國之道——人類共同價值,從而確立中國崛起的道統。
中國崛起的最大身份優勢,就是作為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就超越了美國、歐盟作為人造國家、組織的政治認同。因此,以西方的民主、人權觀來詮釋中國治理的合法性,以所謂的國際關系理論解釋中國和平崛起戰略,必然是牛頭不對馬嘴的。作為文明型國家,時間上追求道統“定于一”,空間上推崇“四海一家”,這就不能用西方式時空邏輯分析其在全球化世界的崛起態勢,必須回到文明的自身維度——文明的生命力。
從文明的生命力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內是中華文明的復興之路,是中華民族的富強之路,是中國人民的幸福之路;對外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偉大創舉,是中國對世界的歷史性貢獻。這是因為,中國崛起是一種全球化現象,并非一個國家的崛起。實現這一崛起依次要解決好以下三個維度問題:
其一是文明的時間維度。傳統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國度。中國的崛起,是迄今人類文明史上唯一延綿不斷的古老文明的偉大復興。然而,這種復興,不只是恢復漢唐盛世,而是在全球化世界實現的文明復興,要解決內陸文明走向海洋、傳統文化走向現代的時代課題。中國崛起,糾結于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等,本質上是“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二元身份的糾葛。只有恢復中國在亞洲的文明道統地位,臺海關系、中日關系、中國與周邊關系,才可能根本理順。
其二是文明的空間維度。現代中國,是一個五百年來被迫融入西方體系的民族嬗變。中國是文明古國中少有未被西方完全殖民且改革開放不以西化為旨趣的國家。現代中國身份建構,不僅要處理傳統文明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而且肩負實現東西方文明大融合的偉大使命,其直接的挑戰就是合理、合法、合目的地繼承西方領導世界的道統,避免落入西方式大國崛起的權勢轉移陷阱,避免東西方文明的沖突。中華文明能否超越西方文明為全球治理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器物、制度與精神支撐,是國際關系史上的重大考驗。
其三是文明的自身維度。全球中國,是一個超越復興與崛起,超越時間與空間,著眼于文明的生命力即自身演繹的全新身份。在古今中國、東西方中國之外,實現南北中國的人類使命,合目的地開創人類文明新范式、繼承性創建人類共同價值體系,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全新挑戰。
總之,堅信應該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中國,當以文明自覺探尋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世界意義,以文明自信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中國崛起的道統,不僅在于復興傳統中華文明,也不僅在于開創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從而合理繼承人類現代文明,或者實現中歐“文明G2”從而合法繼承西方文明,更在于合目的地開創人類文明新范式,實現“傳統中國”、“現代中國”、“全球中國”身份的三位一體。⑥
世界的中國期待:以中國夢實現世界夢
一個多世紀以前,美國獨立戰爭領袖林肯總統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理想,鼓舞了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先驅們去締造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同志“中國應該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理念又激勵著共產黨人將社會主義夢想與中華崛起的目標結合起來。如今,十八大再次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閉幕不久后參觀“復興之路”圖片展時明確指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現時代的中國夢。令人鼓舞的是,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接近這一夢想。
那么,什么是中國夢?一言以蔽之,中國夢的三大內涵就是源于中國(of China)、屬于中國(by China)、為了中國(for China)。
源于中國。中華民族以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邁入救亡圖存的艱難歷程,對世界的貢獻遠不如昔。一些民族虛無主義者甚至得出除了“四大發明”,中國近代的世界貢獻幾乎空白悲觀結論。
“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的理念,經歷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實踐,終于有了眉目,這就是中國模式的現代貢獻。在全球治理中,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給世界帶來不可承受之重。擯棄西方政治負面遺產,為世界展示更符合國情的模式選擇,為不少發展中國家所渴望。在“中國制造”之外,中國的發展道路、治理模式鼓勵中國提供更多“源于中國,屬于世界”的國際公共產品,豐富世界發展模式多樣性。換言之,世界需要中國夢。中國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屬于中國。中國夢首先是屬于中國的。我們不做其他國家的夢,尤其不做美國夢。“趕英超美”只是階段性中國夢。因為美國模式危害甚大,不可持續,絕非中國效仿對象。歐洲就擔心中國會成為又一個美國,認為一個美國就夠受的了。防止美國將霸權負面資產轉嫁到中國頭上,需要我們頭腦清醒,堅持夢的自信、夢的自覺。在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后,一些人認定趕超美國就是中國夢,就很可能滑入美國夢的怪圈。這樣,明確提出中國夢,也是為了防止中國做美國夢。屬于中國的中國夢,不是孤立的,而是特色夢、亞洲夢、世界夢的三位一體:
中國的特色夢:中國成為“中國的中國”,也就是傳統的文明型國家,并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延續世界社會主義夢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國并不輸出屬于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制度選擇和治理模式,中國的持續成功客觀上就在豐富世界的多樣性。
中國的亞洲夢:中國成為“亞洲的中國”,不是去恢復“朝貢體系”——亞洲已經成為“世界的亞洲”,不可能恢復“亞洲的世界”了——而是讓亞洲成為自己。因為,傳統的亞洲秩序、價值由于西方的入侵而處于時空體系的錯亂之中,傳統垂直型體系被植入平行型西方體系理念,和諧不再,沖突不斷,領土、領海主權之爭就是這種錯亂的表象。
中國的世界夢:中國成為“世界的中國”,而非“民族國家”。長期以來,西方壟斷了普世價值的話語霸權。中國模式正在打破這種話語霸權。當然,這首先要求中國建成現代文明國家,并在此過程中展示中華傳統價值、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
為了中國。中國不做美國夢,但不排斥美國夢,也不排斥歐洲夢、印度夢。恰恰相反,中國的成功鼓勵其他國家去實現各自的夢想,中國需要世界夢——為了中國也是為了世界,為了世界才能更好地為了中國。中國夢與世界夢是完全融合的。中國不應做脫離世界的狹隘民族夢,世界也不應做排斥中國的“西方中心論”夢。
總之,中國夢是崛起后的中國交給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答卷,要解答的是現時代的“張載命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天地立心,就是去挖掘中華文明與中國價值的世界意義,探尋人類共同價值體系。為生民立命,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彰顯中國的人權、國權。為往圣繼絕學,就是實現人類永續發展,各種文明、發展模式相得益彰、美美與共。為萬世開太平,就是推動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實現全球化時代的“天下大同”。
結語:中華文明復興的三位一體
簡單用“崛起”來描述中國發展之態勢,的確不準確,因為后者是大國崛起、民族復興、文明轉型的“三位一體”。沒有文明轉型,大國崛起不可續,民族復興不可濟。大國崛起的邏輯是融入、參與全球化,順勢而為,乘勢而上;民族復興的邏輯是文化自覺、自信,回歸道統,回歸自然;文明轉型的邏輯是以“中國夢”實現“世界夢”,為世界轉型提供“源于中國而屬于世界”的器物、制度與精神公共產品。
光陰荏苒,近代以來中國“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的邏輯,⑦今天已上升為文明轉型的邏輯,即通過自身的文明轉型推動人類文明轉型。這就是大國崛起、民族復興、文明轉型“三位一體”式中國和平發展所傳遞的主要信息。
中國迄今為止的成功,可粗略歸納為“三靠”。一靠體量,“中國的最深刻的特點,就是這個國家太大了”;⑧二靠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贏得“全球化紅利”的體制保障;三靠體魄,作為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其意義超越了歷史上任何其他大國崛起,是對世界多樣性的最偉大貢獻。中國的發展目前進入強體魄的關鍵階段,即進入文明轉型階段。
文明轉型的涵義有三:從生產方式講,是指從農耕文明轉向工業(信息)文明;從生活方式講,是指從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向不同文明間的互容互鑒、和諧發展升級;從思維方式講,是指從地域性文明轉化為全球性文明,即在十八大報告確立的“修身”(個人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齊家”(社會層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治國”(國家層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這24字核心價值觀基礎上,確立“平天下”(全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人類共同價值體系,塑造“傳統中國”、“現代中國”、“全球中國”三位一體式國家身份。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是“復古”——復古解決不了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也不能應對世界挑戰;更非“接軌”——西方難言先進,且自顧不暇,一些國家還希望中國創出一條嶄新的道路而與中國接軌;而是復興、包容、創新的三位一體:通過合理地復興我們的原生文明——催生中華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種子而走向海洋,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過擯棄西方普世價值神話而塑造人類共同價值體系,合目的地創新人類文明——通過引領人類文明轉型以實現人類永續發展,從根本上確立中國作為世界領導型國家的道統。
注釋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王義桅:《超越國際關系:國際關系理論的文化解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第一章。
"China is a threat to democracy",BBC NEWS ,Nov. 23, 2008.
[英]馬丁·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張莉、劉曲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印]潘卡伊·米什拉:“當東方遇見西方”,《紐約時報》,2012年10月22日。
王義桅:《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
章百家:“改變自己 影響世界——20世紀中國外交基本線索芻議”,《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第6頁。
[英]戴維·皮林:“中國太大了?”,《金融時報》,2010年10月13日。
責 編/鄭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