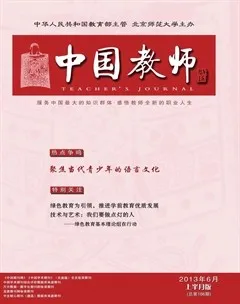高中文言文教學價值的再認識
高中文言文教學先后存在著兩種常見的教法:一是在新課程實施前為應對各類考試追求“字字落實,句句翻譯”,把美文單純當作積累文言知識的訓練材料;二是新課程實施后,為順應語文課要培養人文精神的潮流,匆匆疏通文字后架空語言,分析文章的思想文化。前者“重言輕文”,將文言文學習簡化為翻譯,學生只得到了文言知識的碎片;后者“重文輕言”,將文言文學習簡化為“翻譯+白話文”學習,學生“詞語掌握不了幾個,文章沒有讀懂多少,得到的只是抽象空玄的人文思想的‘碎片’而已”。后者原本是新課程實施后以糾正前者的姿態出現的,但矯枉過正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兩種教法顯而易見都沒有解決文言文教學低效的痼疾。
一、高中文言文教學的核心價值不應定位于文化價值
這兩種教法的病根兒貌似在“怎么教”上,實則在“教什么”上,前者強調文言知識,后者強調文本內容。二者在“教什么”上的分歧,實則是對高中文言文教學價值的認識有分歧。新課程實施以來,在高中文言文教學的三重價值——語言價值、文章(文學)價值、文化價值中,最受重視的是文化價值,最易被忽視的是語言價值。當前“主流”的認識是高中文言文教學應該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的傳統文化。
筆者以為,將高中文言文教學的核心價值定位于文化價值,這個觀點似是而非。第一,目標本身難以量化。所謂的“民族的”“優秀的”“傳統文化”本身就是模糊概念,難以在文言文教材和課堂教學中具體化和量化,只能憑教師自主確定,而這樣又難免有隨意解讀甚至誤讀的風險。第二,學習結果難以評價。關于文言文教材里的“民族的優秀的傳統文化”有多少是學生未知的,又應該讓高中生了解到什么程度,并沒有(也難有)明確的要求和測試手段。所以,一直以來文言文閱讀測試只能考查學生對文章內容的理解。第三,有違于課程目標。從語文課的本質目標看,文言文教學首先是為了提高文言文的閱讀能力,而繼承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應該是次要目標。或者說,繼承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文言文教學的遠期目標(甚至終極目標),而高中階段文言文教學的近期目標則是培養這種繼承的能力。“重文輕言”的教法低效的根源,正是把文化價值當作高中文言文教學的核心價值,把文言文教學的遠期目標誤作近期目標,最終落得“語言”和“文化”兩頭空。
二、高中文言文教學的核心價值應定位于語言價值
我們不妨回到原點思考:文言文是什么?從本質屬性看,文言文是使用象形文字記事的書面語,象形文字筆畫繁多,故文言文需要簡略記事、脫離口語。這雖然帶來了閱讀上的難度,可也幫助文言文克服了不同地域的方言障礙和不同時代的語音變化等困難,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所以,文言文蘊藏著古人在書寫成本高昂時代的表達智慧。當代學生學習文言文時,應該首先探究語言背后所蘊藏的古人的表達智慧,這正是文言文的語言價值所在。
高中文言文教學的實際情況卻是,語言價值非但沒有成為高中文言文教學的核心價值,而且還一直是高中文言文教學的盲點。因為很多一線語文教師對文言文的語言價值比較陌生(甚至對高中文言文教學的三重價值還認識不清),而語文教學專家雖知卻不重視。不過,按“課標”的理念,“讀懂淺易文言文”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吸收文言文蘊含的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如果讓學生直接閱讀名家的譯文,略過“讀懂”環節,直奔“文化”,豈不是更省時高效?事實上教材編者和教師都沒有這樣做,這說明編者和教師也意識到文言文有其語言層面的價值,但對這種價值可能不甚明了,所以大家更重視文言文內容層面的價值,而忽略了文言文語言層面的價值。這種忽略可能源于滯后的語言觀——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是思想的物質外殼。教材編者、高考命題者、一線教師甚至“課標”制定者仍把文言文看作是古人思想的物質外殼,似乎只要(用翻譯法)揭開這外殼,就能(像現代文一樣)幾無障礙地汲取其中蘊含的優秀傳統文化了,這可能也是文言文教學和考試都非常重視“讀懂”字面意思的深層根源。而新的語言觀認為,語言就是人存在本身,而不是一種交往工具;任何語言在傳遞本民族文明的同時,也反映著該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文言文正是這樣一種反映著中華民族特有思維方式的語言形式。
如《左傳·僖公十六年》有一句“隕石于宋五”,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宋國降下五塊隕石”,一個平淡無奇的句子。但看《春秋經》是怎樣分析其妙處的: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這樣的語序將隕石的發現過程和人們驚疑、探究、釋然的心理過程都現場直播般呈現給讀者。再如《資治通鑒》“赤壁之戰”部分有一句“魯肅獨不言”,語境是孫權召集群臣議論如何應對曹操,張昭等力主降曹。按現代漢語語法習慣,這句話應翻譯為“唯獨魯肅不說話”,原句與譯句的區別就在于狀語“獨”的位置不同。若再仔細品味原句與譯句,便可發現:譯句只是客觀地展示了“魯肅不說話”的“鏡頭”,原句除表達“魯肅不說話”的意思之外,用“獨”修飾“不言”,還暗示出魯肅的心理——有意地不說話。這兩個例子說明,原句體現出敘述者對讀者感知體驗的“尊重”,而譯句傳遞給讀者的是經過敘述者加工過的信息,“剝奪”了讀者感知體驗的權利。原句的言簡意豐正是文言文的語言價值所在,對讀者的“尊重”也體現著文言文的文化價值。如果我們語文教師能夠這樣引導學生探究、體味文言文的語言價值,領略文言的魅力,何愁學生沒有學習興趣呢?反思“重言輕文”的教法,并不重視文言文的語言價值,只是滿足于翻譯而已,再加上教學流程單一,讓學生厭學也在意料之中。
三、高中文言文教學應區分三重教學價值
綜上分析,當前高中文言文教學低效的根源是教師對文言文具體篇目的三重教學價值區分不清晰,甚至可以說,只重視文化價值而不重視語言價值。教師首先要明確文言教材里的每篇文言文的三重教學價值分別是什么。其次,教師要根據三重教學價值在文言篇目中的顯隱輕重和學情需要,將教材中的文言篇目大致分類,如將人物傳記類篇目歸入文學價值類。再次,根據分類設計教學流程,如《燭之武退秦師》的語言價值突出,可以省略文化價值的學習;如《逍遙游》的文化價值突出而語言難度大,可提供準確的譯文給學生參考,省出時間研讀其中的文化思想;如《鴻門宴》語言價值、文學價值突出,則可以省略文化價值的學習。最后,無論是探究文言文的語言價值,還是探究其文學價值、文化價值,教學過程都應該在品味語言中進行,這樣師生學習文言文的重點目標和學法就相對清晰了。
這樣的文言文教學策略既能確保實現單篇文言文的核心教學價值,就所有文言篇目的教學而言,又能總體實現三重教學價值的互補兼顧。這種分類教學法也將文言文教學由過去的以單篇教學為主,改為以類篇教學為主。過去的單篇教學只關注本篇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流程,忽視篇與篇之間學習內容、學習方式上的聯系,教學目標和教學流程難免重復、單一。如果改為以類篇教學為主,確定教學目標和教學流程時將關注這一類篇目,將尋找篇與篇之間學習內容、學習方式的聯系作為備課重點,從而使教學目標重點突出,使教學流程形成合理范式。
以上是筆者對高中文言文教學的一點粗淺思考,祈請專家指正。
(作者單位:北京市大興區教師進修學校)
(責任編輯:馬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