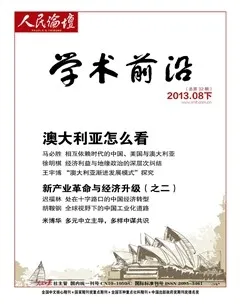一場平靜而深刻的社會政治變革
摘要 澳大利亞漸進發(fā)展模式是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發(fā)展模式之一。200多年來,以社會的繁榮、變革與轉型為主要內(nèi)容的澳大利亞現(xiàn)代化發(fā)展是恢宏而深刻的,它呈自然與平靜狀態(tài)下的演進,表現(xiàn)為各種社會機制在漸進中改進、提升與完善,以相對極低的損失屢屢完成發(fā)展性質變。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相比較,澳大利亞社會的變化不在于驚天動地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或是深邃莫測的理論創(chuàng)新,而是根據(jù)現(xiàn)實需要和自身情況,務實而具體地對移植而來的舶來品進行局部、甚至是很小的一個部分的改進與創(chuàng)新。關鍵詞 澳大利亞 現(xiàn)代化模式 本土化 和平環(huán)境 漸進發(fā)展
【作者簡介】
王宇博,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導。
研究方向:英聯(lián)邦國家歷史、澳大利亞現(xiàn)代化問題。
主要著作:《澳大利亞——在移植中再造》、《移植與本土化——大洋洲文明之路》、《漸進中的轉型——聯(lián)邦運動與澳大利亞民族國家的形成》、《世界現(xiàn)代化歷程·大洋洲卷》(合著)等。
現(xiàn)代化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所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然而,各國由于國情不同,在這階段的發(fā)展情況多有差異。縱觀近現(xiàn)代以來的人類歷史,澳大利亞是第一個完全以和平方式進行社會變革的國家,①進而成為后起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國家中的先行者之一,自然而順利的發(fā)展與理智而明確的選擇是其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顯著特點與表象。然而,其變化與發(fā)展非但未引起外部世界的關注,就連大多數(shù)澳大利亞人都未感覺到。②和諧漸進構成了澳大利亞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路徑與模式。
發(fā)展軌跡:從“海外監(jiān)獄”到現(xiàn)代化國家
英國建立澳洲殖民地的初衷是解決日益嚴重的本土在押罪犯羈押難題。1788年1月26日,英國“第一艦隊”到達悉尼,759名罪犯在646名軍人及20名官員的押解下登岸。這不僅是澳大利亞成為英國流放犯殖民地的開始,而且也是澳大利亞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進程的起點,澳洲由土著原始社會一步邁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繼新南威爾士之后建立的5個英屬澳洲殖民地在形成方式與類型屬性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人們的自覺行為都是效仿英國,認定澳洲勢必“從一個罪犯懲治地成長為一個自由社會”,③即以自由主義為基準的英式社會。
19世紀上半期,“牧羊業(yè)大潮”使澳洲經(jīng)濟突飛猛進,大有成為“大英帝國內(nèi)最偉大的殖民地之一”之勢。經(jīng)濟發(fā)展導致社會繁榮,進而自然引起人口結構的變化,刑釋人員增多、自由移民增加,澳大利亞民族由此生成。蓬頭垢面的罪犯與低俗粗暴的軍人已成為“完全成熟的白種英國國民”,適用于“海外監(jiān)獄”的現(xiàn)行管理制度對于澳大利亞現(xiàn)實社會日趨顯得相形見絀。于是,以伸張作為英國人“天賦權利”為核心內(nèi)容的自治運動應運而生。英國的政治體制與社會制度在澳洲得以順理成章地移植與復制,澳洲社會在漸進中轉型為英屬公民殖民地。然而,“在新大陸,所有由母國漂洋過海而來的東西無不發(fā)生本質性的變化”,④本土化現(xiàn)象明顯。例如,在19世紀中期相繼成立的澳洲各殖民地責任政府在職權、職能與結構上無一不是移植于英國的地方政府,但在社會管理中,它們逐漸取代了英國派遣的總督,“澳洲人管理澳洲”的訴求漸漸成為社會現(xiàn)實。
運作于19世紀后50年的聯(lián)邦運動,起源與終結于澳洲各殖民地之間聯(lián)合的逐漸形成與澳洲統(tǒng)一在法律意義上的趨于確立,澳洲社會形態(tài)由公民殖民地逐漸轉型為民族國家。它的核心內(nèi)容同樣是伸張“天賦權利”,但此時的“天賦權利”具有愈加鮮明的澳洲色彩,而非自治運動所追求的“故鄉(xiāng)的權利”,它所主張的“自主”與“自治”的內(nèi)涵實為獨立。盡管母國情結深厚,但人們無意“犧牲地方主權而去服從一個由聯(lián)合王國支配的、遙遠的中央政府”。⑤在對維護權利與擴大利益的追求中,“澳洲各殖民地之間的隔閡的消除對于社會經(jīng)濟是有益”的觀念⑥逐步成為澳洲社會的共識,而各地區(qū)之間的合作往來正愈加明顯地演變?yōu)檎紊系穆?lián)合,澳洲統(tǒng)一成為大勢所趨。1901年,澳大利亞聯(lián)邦成立,澳大利亞以自治領的形式轉型為擁有國家主權的民族國家。
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相比較,澳大利亞社會的變化不在于驚天動地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或是深邃莫測的理論創(chuàng)新,而是根據(jù)現(xiàn)實需要和自身情況,務實而具體地對移植而來的舶來品進行局部、甚至是很小的一個部分的改進與創(chuàng)新。回顧這些改進與創(chuàng)新,其中有的立竿見影,產(chǎn)生了意想不到的社會效應和經(jīng)濟效益;有的則具有開辟某種或某一領域先河的作用和價值;有的卻見效于后來,給人以細水長流的感覺。舶來品會因澳大利亞人的追求與磨礪而增添了新的內(nèi)容、新的形式和新的價值;并又因這樣的變化,舶來品的創(chuàng)造者與創(chuàng)造國又反過來從澳大利亞移植舶來品的創(chuàng)新部分。
因此,雖然澳大利亞在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制度等方面并無重大的首創(chuàng)之舉,但在具有揚棄功能的本土化作用下,被移植而來的西方文明轉變?yōu)橐环N適合澳大利亞國情的新文明。換言之,澳大利亞人在事無巨細地仿效以英國為主的歐美國家來設計與建設澳洲的同時,又在自然地根據(jù)客觀現(xiàn)實和需要修改著“舶來品”,進而形成了自己的屬性與特征。兩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關系,但又有越來越明顯的差別。在民族意識的驅動下,1901年前,澳大利亞出現(xiàn)了一系列旨在爭取自由和平等的社會政治運動,最終導致建立起一個新國家——澳大利亞聯(lián)邦;之后,澳大利亞進一步移植、兼容和揚棄了西方的多種制度,致力于建設平等和自由的社會。國家的獨立與社會的成熟在平穩(wěn)的漸進中加強,澳大利亞逐步成為后起的發(fā)達國家,躋身于現(xiàn)代化國家排名前列。根據(jù)《1997年世界發(fā)展報告》“1995年世界120個國家(地區(qū))現(xiàn)代化水平得分和排序”,澳大利亞得208.8分,列第18位。⑦
實質考察:穩(wěn)定與和諧的現(xiàn)代化模式
本土化是澳大利亞現(xiàn)代化的重要內(nèi)容與實質表象。在本土化發(fā)展的過程中,以英國為主的社會意識、政治制度及經(jīng)濟體系被自然而系統(tǒng)地移植于澳洲,進而在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狀態(tài)下孕育出新生的澳大利亞民族和國家,澳大利亞也由此逐步與母國分離,走上了獨立發(fā)展的道路。澳大利亞社會變革的基調(diào)與主題由此構成,并作用于澳洲社會的屢次轉型。換言之,澳大利亞現(xiàn)代化模式就是英國現(xiàn)代化模式的澳洲本土化版。
傳統(tǒng)問題是各國現(xiàn)代化不可回避的問題。澳大利亞雖然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卻不是一個沒有傳統(tǒng)的國家,英國的傳統(tǒng)在澳大利亞無處不在,以致人們時常視其為英國的“海外部分”,“一塊被放錯地方的歐洲土地”。然而,本土化如同一只過濾器,對移植而來的舶來品進行揚棄,根據(jù)澳洲的現(xiàn)實,取其精華。17至18世紀,歷史教訓使英國人認識到和平解決沖突的必要性,并致力于用和平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與改造社會制度;時至19世紀上半葉,英國人的努力使它成為運用和平方式解決內(nèi)部沖突的典范。⑧而澳洲社會的發(fā)展與轉型恰在此時與其后,和平方式自然植根澳洲,并造就出了更為穩(wěn)健的和平發(fā)展模式。此外,西方國家的種種弊端雖然時常出現(xiàn)于澳洲社會,甚至產(chǎn)生很大影響,但這些糟粕往往能夠在本土化過程中逐步被淘汰。源于歐洲種族主義的“白澳政策”雖然在澳大利亞民族與國家形成中產(chǎn)生過巨大的凝聚作用,但它對土著居民和有色人種移民的傷害則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當澳大利亞人意識到其嚴重性后,在相當短的時間內(nèi)就將其唾棄。1972年,聯(lián)邦總理惠特拉姆明確表示:“種族或膚色將不再成為進入澳洲的一種標準。”⑨
20世紀后半期以來,澳大利亞已達到了無需借助本土化也能持續(xù)發(fā)展的程度。這表明本土化終將在未來盡其功能,但本土化畢竟影響了澳大利亞社會兩個世紀,使澳大利亞從英國的“海外監(jiān)獄”步入發(fā)達的現(xiàn)代國家行列。
“澳大利亞漸進發(fā)展模式”的最顯著特征是穩(wěn)定與和諧。它表現(xiàn)為:
第一,澳大利亞社會一直處于安定之中。從1788年至今,澳大利亞沒有發(fā)生過戰(zhàn)亂或社會動蕩,外界的動亂不僅沒有侵擾這塊孤懸南太平洋上的大陸,反而為它提供了發(fā)展的機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澳洲內(nèi)部的各種關系易于協(xié)調(diào),人們習慣于不使用激進的方式解決矛盾。在澳大利亞歷史上,僅1854年12月發(fā)生過一次金礦工人暴動——尤里卡起義,造成30名工人和5名軍人死亡,數(shù)十人受傷,轟動一時。這是澳洲歷史上的唯一一次造成傷亡的政治性社會沖突事件。⑩
1788年以來的澳洲史,就是一部既循序漸進又持續(xù)不斷的澳洲社會變革史。無論是在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轉型中,還是在同一形態(tài)的社會政治變革里,社會觀念與國家政策的變化與更改基本上是后者對前者的繼承和完善,而不是后者對前者的批判和否定。這就保證了澳洲社會發(fā)展是在風平浪靜中演進,而不是在天翻地覆中震蕩。如對英國代議制度的移植是自治運動的主要內(nèi)容,而在之后的社會改革與轉型中,它的充實與完善過程表現(xiàn)為其澳洲屬性的愈加鮮明。這種良好的連續(xù)性與穩(wěn)定性使澳大利亞社會得以穩(wěn)步而持續(xù)發(fā)展。
應予指出的是,澳洲白人對土著人及有色人種移民曾有的暴行雖令人發(fā)指,但由于后者人數(shù)不多并長期被排斥于主流社會之外,因此,這類行徑不至于導致社會動蕩。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使社會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成為可能。
第二,縱觀今昔,澳大利亞竟沒有一組足以導致社會不安定的社會矛盾的存在。在這個國度里,宗教問題簡單,民族成分相對單一,勞資矛盾與沖突可以調(diào)和。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合理謀利”是澳大利亞人共有的社會意識與共同的行為規(guī)范,因此,維護和諧發(fā)展成為人們的共識和自覺的行動。簡言之,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和民族和諧是當今各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必備條件,而澳大利亞恰巧都具備這些條件。
近代以來,因社會結構復雜而導致的利益相悖是造成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在社會變革中動蕩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緊隨唇槍舌劍之后的往往是刀光劍影,乃至兵戎相見。而審視200多年來的澳洲主流社會,情況則大相徑庭,涉及社會問題的矛盾沖突此起彼伏,但僅限于口誅筆伐,尤其是在尤里卡起義之后,人們自覺排斥暴力,對沖突升級多加防范。1891年,在制定《澳大利亞聯(lián)邦憲法》的“聯(lián)邦會議”上,與會者圍繞國名“澳大利亞聯(lián)邦”中的“commonwealth”一詞展開激烈辯論,其原因僅是人們心有余悸地由此聯(lián)想到憑借暴政維系的1649年英吉利共和國。最后,利益與共識使這個未來國家的名字“只是勉強地被(制憲)委員會接受了……僅以一票的多數(shù)通過了”。
漸進改革是英國社會發(fā)展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移植到澳大利亞后,則造就出更為平穩(wěn)的“澳大利亞漸進改革模式”,鋪設出平坦的澳大利亞現(xiàn)代化之路。值得指出的是,20世紀20年代以來,人們推崇印度“圣雄”甘地的原因在于他倡導與領導了導致印度獨立的“非暴力運動”,并認為這是他的首創(chuàng)。然而,考察澳大利亞的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早在19世紀,這種運動形式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澳洲,并卓有成效。因而,澳大利亞應是第一個以非暴力形式獲得獨立的民族國家。這也導致了一個澳大利亞與眾不同的現(xiàn)象:其他國家與民族往往因擁有成千上萬捐軀的英烈而自豪,可是,澳大利亞人則為在其歷史中僅發(fā)生過一次造成幾十人傷亡的沖突事件而得意。
從民族意識和民族秉性方面而言,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澳大利亞民族稟承了英吉利民族的求穩(wěn)心態(tài),澳大利亞民族與英吉利民族同樣以穩(wěn)重守成而著稱。這并不是一味頑固地反對進步,而是對變革的進程和方式持謹慎與持重的態(tài)度。例如,20世紀中期以來,共和運動已在澳大利亞醞釀了半個世紀,盡管澳大利亞遲早將實行共和政體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1992年2月至1994年2月的5次民意測驗結果來看,支持共和制的比例分別為57%、56%、66%、62%和63%。在1998年2月召開的憲政會議上,152名代表圍繞建立共和國問題舌戰(zhàn)10天,最終以89票贊成、52票反對和11票棄權的投票結果,同意在澳大利亞建立共和國。投下反對票的聯(lián)邦總理霍華德說道:“我本人毫無疑義地認為這一共和模式已得到一個明確多數(shù)的贊同,可以交由明年全民公決。”然而,在1999年11月6日舉行的全澳全民公決中,澳大利亞人卻明確無誤地拒絕了共和制,致使孕育已久的“共和嬰兒”胎死腹中,盡管之后仍有75%的人支持在澳實現(xiàn)共和制,90%的人主張由澳大利亞人出任國家元首,僅有9%擁護英國女王為澳大利亞國家元首。其原因則相當簡單:一是澳大利亞人認為共和制還有一些不完備之處,尚需進一步完善,不能因操之過急而引起社會波動;二是求穩(wěn)心態(tài)影響了人們的行為,霍華德的一席話道出了原委:現(xiàn)成的君主制“只要沒有破碎,就不必修理它”,澳大利亞“何必勞民傷財,為變而變”?然而,共和運動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一向倡導共和制的工黨總結了經(jīng)驗與教訓,表示將繼續(xù)致力于共和事業(yè),“直到一個工黨政府的總理帶領我們走進共和國那一天為止”。
成因解讀:理性、傳承與融合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的社會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進程可謂是緩慢的,難覓具有標志性的突變事件,它的任何變化都需要經(jīng)過一個較長時期的觀察才能有所發(fā)現(xiàn),但是,它的發(fā)展和變革則是深刻的。回首這200多年的歷史,澳大利亞在一個又一個不顯眼的漸變中,發(fā)生了一個接一個的質變,形成一個連一個的飛躍,從而呈現(xiàn)出可持續(xù)發(fā)展狀態(tài)。所以,從實質上看,澳大利亞的發(fā)展又是迅速的,它用200多年的時間走完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用了更長的時間還未走完的路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澳大利亞民族是一個脫胎于英吉利民族的年輕民族,英吉利民族的民族精神對澳大利亞民族的影響深遠而重大。作為現(xiàn)代化先驅民族國家的一種“精神產(chǎn)品”,英國的“紳士風度”在澳洲得以移植、繼承與本土化,表現(xiàn)為澳大利亞人在價值取向、道德觀念及行為準則等方面與英國人如出一轍。而注重平等與公正、講究理性主義、崇尚穩(wěn)重與平和、厭惡暴力,則是澳大利亞人尤為注重的內(nèi)容。這種文明的傳承對澳大利亞現(xiàn)代化發(fā)展至關重要,也是它可以順利具備現(xiàn)代化發(fā)展必備條件的一大因素。
第二,澳大利亞社會發(fā)展是在穩(wěn)扎穩(wěn)打中進行的,沒有出現(xiàn)在別國常見的大起大落,表現(xiàn)出較強的持續(xù)發(fā)展能力和可觀的發(fā)展前景。無論是19世紀的“牧羊業(yè)大潮”和“淘金熱”,還是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使澳大利亞在經(jīng)濟領域出現(xiàn)驚人的“大起”,然而,事后卻沒有出現(xiàn)可怕的“大落”,反而是在“大起”基礎上的再繼續(xù)發(fā)展,從而使澳大利亞大受其益。平穩(wěn)與協(xié)調(diào)使社會變化所導致的社會損失微乎其微,幾近可被忽略。澳大利亞的仲裁制度“涉及范圍之廣,為任何國家前所未有”,它的移植、建立與完善已歷時百余年,各屆政府對其態(tài)度大致相同。這一連續(xù)性使因制度變革所造成的損失僅表現(xiàn)為少數(shù)人在心理上的一時不適應。
第三,澳大利亞的發(fā)展不是在封閉的環(huán)境里進行的,它從一開始就因英國而面向世界,并愈加融于全球化。這在客觀上使澳大利亞有條件鑒別、篩選、借鑒和汲取其他國家的經(jīng)驗與教訓,在很短的時間里移植別國的成功舉措和成熟體制,確立適合自身發(fā)展的道路和方式,從而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亞社會發(fā)展的速度。例如,在建立福利制度問題上,澳大利亞人目睹西方工業(yè)化中嚴重的社會分化而迫切要求背上這“文明的包袱”。聯(lián)邦總理迪金在1906年寫道:美國的效率是以“人們體質和生命的駭人犧牲作為代價換取的”,決不能使澳大利亞人“陷入這種可憐而絕望的境地”。在福利制度的建設過程中,澳大利亞人并沒有著力創(chuàng)建有關理論,而是借鑒英國人耗費了“幾乎半個世紀的光陰”而探索出的理論,經(jīng)過本土化改造,建立起了適合澳大利亞社會的福利制度。
(本文系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劃基金項目“社會轉型問題研究:以澳大利亞為范例”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9YJA770045)
注釋
至二戰(zhàn)結束前,因受種族主義的影響,社會觀念與社會制度使澳洲社會分為由白人構成的主流社會與由土著和有色人種構成的非主流社會。戰(zhàn)后,隨著種族主義的蛻化,土著和有色人種的權益逐步得到認可與尊重,這一社會界限逐漸消失。文中所論述的戰(zhàn)前澳洲社會為主流社會。
W. J. Hudson & M.P.Sharp, Australian Independence,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
[澳]斯·麥金泰爾:《澳大利亞史》,潘興明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48頁。
Ann-Mai Jordens, Redefining Australians, Sydney: Hale&Iremonger Pty Ltd, 1995, p.57.
L. Trainor,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6.
G. Dish, Australia Then&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92.
朱慶芳:“從三項國家評估看中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水平的提高”,《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5期。
錢乘旦:“社會變革的和平方式:英國的范例”,《學習與探索》,2005年第6期。
R.Ward, A Nation for A Continent, Richmond: Heinmann Educational Australia Pty Ltd, 1981, p.401.
F. Crowley,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Melbourne: William Heinenann Australia Pty Ltd, 1974, p.42.
M. Mckenna, The Captive Republ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90-192.
J. Baker, For Queen or Country?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59.
《人民日報》,1998年2月15日。
王宇博、汪詩明、朱建君:《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大洋洲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4頁。
王宇博:《澳大利亞——在移植中再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8、279頁。
[澳]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亞政治社會史》,北京翻譯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232、289~290頁。
參考文獻
W. J. Hudson & M. P. Sharp, Australian Independence,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澳]斯·麥金泰爾:《澳大利亞史》,潘興明譯,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年。
Ann-Mai Jordens, Redefining Australians, Sydney: Hale&Iremonger Pty Ltd, 1995.
L.Trainor,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G. Dish, Australia Then&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Ward, A Nation for A Continent, Richmond: Heinmann Educational Australia Pty Ltd, 1981.
F. Crowley,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Melbourne: William Heinenann Australia Pty Ltd, 1974.
M. Mckenna, The Captive Republ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 Baker, For Queen or Country?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4.
王宇博、汪詩明、朱建君:《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大洋洲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王宇博:《澳大利亞——在移植中再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澳]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亞政治社會史》,北京翻譯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
責 編∕鄭韶武
A Calm and Profound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
—Study on Australia's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Mode
Wang Yubo
Abstract: The "Australian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mode" is one of the development modes of the world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ver the past 200 years, the Australian modern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social prosperity,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enormous and profound. It has evolved in a natural and steady state and manifested itself with the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of a variety of social mechanisms and the repeated qualitative changes in development with relatively low losses.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and peoples, social changes in Australia do not lie in remarkable inventions or profou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ut result from their pragmatic and specific efforts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parts of or even a minimum of exotic things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needs and situations.
Keywords: Australia, modernization mode, localization, peaceful environment, progressiv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