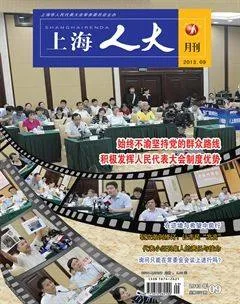以市場化和國際化促進上海經濟轉型發展
一、基本判斷:經濟的潛在增長力下降
今年上半年,上海在黨中央、國務院及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克服了錯綜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帶來的困難,國民經濟保持了平穩發展的良好運行態勢。消費市場增勢平穩,投資保持較快增速,第三產業領先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出口的下降,實現了實際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7%的預期目標。同時,經濟運行的質量也有一定的提高,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經營效益小幅提高,財政收入及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就業形勢總體平穩。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從中長期來看,上海經濟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正在增加,發展潛力不斷下降。主要表現在:其一,由于受資源、環境等因素的約束,上海經濟的潛在增長力正在逐漸下降,要維持現有的增長率有一定的難度;其二,上海的創新能力相對不足,盡管先后有“四個中心建設”等思路,但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其三,產業結構的調整速度緩慢,傳統產業轉移出去了,但沒能迅速建立起新的替代產業,服務業的發展也遲遲沒有新的突破;其四,政策及制度環境不夠理想,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受到制約,無法給上海帶來新的活力;其五,在市場化的浪潮中,上海被迫卷入區域內的過度競爭中,原有的區位優勢逐漸喪失,卻沒能在競爭中建立起新的競爭優勢;其六,市場競爭秩序較為混亂,公平有效的市場競爭受阻,使得未來可能引領上海經濟發展的新的市場主體及新的主導行業難以成長。
二、問題所在:轉型中思想和政策的偏差
上海經濟潛在增長力的逐步下降,既有客觀上宏觀經濟環境變化等因素,也有我們主觀上認識偏差及措施不當等原因。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面對資源及市場的限制,上海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90年代末,面對資源、環境及市場的約束,上海提出要著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進入本世紀后,面對資源、環境、國內外市場競爭及各種社會矛盾的制約,上海又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然而,環顧近20年來上海的經濟發展,我們不難發現,上海的經濟增長方式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極其緩慢的,經濟基本上是循著增長的慣性在滑行,在有些領域基本沒有進展,在有些領域甚至出現倒退。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和政策措施存在一定的偏差。
在指導思想方面,我們習慣于政府主導的思維模式。尤其是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及經濟發展方式中,政府一直起著主導的作用,而市場的作用沒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結果往往出現政府設定的目標與市場主體的需求或意愿不匹配,有時甚至產生尖銳的矛盾,導致無法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來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在政策措施方面,我們習慣于由政府去規劃“產業園區”或“大項目”,但有時由于得不到市場主體的積極響應,結果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或由于市場主體難以進入,結果產業化無法實現,從而加大政策成本。何況,這種政策措施對制造業或許有一定的作用,但對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很難起到應有的作用。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以思想意識及政策體制的不斷創新為必要條件的,尤其是上海的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并已進入重要的轉折時期,轉變思想意識及政策體制尤為重要。
首先,“政府主導”容易導致政策措施發生偏移,使得政策支持的對象因能從政府那里得到充足的資源而得以發展,而非政策支持的對象因得不到必要的資源而發展受阻,具體表現在上海民營經濟、中小企業以及非制造業新的業態的發展相對落后;其次,“政府主導”容易導致企業在面對國內外的競爭壓力時,不是首先考慮通過自主努力來積極應對,而是更多地依賴政府的保護,上海一些劣勢產業長期得以溫存,便是實施這種政策的必然結果;第三,“政府主導”往往容易使主管部門制訂一些不切實際的產業發展規劃,如片面強調上海要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讓其他地區為上海提供各類產業配套,這種過于理想化的產業規劃不利于上海在多層次的產業結構中尋求創新性的突破,也違背城市經濟中各產業層次共存的一般規律;第四,“政府主導”使政策風險和政策成本大大提高,因為隨著經濟市場化、國際化、全球化以及服務化的進展,尤其是當上海進入中等發展階段后,更高層次的產業規劃、目標設定及手段選擇等已變得更加困難,與經濟運行中的“市場失效”相比,“政府失效”的可能性正在逐漸增大。
三、政策建議:進一步推進市場化和國際化
上海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高經濟的潛在增長力,有必要確立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指導思想。在實施具體的政策措施時,要更加充分地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進一步推進市場化和國際化以及有效地維持市場競爭秩序,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來實現上海經濟的創新與轉型發展。
第一,進一步完善要素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尤其是資金利率、能源及主要原材料價格要進一步市場化,通過提高資金成本控制投資規模,抑制產能的繼續擴大,通過提高能源及主要原材料的價格,盡快淘汰耗能高及耗資源大的產業;
第二,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營造促進競爭、禁止壟斷的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著力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讓包括國外投資者在內的各類市場主體能自主、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尤其是要從政策上支持民營企業進入目前的非競爭性行業及壟斷行業;
第三,進一步降低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范圍和程度,尤其是在上海經濟已發展到今天的程度,目標產業設定的不確定性愈益增大的情況下,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直接配置資源會增加資源錯配的可能性,并有可能造成財政資源的巨大浪費;
第四,大幅度減少對劣勢企業及產能過剩企業的一般補貼及融資優惠,相反,對這些企業為轉產而廢棄舊設備、購置新設備則應提供財政及稅收上的必要支持,減輕這些企業的經營成本和經營風險,進而加快上海產業結構的調整;
第五,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及國際航運中心也許是上海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力抓手,但在此過程中光有政府的積極性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通過完善市場化機制、營造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最大限度地調動各類市場主體的積極性;
第六,隨著上海商務成本的提高,一般制造業將會逐漸退出上海,為了構筑上海新的競爭優勢,除了由政府牽頭引進大項目外,有必要在部分區域構建擁有高附加值及特殊生產工藝、配套性強的中小企業集群,并設法改善它們的生存環境;
第七,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擴大內需,除了盡可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改革收入分配方式以縮小收入差距及完善公共養老金制度外,有必要從政策上支持其他各種類型的市場化養老金體制的發展;
第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會伴隨相當時期的陣痛,尤其是短期內失業的增加將會加重社會壓力,為此需要強化失業保障制度,并采取政府、企業、個人分攤費用的方式,開展各種形式的職業培訓,提高職工的就業適應性;
第九,經濟長期持續的發展不僅有賴于有效的市場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還要依靠制度及政策的創新來實現,因此要正確認識新形勢下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在弱化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同時,強化政府對宏觀經濟及競爭秩序的管理職能;
第十,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將為上海進一步推進市場化和國際化提供新的契機,但要把由此形成的國際化效應轉化為上海創新轉型的發展動力及體制改革的促進因素,不僅需要政府的正確引導和有力推動,更需要充分調動區內外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