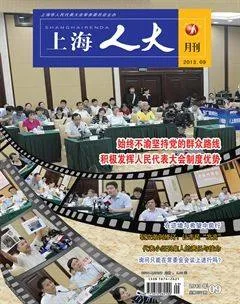文憑、年齡與破格
任何一種決策都要順應歷史發(fā)展的潮流,長期以來,在干部年輕化原則的指導下,一批又一批優(yōu)秀的年輕干部脫穎而出,走上領導崗位,為改革開放輸入了新的血液,也使整個國家保持著年輕的活力。干部年輕化是一個正確的原則,這一點無可厚非,但在執(zhí)行過程中,各級黨政機關還是要從本單位實際出發(fā),在實踐中逐漸修整這一決策,使它真正能夠成為社會和諧發(fā)展的一劑良藥。
首先在干部選拔時不能只看文憑而忽視實際工作能力。趙國名將趙奢的兒子趙括年青時鉆研兵法,在談用兵理論時,他的父親也難不倒他。后來趙王讓他代替老將廉頗出征,在長平之戰(zhàn)中,趙括因不能靈活運用兵書理論正確應對形勢變化,結果被秦軍當場射死,部下四十萬人全部被俘。類似趙括的悲劇人物還有三國時的馬謖,他們可都是學富五車的才子,得到國家權威寵信本來是件幸事,但是,被捧得太高了,就會摔得更重。因此,加強年青干部培養(yǎng),要不斷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武裝頭腦,提高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使他們切實做到忠誠黨的事業(yè),心系人民群眾,專心做好本職工作;要有意識地安排年輕干部在完成重大任務、應對重大事件、抗擊重大自然災害過程中,培養(yǎng)他們的吃苦耐勞、不畏挫折精神,提高他們協調利益關系、處理復雜問題、應對突發(fā)事件、推動科學發(fā)展的能力和水平;有針對性地把政治成熟、綜合素質良好的年輕干部安排到關鍵崗位,讓他們在更加廣闊的舞臺上施展才能,提高綜合協調能力和駕馭全局能力。
其次,在干部選拔年齡上不能搞“一刀切”。有些地方和單位把年輕化等同于青年化,在選拔年齡上搞“一刀切”,實際上是在干部選拔任用上搞“年齡歧視”。我國的法規(guī)條例既沒有一條規(guī)定年齡偏大者不予晉升職務,也沒有一條規(guī)定年輕者優(yōu)先晉升職務。就是說,無論干部年齡大小,只要在法定年齡內,決定干部職務晉升的條件是平等的,即以德、能、勤、績、廉一個標準作為統一衡量尺度,而不是年齡的大小。干部年輕化必須在遵循基本原則和法規(guī)的前提下,對那些優(yōu)秀年輕干部培養(yǎng)選拔,使其脫穎而出,而不是一種以年齡為杠杠對年輕干部優(yōu)惠,對年齡偏大干部排斥,更不是任職年齡的層層遞減。同時,在年齡上搞“一刀切”,打擊了不再年輕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一些無望提拔的干部雖然年富力強、工作兢兢業(yè)業(yè),卻感到前途渺茫、被組織拋棄,工作動力和工作熱情減退,對工作產生厭倦和觀望情緒。然而這些干部,往往是各個單位的骨干和事業(yè)的“中流砥柱”,他們工作積極性的衰退,必然影響一個單位、一個部門的工作和事業(yè)的發(fā)展。
再次,不能讓“破格提拔”成為少數人達到某種目的的借口。最近幾年之所以這個問題被越炒越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民眾對年輕干部們的能力有懷疑,對其背景也是大加揣測。實際上也有最終因“寡不敵眾”而被免職或者自動辭職的。如某地畢業(yè)三年晉為副處的袁慧中是市政法委書記的女兒;畢業(yè)半年破格提撥為團縣委副書記的常駿生是縣編辦主任的兒子;六年連續(xù)三次晉升,最后被任命為副縣長的江中詠,他的父親就是副縣長。我們不反對領導子女當官,也不是說年輕人就一定不行,能力和年齡也不是絕對成正比的。甘羅十二歲拜相、周瑜十四歲拜將,革命戰(zhàn)爭年代二十幾歲三十歲左右的高級將領,屢見不鮮,國外更是有三四十歲的總統總理。網絡時代的今天,出現一批二三十歲的年輕領導干部特別是基層領導干部,無可厚非。只要按照公開、平等、競爭、擇優(yōu)的原則,選拔那些實績突出、社會認可、德才兼?zhèn)涞哪贻p干部,就不怕爭議。群眾爭議的是有沒有后臺、背景并且暗箱操作的選拔方法。組織部門既然能“破格”提拔年齡較低的干部,就也應拿出與“破格”相符的有說服力的理由回應公眾關切。如果僅拿符合用人程序這樣的話來應對公眾質疑,組織部門選人用人的公信度必然不高。干部隊伍新老交替和合作是永無完結的歷史過程。全國各個層次的優(yōu)秀年輕干部數量仍然偏少,公眾期待選拔年輕干部的程序更加民主透明、科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