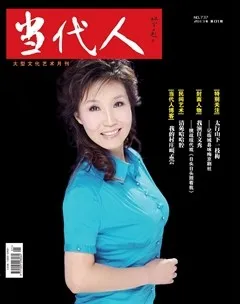唱腔的古意與現(xiàn)代味兒



我一直在思索著一個(gè)問題:為什么有的流派中某些名家唱腔中總能感覺到一種古意?另外有的流派中縱然是代表人物不論唱的是什么時(shí)代背景的戲,卻較少能品到那種“古意”,而是另外一種“現(xiàn)代味兒”?
問題一提出,有明公可能立馬會(huì)說:一定是那名家所處的年代離現(xiàn)在比較久遠(yuǎn),而后來的還健在或是離現(xiàn)在較近,當(dāng)然感受就不同了唄!
其實(shí),我指的不僅僅是唱戲人所處的年代離現(xiàn)在遠(yuǎn)近,而是他作為演員的感覺遠(yuǎn)近的問題。我心目中的一個(gè)典型例證就是程派的創(chuàng)始人程硯秋。程先生所灌制的唱片我在青少年時(shí)期就已聽過,但使我感受極深的是他生前所拍的唯一的影片《荒山淚》。說實(shí)話,如果單從面容和體態(tài)上看,拍電影時(shí)肯定不是程先生最俊美的時(shí)期,然而我并沒有著意于先生的扮相,而是潛心品味他唱腔之精髓。當(dāng)然,我們?cè)缇蛷脑S多業(yè)內(nèi)人士和評(píng)論家的文章中領(lǐng)略到對(duì)程腔的評(píng)價(jià),無非是幽咽斷續(xù),韻味濃郁,乃至對(duì)他運(yùn)用“腦后音”的推崇,等等。這些我大都是贊成的。但我特別感覺到,程先生唱“古戲”就是地道的古戲。他作為演員本身雖還夠不上是個(gè)古人,但他的聲腔意韻分明將劇情的時(shí)代、環(huán)境和人物的特定感情都傳達(dá)出來了。也就是說,許多演員(包括某些名演員)也可能唱出應(yīng)有韻味,而程先生還能唱出古代人物特有的意韻。古人的意韻是什么?今人誰經(jīng)歷過那個(gè)時(shí)代?答曰:雖未親身經(jīng)歷過,卻能從合理的想象中體味到幾百年以至上千年的時(shí)代環(huán)境與人物的離合悲歡;雖未親身經(jīng)歷過,卻能從間接的知識(shí)、遺存的發(fā)現(xiàn)中感受到那個(gè)時(shí)代人物與現(xiàn)代的異同。只要恰到好處,傳達(dá)出想象中應(yīng)有的真實(shí),便會(huì)得到有心人的認(rèn)可。從程先生的唱腔中,確能認(rèn)同他是一位現(xiàn)代演員穿透時(shí)空的樊籬而進(jìn)入那個(gè)時(shí)代環(huán)境,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具體人物在傾訴自己,而已遠(yuǎn)遠(yuǎn)超越了演員自身。
那么,在唱腔中如何能夠滲透著濃濃的古意?我覺得這是一個(gè)素質(zhì)與學(xué)養(yǎng)的問題,是一個(gè)演員以自己的靈性去熟識(shí)歷史,感受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結(jié)識(shí)”那個(gè)歷史環(huán)境中的具體人物,使自己的聲音變成了從屬于那個(gè)時(shí)代的天籟之聲,成為本人的心靈與歷史人物完全融合的產(chǎn)物。而舞臺(tái)只不過是連接古今貫通時(shí)空的載體。
毋庸諱言,程硯秋先生能夠達(dá)到的,不等于凡宗程派唱腔者都能達(dá)到。在程派傳人和再傳者中間,有的肯定在相當(dāng)程度上已得大師之三昧,但更多的情況卻不是那樣。只能說是抓住了容易學(xué)到的表面上的突出特點(diǎn),但究其實(shí)質(zhì),還是內(nèi)外兩張皮。唱的是古戲古人,但聽起來仍是穿古戲裝的今人。為什么?很簡(jiǎn)單,還是一個(gè)素質(zhì)與學(xué)養(yǎng)的問題。同樣是非止個(gè)別的比較年輕的演員對(duì)劇目有關(guān)的古代知識(shí)比較匱乏,有的還自得于能夠受到觀眾認(rèn)可,覺得時(shí)代不同了,京劇越是“現(xiàn)代味兒”越會(huì)受到群眾歡迎。其實(shí)這是一種誤區(qū),一種十分淺近的意識(shí)。譬如說,我們不能因?yàn)橛胁簧偃瞬粣劭垂盼奈镎褂[,就可以認(rèn)定舉辦這樣的展覽沒有意義;我們更不能因?yàn)橛腥瞬幌矚g歷史課,就可以得出學(xué)歷史不必要的結(jié)論。
在從事古典戲劇如京劇的“角兒”中,絕不只有旦行如程硯秋先生的唱腔透著古味。近百年來,不少的生行和凈行名家也具有這種品格。我還發(fā)現(xiàn)一個(gè)有趣的現(xiàn)象,有的名家的唱腔聽起來并不那么流利滑潤,甚至還帶有“毛刺兒”(借用加工零部件的工業(yè)技術(shù)詞語),卻就是古意十足。另外,也不是說平時(shí)的日常生活中表現(xiàn)泥古崇舊,上臺(tái)唱戲才能古意十足,同樣未必如此。如上個(gè)世紀(jì)前期的著名女老生孟小冬在卸妝后穿著相當(dāng)“現(xiàn)代”,在那個(gè)時(shí)代中恐怕還應(yīng)是比較時(shí)尚的,但一唱起戲來,唱、念、做都是一派“古人”的氣度。
相反,我也看到另有一些演員(有的可能已步入名家行列),演的并非是現(xiàn)代戲,而是地道的傳統(tǒng)劇目,可能還帶有自身的優(yōu)點(diǎn)與所長,譬如很響亮很華麗,或者是十分流暢、非常高亢等。這樣的一些特色無疑能夠形成為風(fēng)格,甚至被譽(yù)為某個(gè)流派亦有可能。但我仍然不掩其短,稍許嚴(yán)格一點(diǎn)加以評(píng)判,聽來聽去就是缺少古典戲曲應(yīng)有的古風(fēng)古意,如不掌握應(yīng)有的度而大加“發(fā)展”下去,便與現(xiàn)代“戲歌”相去不遠(yuǎn)了。從這個(gè)意義上講,一種“風(fēng)格”縱有九個(gè)優(yōu)點(diǎn),唯缺了上述之一項(xiàng),也無形中減了不少分?jǐn)?shù)。我認(rèn)為。
言至此,我忽然想到一個(gè)道理,文學(xué)也好,戲曲唱腔也好,言其“流暢”從一定高度來衡量也可能是個(gè)優(yōu)點(diǎn),但如太過,弄得不好反會(huì)與“流于一般”搭界,與真正的大家更拉開了距離。所以我還是要啰嗦一句:不論你生活在哪個(gè)世紀(jì),你唱的可是古典戲曲啊!
(責(zé)編:郭文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