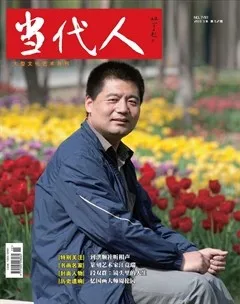父親的竹笛能“吹破天”

在父親馮子存早年活動(dòng)的張家口一帶,人們都叫他“吹破天”,因他吹笛子的造詣無人能及。他的前半生,身背一支竹笛顛沛流離四處賣藝;他的后半生,得以進(jìn)入中央音樂學(xué)院、中國(guó)歌舞團(tuán)教學(xué)、演出。對(duì)一位貧苦出身的民間藝人來說,父親無疑是幸運(yùn)的。
將笛子獨(dú)奏搬上舞臺(tái)第一人
1953年,是父親人生的一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
這一年4月,父親作為河北省代表,參加了全國(guó)第一屆民間音樂舞蹈觀摩會(huì)演。他演奏了《放風(fēng)箏》、《喜相逢》兩首笛子獨(dú)奏曲。
不論是普通觀眾還是藝術(shù)家,誰(shuí)都從未見過,原本都是用作伴奏的竹笛也能單獨(dú)演奏,并且旋律能夠如此豐富、花樣百出。父親在吹奏《放風(fēng)箏》時(shí),自創(chuàng)的“飛指花舌”音,能模擬出風(fēng)箏的升起和降落。而《喜相逢》這首原來流傳于內(nèi)蒙古的民間樂曲,原本是河北梆子、二人臺(tái)等地方戲里的過場(chǎng)音樂,在父親的吹奏下,成為一首表現(xiàn)情人別后重逢心情的曲子,而且愈到最后,他吹奏的速度愈快,情緒也愈加熱烈。
父親音色嘹亮、豐富純熟的演出技巧贏得了觀眾的掌聲,也因此獲得了這次匯演的一等獎(jiǎng),并且被評(píng)為優(yōu)秀演奏員。
這次演出被電臺(tái)反復(fù)播放,人們從當(dāng)時(shí)還為數(shù)不多的半導(dǎo)體里,都聽到了這兩首笛子獨(dú)奏樂曲。
父親成為全國(guó)首位將笛子獨(dú)奏搬上舞臺(tái)的藝術(shù)家。自此,很多文藝團(tuán)體竹笛演奏者們也開始學(xué)習(xí)笛子獨(dú)奏,最先學(xué)的就是父親吹奏的這兩首曲子。
這一年7月,父親被調(diào)到中央音樂學(xué)院音樂工作團(tuán)。年底,他又隨同中央音樂學(xué)院音樂工作團(tuán)一起調(diào)入中央歌舞團(tuán)(今中國(guó)歌舞團(tuán))。
從一個(gè)民間藝人成為國(guó)家級(jí)的文藝工作者,父親無疑是非常幸運(yùn)的。如果他沒能參加那次匯演,如果當(dāng)時(shí)的宣傳隊(duì)長(zhǎng)沒有別出心裁想出“獨(dú)奏”,父親也許會(huì)像大多數(shù)民間藝人一樣,雖然才華橫溢,但依舊湮滅無聞。
父親的藝術(shù)完全來自民間。
吹不成就不吃飯不睡覺
父親1904年生于張家口陽(yáng)原一個(gè)貧苦之家。據(jù)父親回憶,小時(shí)候從未穿過新衣服。父親14歲開始跟隨大哥學(xué)吹笛子,也跟著大哥到張家口、尚義、張北一帶賣藝演出過。當(dāng)時(shí),尚義一帶流行“東路二人臺(tái)”,通常以笛子為伴奏。父親不識(shí)字更不識(shí)譜,但是他非常聰明,白天聽別人吹奏一遍,便能記下,晚上就躺在炕上把白天記的曲子自己哼唱出來。
有時(shí)候看到一些民間演出,聽完一遍馬上就拿起自己的笛子吹奏,他要求自己和人家吹得一模一樣,如果吹不成,就不吃飯不睡覺。
祖父病故之后,父親和幾個(gè)藝友到尚義縣賣藝求生。父親一般是和別人搭戲班,作為“二人臺(tái)”笛子伴奏,他們到過察哈爾、內(nèi)蒙古、山西、門頭溝,還到過北京的天橋。但是這些戲班合合散散,沒有定數(shù),父親也常常是不斷轉(zhuǎn)換地方,帶著自己的竹笛四處奔波。
張北、內(nèi)蒙古一帶常年氣候寒冷、風(fēng)沙彌漫。父親練就了一身頂風(fēng)吹笛氣不散的本領(lǐng),得了個(gè)“吹破天”的名號(hào)。一有演出,好多人從幾十里外專門跑來看,就是為了聽“吹破天”的笛音。
可以說,父親的笛曲風(fēng)格是在張北一帶的民歌、山西梆子、二人臺(tái)等民間音樂和戲曲的熏陶下形成的。通常,他的演奏力度很強(qiáng),比別人要高出幾十個(gè)音分,甚至半個(gè)音。另外,歌唱性是他笛曲的特色。北派梆笛風(fēng)格高亢、嘹亮,父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沒有演出就沒有飯吃
父親到中國(guó)歌舞團(tuán)工作后,有一次隨同演出隊(duì)到山西演出,每天跋山涉水七八十里路,當(dāng)時(shí)他已經(jīng)50多歲,也和年輕人一樣,裝臺(tái)、卸臺(tái)、裝馬車,毫不含糊。在貧困山區(qū)每天只能吃兩個(gè)糠窩窩,年輕人抱怨,父親卻唱起了“爬山調(diào)”,為演出隊(duì)鼓舞士氣。
對(duì)父親來說,這點(diǎn)苦頭和之前他流浪賣藝相比不算什么。那時(shí)候沒有演出就沒有飯吃,就著雪吃冷饃的事情再平常不過。除了饑寒,還有其他辛酸。1935年,父親結(jié)束了自己的漂泊,在尚義開了一個(gè)小雜貨鋪。有一次,一隊(duì)國(guó)民黨兵路過,搶了父親的鋪?zhàn)樱€把他的笛子搶走了。那時(shí)候,他連買一支笛子的錢都沒有,此后兩年都沒有笛子吹。
因而,他對(duì)新生活的渴望和感恩異于旁人。
尚義縣解放時(shí),父親和許多藝人一樣,加入了慶祝的行列,他們編演了很多新的劇目,宣傳新生活。后來他干脆賣掉了雜貨鋪,參加了“察哈爾察北區(qū)文藝宣傳隊(duì)”,成為一名專職的文藝工作者。
自己掏錢買笛子送給“粉絲”
我從懂得認(rèn)字開始,就幫父親讀信。父親每天都要收到從全國(guó)各地來的幾十封信。大部分都是求教信,有專業(yè)學(xué)笛的,也有業(yè)余愛好者。那時(shí)候,馮子存名聲很響,他如同現(xiàn)今的明星一樣,擁有許多的“粉絲”。有的來信者說自己喜歡笛子,但是買不到合適的。父親還會(huì)自己掏錢買笛子,寄過去送給人家。
到家里來的人也很多。有的拿著單位的介紹信,有的干脆就直接登門。父親一向來者不拒,有求必應(yīng)。不過,因?yàn)闆]有文化,對(duì)音樂理論的知識(shí)很多可意會(huì)卻無法言傳,經(jīng)常是他的學(xué)生霍偉等人在一旁幫忙解答。來人到家里來,跟隨他學(xué)習(xí)笛子,一到飯點(diǎn),他就吩咐保姆多做飯,一定要留人吃飯。
父親為人隨和,從來沒有和別人發(fā)過脾氣,教笛子的時(shí)候更是這樣。不過,父親的笛子很難學(xué)。
父親的演出很即興,即使是同一首曲子,每次吹奏都不一樣。中央音樂學(xué)院的方堃老師說,不如把它們編曲。于是,由父親演奏,方堃編曲,這樣才有了后來的傳世曲目《喜相逢》。之后,在方堃、霍偉等人的幫助下,父親得以譜下《對(duì)花》、《鬧花燈》、《五梆子》、《春耕》、《黃鶯亮翅》等幾十首曲目,很多成為笛子獨(dú)奏曲中的經(jīng)典曲目。
每天醒來就去摸笛子
父親卻從不讓我學(xué)笛,在他們那個(gè)年代沒有女孩學(xué)習(xí)管樂,所以“傳男不傳女”。父親在老家的侄兒馮順兄弟兩人則繼承了父親的技藝。他對(duì)侄兒非常照顧,經(jīng)常寄錢給他們。但是由于演出繁忙,他沒有能夠更多地指導(dǎo)侄兒。馮順大哥后來參軍,在部隊(duì)上也是文藝骨干,復(fù)員之后,他也想調(diào)到縣里或者張家口,專門做文藝工作,但是父親說,不愿意給黨添麻煩,讓他們?cè)谵r(nóng)村鍛煉吧。于是,馮順大哥一輩子都在農(nóng)村,到如今已經(jīng)三十年沒有再吹笛子了。
1969年,以“戰(zhàn)備疏散”為名,我們一家人被迫回到了陽(yáng)原老家。父親除了務(wù)農(nóng),更多的還是搞他的笛子演奏,母親是京韻大鼓表演藝術(shù)家。他們倆人到村里的小學(xué)做音樂老師,教孩子們唱歌吹笛子。父親到中國(guó)歌舞團(tuán)以后工資待遇很高,所以他有一些積蓄,在鄉(xiāng)里無論誰(shuí)家有困難,只要求到他,他從來都沒有拒絕過。
到上世紀(jì)70年代我們又重新調(diào)回北京。那時(shí)父親已經(jīng)70多歲,淡出舞臺(tái)。但他袖筒里面永遠(yuǎn)都帶著自己的笛子,所以別人看到他左臂總是直的,不能彎曲。只要有人說“馮老來一個(gè)”,他就馬上從袖筒里取出笛子滿足大家的要求。
父親對(duì)笛子鐘愛一生。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拉開床邊的抽屜,摸出他的笛子,吹奏一曲,到晚年身體十分不適,即使只能吹一小會(huì)兒,他也從不間斷。
(感謝中國(guó)歌舞團(tuán)離休干部霍偉、太原師范學(xué)院教授任俊文及馮子存侄兒馮順接受采訪并提供資料)(作者單位:河北青年報(bào))
(責(zé)編:劉建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