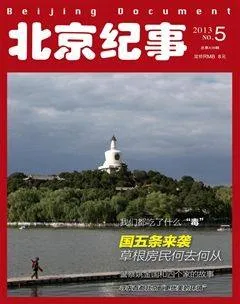王盼:我眼中的張派藝術
王盼,女,漢族,北京京劇院演員,工青衣,張派傳人,第五屆青研班學員。2003年至2007年在中國戲曲學院學習。師從蔡英蓮、王蓉蓉、孟憲榮、劉秀芳、楊秋玲、李維康、沈健瑾、張毓文、張晶等。2006年7月29日正式拜蔡英蓮教授為師,同時在蔡英蓮教授的推薦下正式拜著名張派表演藝術家王蓉蓉為師。
代表劇目:《秦香蓮》《狀元媒》《望江亭》《玉堂春》等。所獲獎項:2000年獲天津市京劇大賽專業組一等獎。2001年天津市第十二屆文藝新人月新苗獎。2005年獲CCTV第五屆全國青年京劇演員電視大賽熒屏獎。2005年在紀念京劇大師張君秋誕辰85周年活動中被評為藝術新人,在此活動中同時被評為張派藝術新秀。2008年獲CCTV全國青年京劇演員電視大賽銀獎。2012年獲CCTV第七屆全國青年京劇演員電視大賽金獎。
張派的難點
王盼說張派的唱腔對嗓音的要求很高,如果開口音不好,很難完成張派的行腔。張君秋先生的嗓音條件極佳,而且音色絢麗,高亢甜美,演唱時舒展自如,所以形成了華麗柔美、剛健清新的獨特風格。他能夠利用天生的好嗓子,高低虛實結合,而且過渡得十分平滑。實際上,這也反映出張先生用氣的技巧高超。巧妙地蓄氣、緩氣、偷氣,張先生運用得非常自如。先生的嗓子,音色俱全,處理行腔轉換流暢、若斷若續,放聲聽來,如飲“甘露”,“羚羊掛角,了無痕跡”。張派藝術,曾有人形容其唱法為“點唱法”,如蜻蜓點水;又似“棗弧形”強弱回旋,有許多從事西洋聲樂的研究專家十分欣賞張派的發聲,認為在京劇演員中,張派的發聲最符合科學的發聲方法。
因為張派的旋律靈活、明快,上下起伏比較大,所以氣息的運用非常重要。“聲隨氣行,以氣催聲”。用氣來控制聲音的強弱粗細,隨著氣的運行,唱出千變萬化、美妙自如的聲腔。
另外,由于男性嗓子的生理構造與女性不同,男性發聲用氣通常比女性足。在張派的劇目中有許多張口音的唱腔,特別是一些唱段結尾處的高音張口音,更需要很足的氣息;而一般女性閉口音比較好,氣也沒有男生足,所以想完成好張派的每一個行腔,需要下很多功夫——能否把張派的張口音唱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張派唱法水平的高低。
王盼上中專時學的是梅派,梅派的行腔相比較平穩,發聲位置比較集中。進了大學后,王盼開始學張派,張派是在梅尚程荀四大流派之后成立的一派,明顯地吸收了梅派唱腔中的甜美華麗、舒展大方的特點,又繼承了程派唱腔婉轉迂回,細膩深刻的特點。而張先生所演唱的快板又具有尚派的那種流利順暢、明快清晰、節奏靈活的特點。又有荀派演唱收音的俏麗之美。所以張派是博采眾家之長的流派。在張先生的唱中,高亢能寬亮、低婉能打遠,其原因是他成功地運用了胸、口、鼻、腦后等共鳴,這樣唱既省力,又打遠,還寬亮。
靈活學習,回歸人物
王盼上大學后,帶著梅派的基礎學張派,似乎重新開辟了另一條起跑線,重新起跑。我問她何時跳出梅派的影子,完全成為張派演員?她說:“談不上‘跳出’,把張派學好,同時保留梅派的精華也很好。”王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竟道出了張君秋先生對京劇傳承的看法——不拘泥,不固守,靈活地學習掌握。
有這樣一個故事,當年有幾個青年演員到張君秋先生家里學戲,向他詢問一個動作。她們中間曾有過爭論。有的說,張先生在這里走兩步,這是“張派”;有的說,不是兩步,而是三步,這才是“張派”呢。雙方都出于對張先生的尊重,想一絲不茍地學習他的藝術,由此而發生爭執,希望他為她們評出個是非來。當時,張先生很為難,說實在的,臺步的多少,他自己并沒有一個嚴格的規定,有時候臺大就多走一步,臺小興許就少走一步。張先生自幼在老師家里學戲,14歲跟李凌楓先生,后來又從王瑤卿、閻嵐秋(藝名“九陣風”)、朱桂芳、張彩林、姜玉佩、朱傳茗、鄭傳鑒等先生學戲,也拜過梅蘭芳先生,還向程硯秋、尚小云先生學過流派代表作。他在臺上的藝術,許多都是以上幾位先生教過的,但細想起來,許多又不都是他們教的。并沒有完全按著先生們教的去做,反而漸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有了張派。
她的老師蔡英蓮、王蓉蓉曾告訴王盼,要科學地學習張派,不要一味地模仿張先生,把戲學死了。學習的同時,多了解自己嗓音的特點,要把張派的特點和自己的特點結合起來,這樣才能通過自身的優勢把張派詮釋得更好,才可能把張派發揚光大。當然,靈活地學習并不意味著忽視規范。張先生也強調,對于青年演員來講,第一步是要把前輩藝術家的藝術真正學到手,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再不斷創新,有所發展。所謂的創新,不是為創新而創新,更不是在學習的時候,為了省勁,避免了對難度較大的藝術的刻苦鉆研而去走捷徑。這樣做,不是張先生提倡的。
王盼說,學習張派不僅要靈活,還要像張先生那樣,對劇中的人物盡心揣摩,注意細節表現人物。曾經也有觀眾稱贊某某演員是“活曹操”“活趙云”,那是因為演員對歷史材料作了深入的研究。我們也應該對張派的不同劇目、不同人物進行分析和區分,演出的個性不能千人一面,要注意內心的細膩,通過不同的板式惟妙惟肖地展現出人物的不同情緒。例如:張派代表作《狀元媒》一劇中“天波府”一段唱表現了柴郡主對救駕小將多次贊許產生了曖昧之意想托付終身的纏綿情緒;在“自那日”一段中柴郡主在宮中獨自傾訴她對愛情的美好向往,也體現出女子內心躍躍欲試的柔美之情。直到“到此時”一段中人物的情緒有了大幅度的變化。運用了“導板”通過尾腔的高亢抒發柴郡主的無奈之情,也表現了她對真愛的向往。最后一場金殿中“西皮流水”“付丁奎休要發癲狂”一段表現了柴郡主氣憤之情,當眾揭穿騙局,也體現出人物直率自主,愛憎分明的人物性格。只有對人物精心的揣摩,才能通過技術塑造出有血有肉、性格鮮明的藝術形象。作為演員,要對得起每一位來看戲的觀眾,在舞臺上的每一刻都容不得有一點馬虎。
采訪最后,王盼說:“我們在繼承張派、學習張先生的戲時,不能忘了他的精神、他的觀念,還有他對美的那份執著的追求。”
(編輯·韓旭)
hanxu7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