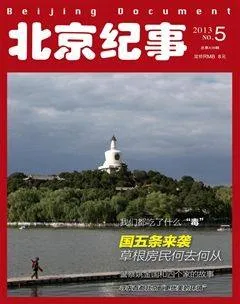在澳洲又見龍泉青瓷
2013年3月,我這個連26個英文字母都忘卻很久的人,去了澳洲自助旅行。由于不懂英語,我就靠一張當地中英文地圖,連猜帶蒙地參觀了博物館、美術館。澳洲的生態之美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澳洲人是在森林里插花地蓋幾棟房子,而我們國內則是在水泥森林中插花地種幾棵樹。
在悉尼,為了體驗一下悉尼歌劇院,我特地前去尋找悉尼音樂會的票。來到售票處一問,兩周前已售完。心中有些不甘心,于是留下來等著退票,沒想到竟真的等到了。這部音樂會以人類在太空飛船中生話的記錄片為音樂背景,整個樂隊在指揮帶領下以即興的方式,為懸浮在太空的靜寂時空襯上一抹淡淡的色彩。這種形式令人想起默片時代,只是歷經百年時光后,影像和音樂落在人心中的情感早已截然不同了。
澳洲的第二大城市墨爾本,保留了百年歷史的環城有軌電車,且還是對全城免費。作為一個外來游客最經濟的旅行方法,是先在地圖上標好想去的地方,然后找到環城電車停靠車站,離目的地最近的那一站,剩下的路只需拿著地圖,指著標記問當地人即可。對一個如我一般不會26個字母的人一樣可行。
當我背著包手持地圖“撞”到維多利亞洲博物館時,竟然在此巧遇了我國北宋的三件龍泉青瓷。第一件是一個龍泉窯褐斑蒜頭瓶,其器身修長,施釉肥厚,釉色青中帶黃,器身布滿不規律的大開片,釉色溫潤。釉色青中帶黃應是龍泉窯在南宋時期窯工在摸索試燒粉青和梅子青時對釉中鐵元素含量控制不準的結果,如果以此標準斷代的話,這件龍泉窯褐斑蒜頭瓶應在南宋末年和元代初年之間。展品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粉青釉立耳三足香爐,其釉色之美令人嘆為觀止,釉似堆脂,其色晶瑩如玉。其工藝美學無疑已進入到登峰造極之境。其技藝實現了將宋元時期以質以純為標準傳統審美之精神,開創了單色釉瓷器進入廟堂祭祀先河。(廟堂祭祀由青銅轉而為瓷器祭祀自南宋始。龍泉青瓷進入國家禮器等級)而第三件梅子青斗笠碗則是從技藝的角度為當時的人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不同色質的審美空間。
什么叫彈指一揮間?我站在這個時間點的坐標上,上推北宋,距我已有千年!人生若以百年記,我已然活了十輩子了。館中的龍泉青瓷以沉靜似玉的目光隔窗與我相望。龍泉之美在異國他鄉一下點燃了我的思鄉情懷,那無言的淺淡之綠,幻化成青青未熟的梅子,虛擬的酸澀填補了心中的饑渴。粉青之色從有質感的實用器物一下上升為慰人心靈的形而上的靈藥,附著其上的是文明之美。
兩年前有一次偶然看到電視片,令我邂逅了龍泉青瓷的前世今生。片中介紹了有個叫葉英挺的古陶瓷愛好者,在2005年4月份的一天,在杭州二百大市場外面的一個樓梯口的轉彎處,發現了一個放了一大堆青瓷片的攤位。葉英挺以500塊錢買下了這一堆瓷片。葉英挺持瓷片陸續走訪了省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專家。正是這堆瓷片引發了古陶瓷界對龍泉青瓷的再認識。
2005年11月,一則龍泉發現了明初官窯的消息,轟動了陶瓷界。隨之而來的是在學術界和收藏界引起真假爭論。與此同時,在2006年新年初始,世界各大古玩市場里,被認為是官窯所產的龍泉青瓷,一時身價倍增。
一年前有位朋友從我處拿了一把龍泉粉青釉執壺,回去后請當地專家鑒定,專家是四川人,看了后說了句開門假,疑點有三,一是分量重了,二是釉面失透缺少玻璃質感,三是壺身手柄處有釉剝落,剝釉處不像是日常接觸和磨損造成的,且有當地出土的龍泉殘片作支持,殘片和執壺比,果然玻璃質感強。專家是以當地出土器為標準來比對器物的真假,這在收藏界叫目鑒,問題只是目鑒者所擁有的資料是否有限。
龍泉青瓷為什么有著那種青玉般的色彩?早在1959年,輕工部、浙江輕工業廳邀請中科院上海硅酸鹽所等單位對龍泉青瓷進行了專項研究,樣品涵蓋了從五代至明各歷史時期。從技術層面講,古代龍泉青瓷大體可分為石灰釉和石灰堿釉。前者產于五代和北宋,后者產于南宋、元、明。石灰釉的特點是高溫下黏度比較小,易于流釉。龍泉青瓷一般施釉較薄,氣泡和未熔石英顆粒少,釉層顯得透亮,釉光較強。石灰堿釉則高溫黏度較大,高溫下不易流釉,這樣釉層可施得厚一些。用顯微鏡觀察,可見釉層中含有大量氣泡和未溶石英顆粒,正是這些顆粒在光線進入釉層時令光線發生散射,從而使其外觀產生有如青玉一樣的效果。
四川專家的判斷顯然受限于他的眼界和見識。
龍泉進入現代人眼中的歷史要倒推到上個世紀50年代。當年馮先銘先生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庫房里,發現了幾件從前沒有留意過的瓷器,它們的表面滋潤豐腴,釉面呈青青翠色,大部分用刻花文飾,據傳這是傳世的元末明初龍泉窯貢器,文獻記載,它的產地就在浙江龍泉。這種非同尋常的瓷器,究竟產自龍泉的什么地方?若能夠找到窯址,龍泉官窯的疑問才能水落石出。
1976年的夏天,一位韓國的漁民在出海打魚時,無意之中撈起了一個古色的木箱,緊接著,他們發現了許多精致的中國瓷器。令人震驚的是,他們竟然發現了幾件與故宮里龍泉青瓷極其相同的瓷器。神秘的龍泉官窯再一次激起人們的好奇求解之心。
1984年夏季,在北京四中的基建工地上。考古人員發現了大量的明洪武青花、釉里紅和龍泉青瓷瓷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青瓷瓷片與普通的龍泉青瓷瓷片不同,多是中心印花,壁刻纏枝花的大中型盤碗,并采用裹足墊燒的工藝。這與故宮傳世的龍泉窯有很多相似之處。而這里原來是明清兩代的宮廷庫房區。這一研究成果歷經20年于2004年由著名漫畫家、古瓷鑒賞家畢克官編著成《古瓷探妙》一書出版發行。
2006年1月,為了確定龍泉官窯的確切年代,中國科學院的專家決定用微量元素分析法,將流到市場上的龍泉青瓷瓷片進行斷代。經過物理和化學特征的分析,這些瓷片大約燒制于600年前,誤差為正負50年。從此,這些帶著身世之謎的龍泉青瓷,終于有了答案。
時間已不可考的21世紀,龍泉大窯村的一個村民在一個名叫峰洞巖的地方,種植農作物時無意中挖出一些青綠色的瓷片。隨后,村民在附近的田野中還發現了相對完整的瓷片。經過整理,在同一地方出土的瓷片竟然可以完全復原起來。龍泉窯的窯址終于浮出水面,龍泉窯的確設立過官窯。
我站在澳洲維多利亞洲博物館里,恍惚間穿越千年時空回到大窯村,河邊傳來石槌粉碎瓷石之聲,依山而建的龍窯已燃起窯火,松柴之火由紅而白蜿蜒而來,已燃了千年。
(編輯·宋冰華)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