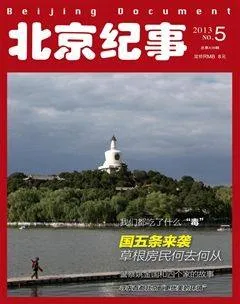公交座兒上的北京
我對煙臺印象特別好的原因在于高中時候的一次單獨旅行。一個人,背了仔包兒到山東半島閑逛。煙臺市里,公交車上,有小伙子起身讓了個座位給一位老人。那時候的煙臺于我有鄉下的感覺,市容比不得北京漂亮,公交車也遠遜于北京——盡管北京的車也真好不到哪兒去。
就是那一次讓座,讓我喜歡上了那座小城。盡管那座城市里充滿了嗆人的海腥味,滿眼沒一輛不生銹的自行車。
線少車少還是什么原因,十六七歲時,我身后北京城里的人們正咬著牙跟公交車較勁,扒門、愣擠、硬沖。從不高于6層的樓里,從斗折蛇行的雜院,從同一個模子翻扣某廠的排排宿舍中,鉆出一兩個零星疾走的人頭,流入胡同,匯集到一個個銹蝕的站牌下,伸長脖子等著。黑壓壓的陣勢,猶如瀕涸水洼中仰頭吞水延命的魚。車來,沒等進站,人群開始移向門子,很多手從人縫兒中急切地探出來抓夠,一旦攀住車身,人,興許瞬間就騰了空。所以那時公交兩門子之間擋風的橡膠封條永遠都甭想齊整,里出外進狗啃的一般。上了車的盼著快開,沒上車的扒門喊著號子往上擁——我上不去,誰也甭打算走。一趟車,因僵持而暫停個一刻鐘半小時是常有的事兒。
上車成了天然的濾網,身強體壯的尚且打怵,老弱病殘自被濾到車外——跟孕婦一同車下做著怨婦版的興嘆。
缺了讓的對象,座兒讓給誰去?
所以那時的北京被稱為自行車王國。很多人寧可騎車穿城上下班也不樂意去跟公交搏命。國企沒改制的時候,你經常可以看到爸爸騎著自制加了玻璃窗的側拖斗的自行車,帶著閨女兒子上下班。爸爸進車間,孩子進企業自辦的幼兒園。
羊剪絨帽子、棉手套、離座兒微躬之身以及掛在胡茬兒上的白哈氣,北風里定格成獨屬于那個時代的出行畫面。
城猶如一個粗瓷大碗,上班一股浩蕩洪流,下班一股浩蕩洪流,中間是售票員含混不清報著站名的紅白藍白拖著大辮子不拖辮子的公交車。這渾濁,以上下班為高峰定時攪裹,逐漸分不清季節時令,變成一個找不到中心的大旋兒。原本安靜地臥在燕山山麓臂彎內的那個大碗,亦被逐漸撼動,讓大旋兒帶著在華北平原這張大桌子上踉蹌晃蕩,變成了陀螺。
緩慢旋轉的陀螺,吸納著被時代甩出去的那些年輕人——我指的是回城的知青,以及逐漸長大加入就業大軍唇上茸毛未硬的半大孩子。當時有一個專用名詞稱呼那些人:青工。青工是進入到就業高峰期沒有預留設計好就業通道的社會對一個群體的獨特稱呼,那個群體被質押在一個相對狹小板結的空間內,青春的活力只能以在獨屬自己的群體內不停地制造冤仇消解摩擦來釋放。而狹窄擁擠的公交車給他們提供了外在的客觀條件。所以因為爭搶一個座位而大打出手的事件每天都會上演。每條線路每輛公交上的這些事件,猶如春節雪夜中的爆竹——時不時炸一個,時不時炸一個,驅趕節日空曠的寂寥,引起些隨炸隨平的小騷亂。我的姨父,一個旗人,家住菜市口附近的勝利巷,工作單位在大山子,每日陪他上下班的居然是一把鋸成短把兒的小鐵鍬。
破舊的公交,呼哧帶喘追車,前擠后擁,無座可讓,是那個時代給我的記憶。
公交車比北京城更早地進入到了充滿競爭味道的商業社會,或者說公交車是北京城探入商業社會最早的幾根觸須之一。遠離公交,人們相對安詳與和氣;一旦不得不選擇公交出行,窘迫逼著眾人去爭去搶,蠻力等于空間,空間愈大安全感愈強。
成天在那樣的環境里工作,給司售人員以良好的心理訓練。6路車里,一個被打得滿臉是血的年輕人趴在車里久久不動,售票員依舊賣她的票跟乘客戧嘴,司機說:“要是沒死,起來別老趴著啦,時候長了凍上還得開水澆,多費事兒啊!”
見怪不怪生成冷漠的原因在于其多發,在于其常見。所以你就不難理解當時應景而生,富于引導意義,教育大伙兒愛崗敬業的相聲演員們為何總愛拿售票員當反面教材抓哏了。要是您聽過幾回那時候北京售票員與初來北京外地人之間的對罵,恐怕不難產生與我重合些的判斷:北京人優越感與排外思想的初發與北京的售票員脫不清干系。
由國家統管一切的圈養到打開籠門的散養,80年代北京人對社會變革的默默接受遠沒有旗人倒了鐵桿老米樹一般炸窩。商業社會猶如一團濃霧兜頭罩下彌散開來,捶胸跺腳地咳嗽搶天呼地地咒罵——濃霧中也有,跟霧一樣蒼白且無處懸掛。濃霧很快散盡,矗立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陌生世界,這個世界新得有些令人不敢相信。不適感被瞅哪兒哪兒新鮮的好奇壓著,暫時沒能翻了塘。捏著手里忽然富裕出的一些錢,人們蜂擁著考本兒買車,從面包兒夏利一路頂到了廣本。等走哪兒哪兒堵,哪兒停都有罰款條兒的細槍管兒瞄著,還別說汽油超猴兒價,更遑論掉雨點兒淹車捎帶著死人……真膩煩!真膩煩!拍腦門子想起了公交,登車一看,說不清從啥時候起,北京公交一夜間變成了外地人的通勤專列。
奧運帶給北京的福蔭包括四通八達的公交建設——加站增線的幅度史無前例。這些福利屬于居住在北京城的所有人——不分外地還是土著。部分獨屬于北京人的特權(比如月票制度)在慢慢攤薄的城市中逐漸解禁,侵蝕那些剩得不多北京人的優越感。你花4毛錢能從八王墳到公主墳,別人同樣也能。錢,不但能通神,還能一卡通。
還有一個現象很值得注意,奧運之后,北京城里的老人忽然一下子多了起來,非高峰期,每輛公交車有20個乘客,白發老人能占12個以上的名額。那景象頗有點兒辦完人生最后一樁大事兒殫精竭慮之后的大松心。大松心能令人年老,年老當然要有個證明。老年證能當錢使,而免費乘車大小都是個誘惑。
出家門走七步,坐上公交逛馬路;逛馬路總眼暈,爬爬香山解解恨。公交的免費給老頭兒老太太們帶來新的生活境界——大半輩子都得捏著錢出行,沒錢寸步難行的老理兒真真要改——老年證一亮,甭說售票員,公園收門票的都得耷拉眼皮。
(編輯·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