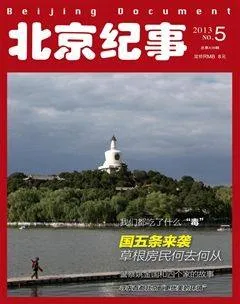王碩:為師為人,鏗鏘有力
王碩講話的語調恰如他的司鼓,充滿了節奏感。娓娓道來時蜻蜓點水,意欲強調時擲地有聲。這么引人入勝,我想他的學生聽起課來一定不會開小差兒。采訪前他列了一個提綱,采訪時條分縷析地按著提綱一條條說開去,邏輯嚴謹,藝海人生、教學心得無所不包。他說年輕時他拜望“鼓王”白登云先生,白先生說:“我這一輩子就是‘認真’二字。”再看鏡頭前的王碩,熱情滿滿地介紹司鼓文化,口若懸河。他在京劇伴奏這方面懂得太多,所以有時會越說越遠,時不時看一眼提綱,保證自己不離題,把該說的都說到了——透著認真。梨園有句老話:若要學戲,先學做人。我能在王碩的身上看到白登云先生的那種品質,那種做事認真的態度,不做則已,要做就盡力做到最好。
結緣打鼓佬
王碩生在梨園世家,爺爺王泉奎是有“金嗓銅錘”之譽的花臉前輩,姥爺李春林是梅(蘭芳)劇團的大管事。父親王志廉是老生演員,后在北京戲校任教。母親李文敏同樣在北京戲校任教,乃桃李天下的程派名師。王碩在這樣的環境里成長,童年時光充滿了京劇的記憶。
上世紀60年代,爺爺去蘇聯演出,帶回來一臺17寸黑白電視機。打這以后,王碩晚上經常坐在電視機前看戲。看得多了,不僅戲唱得像模像樣,而且戲里的音樂鑼鼓他也能倒背如流。王碩說,這為他以后學習司鼓專業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當時正值“文革”,京劇所演全是樣板戲,王碩愛看愛聽愛學唱,入迷了,守在家里的收音機旁經常聽著聽著就睡著了。上小學時,他也曾穿上家里給制作的行頭,上臺表演一段《杜鵑山》的雷剛。
1978年,“文革”結束后中國戲校、北京戲校重新招生,前來報名的有上千人,最后招收只要40多名。生源一多,錄取的條件就變得苛刻。其中一條,報表演專業的考生不能是近視眼,一下把王碩擋在了門外。做不成演員了,母親就想讓王碩去學拉京胡。王碩的大舅李榮巖是給尚小云先生操琴的,表舅李志良也是京胡行家,其父是余叔巖的琴師李佩卿。王碩從小就和這兩位舅舅學過京胡,他還清楚地記得,剛學京胡那會兒“文革”還沒結束,表舅不敢教他傳統戲,結果就拉了一段《東方紅》。所以,王碩學拉京胡的第一段曲子便是《東方紅》。后來,他又投師母親的同學燕守平,燕老師便教他拉了一大段《智取威虎山》的“朔風吹”。
得益于多位京胡高人的真傳,1979年北京戲校音樂班招生時,王碩考得很順利。他是考京胡進的學校,可一分專業卻被分到了打擊樂組。京胡學得好好的,怎么讓去改學打鼓打鑼了呢?原來錄取學生中女生的比例高,像打擊樂這種“力氣活兒”,只能留給男生來學了。
學了自己不熟悉的打擊樂,王碩起初很不樂意。但慶幸的是王碩趕上了好老師,當時戲校教司鼓的老師都是技藝精湛的老先生,像王碩的蒙師劉耀增先生便是荀慧生先生的鼓師。這位老先生不同常人,不僅鼓藝超群,而且文化修養好,他教課自有一套,叫“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鼓簧戲理,剖析由來,舉一反三。王碩從中受益匪淺,以致后來自己也做了老師,教學生也是這樣的路子。
劉先生教課認真負責。那會兒實行單休制,周一到周六,上午四節專業課雷打不動,下午是文化課和一些公共課,晚自習也經常是排戲時間。劉先生都是盯到晚上排完最后一出戲才回家。那時他已經60多歲,平時擠公共汽車上班,王碩經常看到老師這貼一塊、那貼一塊的橡皮膏,都是擠公共汽車時磕碰的。他對學生是出了名的嚴格,尤其教昆腔戲時要求學生必先會背唱曲牌,個中原因是昆腔的音樂比京劇的更加細膩,而更細膩也意味著更復雜。由于昆腔是曲牌體,不是京劇的板腔體,經常一段就是一個味兒,本來鼓師就是樂隊指揮,要背的戲比誰都多,這回加上昆腔,內容就更多了。老師敦促得緊,背下來之后才教鼓的打法,背不下來要被“發”出教室繼續背。經受了劉先生這樣的千錘百煉,學生們皆被打下了扎實的基礎。王碩感慨地說:“小時候學的東西非常瓷實,這得益于老師的嚴格要求,打的底子好。”
傳道授業,自我提升
王碩當初上學的時候,劉增耀先生就曾指著他的4名學生說:“你們4個人,將來只有王碩能搞教學。”原來劉先生彼時便已經發現王碩學習細心,愛琢磨,學戲能舉一反三。此外,王碩重視文化課,愛讀書看報,18歲時就在《中國戲劇》發表了關于司鼓的理論文章,這使得以寫作見長的校長也很喜歡,所以到畢業的時候,留校從教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王碩留校后,工作之余仍自覺地去繼續深造。他一沒事就去拜望鼓王白登云先生。那時白先生已至耄耋之年,家在城北黃亭子住。王碩從學校騎車過去,要將近兩個小時。通常下午1點鐘頂著太陽出門,騎到白先生家,正好到3點他睡過午覺。 那時白先生家鮮有人登門,一是住得遠,二是他威望極高,年輕一輩都有點發怵。王碩是初生牛犢,為了取到“真經”,就執著前往。有時帶點茶葉孝敬老人,老先生很高興。但過去的老先生們有個特點——藝不輕傳。他和王碩聊天,什么都聊,打鼓的事卻不多說,但聊來聊去終究還得聊到司鼓上。王碩慢慢地套話,說:“爺爺,我那天聽了一段您的錄音,您那會兒是怎么打的?怎么和后來的不一樣?”不經意間,勾起白先生的回憶,便侃侃而談起來。
從不敢多問到有惑就問,王碩虛心好學。白先生看到一個年輕人這么用功,也很感動。日升月往,傳授了王碩許多真知妙諦。王碩每次去拜望,都拿著錄音機,因而保留了白先生的許多珍貴資料。就在前兩年,中國戲校主辦紀念鼓王白登云先生誕辰100周年的活動。副校長說:“中國戲校,73班以前的發請柬,73屆以后的沒見過白先生,不用發了。王碩例外。”
“對打鼓中的問題,一旦經白先生解答,”王碩“啪”地拍下桌子,十分篤定道,“那就像蓋了章一樣,就是取到了‘真經’,你就有自信了,甭管以后再遇到誰,聊一些專業的東西,你就覺得自己是有根的。”
1990年,北京戲校音樂班改革開放后又一次招生。這時王碩二十五六歲,司鼓技藝日漸成熟,遂走上教學崗位,任教同時,還做班主任。北京戲校還專門安排王碩為特聘的閻寶泉老師當助教。閻老師是白登云先生的得意弟子,資深鼓師,從事教學多年,風格與白先生一脈相承。他有一個特點,若是喜歡哪個學生,一定傾囊相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王碩形容閻老師的腦子比電腦都快,不管提什么戲,他馬上就能給你說得詳詳細細。王碩說,像閻老師這樣的腦子,他沒見過第二個。
王碩給閻老師做助教,藝術上、教學上均獲益良多。閻老師教學講究“規格”二字,就是現在人常說的規范。這一點王碩特別認同,他說:“規范是教學的根本,也是藝術的根本,這是老藝術家們都強調的,但規范不意味著保守。像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戲校排的新戲《白蛇傳》,從表演到音樂都是新編的,王瑤卿是總導演,我們閻老師打的鼓。你會發現,雖然音樂是新編的,但閻老師打出的每一個鼓點,都有章可循,那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所以這種創新才是京劇該有的創新,是在規范基礎之上的創新。”
王碩的“三柱理論”
如今,王碩從事教學工作20多年,他有許多心得。他說司鼓是京劇打擊樂的領奏,打擊樂不像管弦樂那樣有旋律,它是打節奏,表現手段主要是力度、速度的變化,所以,特別要注重學生的節奏訓練和節奏感的培養。在王碩眼里,現在學生的學習條件比原來好很多了,但刻苦用功這個概念好像越來越淡化了。
對于老師的個人素質培養,王碩也見解獨到:他對要求戲校的老師既能教又能演不大以為然。他直言不諱道:“作為一名好老師,他當然要重視舞臺實踐,能有豐富的舞臺實踐經驗是很難得的,也一定會在教學中發揮優勢。但這是不可強求的,我們難以要求每一位老師都具備這樣豐富的舞臺經驗和亮相舞臺的實力。教師的工作是教書育人,教學工作自有道行,演好一臺戲并不說明你就能教好一臺戲,教師的本領和成績還是應該體現在學生身上。京劇史上很多的好教師并非名演員,但他們卻培養了無數的演員明星。所以,教師還是應該在教學方法上多下功夫,探索秘籍,要有捏泥人的功夫,要踏踏實實地做幕后英雄、無名英雄。”
談到培養學生,王碩回憶當初白登云先生曾說:“我們一輩子下在鼓上的心思不亞于一個科學家。”他說:培養一名鼓師的難度確實不亞于培養一個主演,因為鼓師的專業素質要求是很高的。鼓師作為京劇樂隊的指揮,他要以領奏的方式來帶動整個樂隊為舞臺伴奏,他需要對樂隊、對演員、對舞臺有全方位的了解。王碩比喻道:“鼓師就像一名交警,他雖然不開車、不走路,但他心里一定得明白道路上的車應該怎么開、路怎么走,這樣他才能盡到指揮之責。” 就鼓師的專業素質培養,王碩自己總結了一個“三柱理論”。他形象地把支鼓的鼓架子的三根支柱各設定了一個內容標志:如第一根代表司鼓的操奏技能,這需要不斷地勤學苦練,以臻嫻熟;第二根代表打擊樂的技能基礎和整個樂隊的伴奏知識,強調學習司鼓的人應該先從“下手活兒”(打鑼、打鐃鈸)學起、干起,“先當兵扛槍”,才能逐步勝任指揮。他說:“像燕守平老師在戲校學習時,是到了最后一年才開始拉京胡,之前都是學、練、實習下手活兒,甚至文武樂都學過、練過。你看我們學校老照片中燕老師當年的照片多是彈月琴而不是拉京胡。所以他能達到六場通透是一點一點積累來的。”
“三柱理論”的第三根則代表著伴奏對象——演員的表演藝術,務求熟識和理解,知己知彼,才能配合默契、伴奏到位。因此,三根支柱缺一不可,合在一起,便可撐起一面鼓來,演繹出精彩的藝術神話。
王碩曾以《伍子胥》一劇的司鼓伴奏為例,談京劇司鼓藝術的實踐方法,題目叫作《鼓師心語》。他想告訴世人,鼓也是會說話的,它能跟著劇中的人物一起喜、怒、哀、樂。
采訪最后,王碩說:“司鼓藝術絕對稱得上是一種文化,之所以不被重視,主要是人們還不太了解它,不了解它的深奧,不了解它的重要。不過我相信:經過我們的努力,司鼓藝術一定會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賞,會作為我們的傳統藝術瑰寶一代代傳承下去。”
(編輯·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