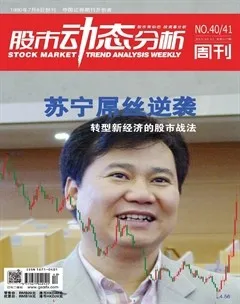轉型之路徑與代價

簡而言之,經濟轉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從支出法GDP 看,轉型在于從投資驅動型經濟模式向投資消費相對均衡發展模式轉變。中國在未來20 年內實現消費驅動型經濟模式存在較大困難,但多方證據顯示,現有投資驅動型模式難以持續,向投資消費均衡結構轉變是必要的。二是從生產法GDP 看,經濟轉型在于從制造業驅動型經濟向制造業和服務業相對均衡發展轉變,主要驅動力可能更依賴于服務業。這兩類轉型能否成功,決定著未來20 年經濟增長情況。今后10 年經濟能否保持7%的增長,未來20 年能否保持6%的增長將取決于這幾年結構調整進程。
第一類轉型是支出法GDP 下的結構轉型。設定不同的轉型情形,觀察相應結果可以對轉型代價有所認識。如果2012-2020 年GDP 名義投資保持10%的增速,結合其他假定,消費占GDP 比例在2020 年將達到56%附近,相較于現在49%的水平,年均增速約為1 個百分點。如果此速度持續至2030 年,消費占GDP比重將達到61%。雖然仍低于發達國家約75%的平均水平,但經濟結構已經達到相對健康狀態。而如果急速轉型,假定2020 年消費在GDP 中比重提高至65%,名義投資則需要下降至7%,放寬假定至2030 年消費在GDP 中比例達到65%,名義投資增速需要下降至9.3%。投資增速過快下降可能對經濟帶來大的沖擊,因為消費一定程度上受投資驅動,投資增速大幅下降會抑制消費。經濟向合理結構轉型應漸進完成。
經濟結構失衡事實上出現于2000年之后。2000-2012 年名義投資年均增速達到18.0%,而名義消費增速只有12.7%,導致了結構失衡。特別是2008 年以來,結構失衡加速。2012 年,消費在GDP 中比重下降至49.2%,投資則提高至48.1%。未來若回到相對均衡狀態,消費需要保持持續高于投資的增速,而這需要政策進行方方面面的調整。
第二類轉型是生產法GDP 下的產業結構轉型。2012 年,中國二產占GDP 比例45.3%,三產占比只有44.6%。服務業在經濟中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與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需要從制造業驅動到制造業與服務業相對均衡發展轉變。其他條件不變,如果未來二產年均增速保持5%,2020 年,二產占GDP 比例將下降至39.0%,三產占比提升至51.0%;如果此速度持續至2030 年,二產占比下降至32.8%,三產將提升至57.7%,基本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如果轉型過于激進,假定2020 年三產占GDP 比例增加至60%,工業增速將下降至1.6%,基本接近零增長;放寬假定至2030 年三產占GDP 比例提升至60%,工業增速將下降至4.6%。經濟產業結構調整是更為痛苦的過程。但根據上半年公布數據,我們欣喜的看到調整過程在加速。今年上半年第二產業增速7.6%,但是第三產業增速達到8.3%。如果未來服務業和制造業增速繼續保持現有態勢,經濟轉型還是有望實現。
經濟轉型有內在的必然性,如果宏觀政策不當,轉型可能會夭折。制造業如不能成功轉型,將在其它更低成本或更高生產率國家的競爭下喪失優勢;而服務業如不能及時發展,經濟增速可能面臨大幅下行風險。無論從體制、企業成長還是過度政府干預等角度看,這種風險均難以忽視。現有貨幣政策仍相對較為寬松,而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擠出企業的融資需求,導致貨幣發行量雖然較大,但企業資金面仍然較緊。如果政府不能對此有所制約,將構成轉型重大障礙。政策應該對經濟內在轉型需求順勢而為,而非選擇過去十年“保八”類似的單一保增長方式。單純的保增長的經濟措施是不具有建設性的,相反,在短期內忍受一定的經濟下滑,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驅動廣義改革紅利,著力增加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應該是未來政策的核心著力點。
經濟轉型伴隨著需求結構變化,必然意味著原有資源配置狀態的改變。在向消費主導、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拉動的增長模式轉型過程中,傳統行業不得不面臨需求相對萎縮、資本較快貶值和資產質量惡化的問題,這是過剩產能與新需求點不匹配所帶來的直接后果,也是經濟轉型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尤其是在經歷了過去幾年刺激政策后,大部分傳統行業增加了很多新產能,產能過剩壓力不斷增加,推動PPI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環比大幅下跌,工業行業持續面臨通縮困境,企業盈利能力不斷下降。制造業盈利能力下降的同時,產成品通縮推高實際利率,投資需求持續受抑制,成為帶動經濟下行的重要因素。
在盈利能力持續下降情況下,企業資本價值和資產質量也出現相應的惡化。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企業部門債務率居高不下,近年來快速攀升,成為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最重要風險因素。據統計,中國非金融企業占GDP 比例從2008年的87.8%提高至2012 年的109.1%,顯著高于美國80.7%的水平,而同期歐盟企業杠桿率略升5.3%,日本甚至下降3.8%。傳統行業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一方面反映出這些行業面臨的困境壓力,另一方面也說明金融系統資源配置機制缺陷和企業市場化退出機制的不暢,大量過剩產能遲遲不能從市場退出,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無形中拉長了經濟下滑周期,也增加了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中國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過程中需要高度重視的另一個問題是勞動力就業轉換和人力資本制約問題。隨著人口結構變化,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在2012年開始出現下滑,未來新興產業的勞動力供給逐漸需要依靠分布在現有產業內的就業人群來滿足,而傳統行業的萎縮也意味著部分行業從業人員面臨再就業問題。目前在就業行業分布中,制造業就業仍占有相當比重,且相當部分集中于中低端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隨著中國在這些行業競爭優勢的逐漸削弱,這些行業的勞動需求可能趨于下降,而服務業就業占比將不斷上升,我們注意到最近幾年服務業對農民工就業的吸納能力也明顯增強,2007-2011年外出農民工數量年均增長3.7%,其中從事批發零售業農民工數量年均增長21.4%,居民服務及其他服務業吸納數量年均增長7.5%。
然而,在傳統行業就業的部分人員包括大部分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相對較低,未來如何提升人力資本以較快實現就業轉換將是中國面臨的重要挑戰。隨著人口逐步老齡化,人力資本投資的總收益和動力將明顯下降,而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轉型又迫切需要勞動力素質的快速提高。長期來看,中國在未來城鎮化進程中不僅將面臨人口紅利消失的壓力,也將承受勞動力素質提升相對緩慢的挑戰。中國需要建立新的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徹底改革戶籍管理制度,統一要素市場,構建全國統一、能夠有效降低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勞動力和其他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機制改革,加大教育體制和科技創新體系改革,逐步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同時政府要加快自身職能轉變,取消對資源配置和市場競爭的干預,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轉向維護市場公平、降低市場不確定性和促進人力資本投資等相關制度建設。這是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邁向全球產業鏈更高端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