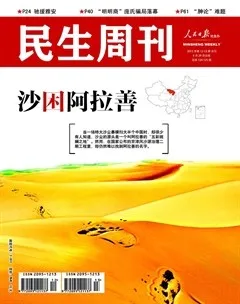康熙獨撰《地震》論文
“朕臨攬六十年,讀書閱事務體驗至理。大凡地震,皆由積氣所致。程子曰:凡地動只是氣動,蓋積土之氣不能純一,秘郁已久,其勢不得不奮。老子所謂地無以寧,恐將發(fā),此地之所以動也。陰迫而動于下,深則震雖微而所及者廣,淺則震雖大而所及者近;廣者千里而遙,近者百十里而止。適當其始發(fā)處,甚至落瓦倒垣,裂地敗宇,而方幅之內,遞以近遠而差。其發(fā)始于一處,旁及四隅,凡在東西南北者,皆知其所自也……”
公元1721年(康熙六十年),當67歲高齡的康熙皇帝在一個靜寂的夜晚意興勃發(fā)地寫下這篇關于地震的論文時,他或許未曾想到,作為天子,自己的生命之火行將熄滅,一年后即撒手人寰。
這篇短短534字的文章,在冷靜的分析與說理背后,跳動著康熙亢奮的情感與曲折的人生經歷。當后人評論康熙皇帝以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豐富的天文地理知識闡述自己的地震理論,開創(chuàng)國君撰寫科技論文的先河時,或許只有康熙本人知道,康熙十八年(1679年)那場京師大地震帶給他的內心震撼。
親歷大地震
1679年注定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年份。大旱至夏, 七月才開始見雨。老百姓還沒來得及在上蒼恩賜的雨露下獲得喘息的機會,一場巨大的災難便突如其來。
這一天是9月2日,北京城剛剛入秋的日子。太皇太后的義女、離開皇宮九年的四格格孔四貞突然回到了紫禁城。久別重逢,康熙顯得非常高興,他攙扶著年邁的太皇太后孝莊來到皇后赫舍里氏的儲秀宮里,暢敘別后之情。
正說話間,宮外隱隱傳來隆隆之聲,隨著太監(jiān)們的驚叫聲,儲秀宮的門窗開始作響, 大殿四角的宮燈左右搖晃,人也站不穩(wěn)了,紫禁城里一片驚叫慌亂之聲。太皇太后連忙喝命眾人保持冷靜,并在嬪妃們的簇擁下跌跌撞撞地來到門外空地上。
大地像醉漢一樣在搖晃,宮殿的梁柱隨之咯咯吱吱地響了起來, 天空中揚起了漫天黃塵。太皇太后合掌閉目, 口中念念有詞, 皇妃們個個驚恐萬分,只有康熙不動聲色, 他仰視著蒼天,進入沉思。
與此同時, 北京城內大街小巷房屋坍塌。宣武、德勝、崇文、廣安等城門倒塌,城墻坍毀,大學士勒德洪被砸壓致傷,內閣學士王敷政被砸死,原任總理河道工部尚書王光裕一家四十三口全部死于地震,其他文物官員及其他死者甚眾……
“天人感應”
讓康熙無法釋懷的是,此次地震還造成紫禁城中養(yǎng)心殿、永壽宮、乾清宮、慈寧宮、武英殿等宮殿遭到不同程度的損毀。
熟讀歷史的康熙知道,紫禁城從永樂皇帝建成開始一直到康熙年間,只經歷過兩次大的地震并遭受破壞,一次發(fā)生在明代萬歷年間,另一次發(fā)生在明代天啟年間。萬歷和天啟都是清人眼中的“亡國之君”,而素來以明主自居、秉承天命的康熙,面對著坍塌損毀的紫禁城,不禁仰天長嘆,內心恐懼:難道這真的是上蒼的懲罰?難道這是對朝廷行政腐敗的警示?難道大清的政權會毀于一旦?
這天下午,康熙冒著余震的危險,在宮中召見了時任左都御史魏象樞,兩人密談了很長的時間,魏象樞一度傷心落淚。但具體的密談內容,康熙沒有公布,直到二十多年后,在相關人員都已不在人世后,康熙帝才向朝廷公布了他們密談的內容,原來,魏象樞在地震后提出“天人感應”說,勸康熙帝調整朝政。魏象樞認為,皇宮發(fā)生地震是由于人事導致,請求康熙帝遵照歷史上的做法,誅殺大臣以彌天災,具體而言,是殺掉當時把持朝政的明珠和索額圖。
地震真的是“天人感應”嗎?明珠與索額圖真的是罪魁禍首嗎?康熙思索良久,終于于地震后的第三天發(fā)布“罪己詔”進行自省:“朕薄德寡識,愆尤實多。遘此地震大變,中夜撫膺自思,如臨冰淵,兢惕悚惶,益加修省……”他一口氣列舉出六種官員害民的行為,強調了整治吏治的嚴厲態(tài)度,同時帶著太子和貴族們離開皇宮,住進帳篷內,處理公務,賑恤災民,并“率諸王、文武官員詣天壇祈禱”,消弭災難。
禍不單行。京師大地震的陰云還未散去,年底又發(fā)生了一件讓康熙帝非常不安的事情,十二月初三日,太和殿焚于大火。康熙在驚恐之余再度將此次火災視為天意,并與人事行政聯(lián)系起來。他在上諭中說:“朕心惶懼,莫究所由。”表示一定要“朝朝夕惕,答上天仁愛之心”。
從懷疑到否定
盡管如此,康熙對魏象樞的“天人感應”說還是持將信將疑的態(tài)度,他沒有像漢武帝那樣遇到災難時殺大臣以謝天,明珠和索額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影響著當時的朝政,后人議論至此,不由感嘆康熙的天縱英明。
真正讓康熙從懷疑走向否定的,是他在位時多次地震的經歷和外國傳教士南懷仁“氣動說”的影響。作為中國歷史上經歷地震次數(shù)最多的帝王,切身的經歷使康熙帝開始從科學的角度對大地震做出解釋。他終于否定了“天人感應”,并堅決反對有人利用“天人感應”的邪說破壞社會穩(wěn)定。他研讀了南懷仁的“氣動說”,最終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地震理論。
在《地震》一文中,康熙闡述了地震成因及震源深度與地震烈度的關系:“深則震雖微而所及者廣,淺則震雖大而所及者近”;并指出地震地區(qū)分布的不平衡:“西北地方,數(shù)十年內,每有震動,而江浙絕無”;同時還對余震有了一定的認識:“既震之后,積氣已發(fā),斷無再大震之理”…… 他在集中梳理、高度總結中國傳統(tǒng)地震學說的基礎上,自覺地將西方傳自希臘的“氣動說”吸納到中國古代的“陰陽說”中,成為我國近代以前最具影響力的會通中西的地震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