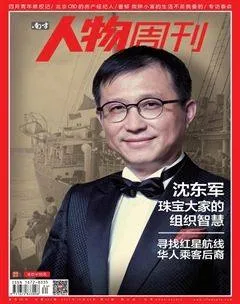“紅色拿破侖”去世

10月4日,武元甲去世,終年102歲。越南官方媒體給予高度評價,給這位越南黨政軍元老冠以一系列偉大的稱號—— “越南民族的優秀兒子”、“胡志明主席的優秀學生”、 “20世紀世界杰出軍事領導人”、“唯一同時打敗過法國殖民主義者和美帝國主義者的天才指揮官”,甚至“紅色拿破侖”等等。
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存在。
《紐約時報》稱,推崇者將武元甲與麥克阿瑟、隆美爾、蒙哥馬利相提并論,但同樣有許多人認為,他的功績印證了“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東方名言。他對己方士兵傷亡的不加顧惜,令世人側目。
沒上過一天軍校的總司令
越南官方媒體稱贊武元甲“文武雙全”。越南通訊傳媒部副部長杜貴尹曾稱贊其“文采在世界名將中罕見”。盡管這有溢美夸大之嫌,但武元甲的確是文人出身的武將。
1911年8月25日,武元甲出生于越南廣平省麗水縣,幼年時曾在私塾學習,后在河內大學歷史系畢業,擁有法學學士的文憑。他不僅寫得一手好文章,且能流利使用越南語、漢語和法語。上世紀20-30年代,武元甲曾是報刊上非常活躍的撰稿人。他還和同伴合伙辦過刊物。在當時的越南,武元甲算得上鳳毛麟角的“大知識分子”。
在上世紀初的東亞,學生往往成為新潮政治思想的信徒,武元甲也不例外。他很早就和好友長征一起結識了胡志明,并在1938年加入胡志明創立的印度支那共產黨。
1939年,法屬印度支那殖民當局取締印支共,迫使胡志明、武元甲等人逃入中國境內。1941年,胡志明成立越南獨立同盟(即越南民主共和國前身)。同盟會下設軍事委員會負責武裝斗爭,該委員會負責人就是武元甲。
當時,越盟中并不乏具有正規軍事教育背景的干部,其來源包括黃埔軍校、云南陸軍講武堂的越南籍學生,和被越共送到蘇聯學習軍事歸國的干部。但這些人或很快犧牲,或水土不服。在胡志明看來,遠不如武元甲可靠。武元甲本人接受外媒采訪時也坦承“從未接受任何正規軍事教育”。
1944年12月22日,越共第一支武裝——越南解放軍宣傳隊在越南靖西成立,武元甲任總指揮。3天后,他率部越境進入高平省,先后在費克、那銀襲擾維希法軍成功。這被認為是越南人民軍(當時稱越南解放軍)的誕生標志。由于這段經歷,在越南人民軍中,武元甲被尊稱為“大哥”。這也一度是其領導游擊戰時的化名。
抗戰期間,越共武裝曾得到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但戰后這種支持轉變成打壓,不過此時越共已羽翼豐滿。1945年8月,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武元甲被任命為國防部長、武裝力量和民兵自衛隊總指揮。
在河內期間,武元甲常常和法國人打交道,并得到一個“越南托洛茨基”的綽號。當時的法國報刊稱,武元甲“額頭光滑,身材矮小,脾氣火爆而好戰,不耐煩多聽多說”。他的法語一開始總是很溫和,然而一旦被激怒,就會變得粗暴尖刻,常常喜歡展示“戰斗到死”和“不怕犧牲消耗”的決心。然而,由于法軍后來攻占河內,武元甲一度被譏諷為“紙上談兵的小個子”。
“犧牲千萬人,也在所不惜”
1946年12月9日,法越戰爭爆發。武元甲指揮的越軍節節敗退,只能在中法邊境活動。1949年,得到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越軍重振旗鼓,先后編成4個師,總兵力達一萬人以上。1948年,武元甲獲得大將軍銜,他也是越軍第一位大將。
1954年3-5月,在奠邊府之戰中,法軍戰死、被俘1.6萬余人。此役迫使法國承認戰敗,并最終退出整個印度支那。奠邊府戰役令越南人民軍士氣大漲,奠定了此后長期抗美的基礎,也令法國的全球殖民體系開始崩潰。此役的名義總指揮是武元甲,他因此成為舉世聞名的人物。“奠邊府之虎”的稱號,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此。
但許多資料顯示,在整個抗法戰役期間,“大哥”的戰略思想常常“慢半拍”:滿足于打通中越交通線,站穩腳跟,依托中國援助和法軍對耗,不敢集中兵力和法軍決戰的。胡志明的推動和中國軍事顧問的全方位參與,給了這位“世界名將”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機會。
1951年的越共二大排定了早期越南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座次,依次為胡志明(主席)、長征(越共總書記)、黎筍(綽號“三哥”,越共副總書記兼南方局書記)、范文同(總理)。武元甲僅次于上述4人之后,以人民軍總司令、軍委書記、國防部長的頭銜,列第五位。
上世紀60年代前期,武元甲兩次訪蘇,對蘇聯的“大縱深”、“大兵團”機械化正規戰印象深刻。他極力主張采用蘇聯軍事模式,并用蘇聯體系改組軍隊。這遭到軍委第一副書記、越軍總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大將的抵制。胡志明雖仍信任武元甲,但也不認同其軍事觀點,令其“養病”兩年。越南南方的軍事行動,轉由阮志清大將負責。1967年,阮志清大將去世,在胡志明支持下,武元甲重掌軍權。
1972年春節,武元甲不顧中國顧問的勸阻,集中越南幾乎全部軍隊和現代化裝備,發動了抗美戰爭中越方最大的攻勢戰役——廣治戰役。他試圖畢其功于一役,一舉吃掉南越。結果,在這場“乞丐和龍王比寶”的大會戰中,越軍精銳損失殆盡,傷亡逾10萬。

1975年4月30日,越南統一,身為總司令的武元甲卻并未獲得“解放第一功臣”的稱號。此后,他逐漸淡出越南政治核心:1979年,他的國防部長位子被文進勇大將取代。1980年,任職30年的軍委書記被撤銷。1982年,他被排擠出中央政治局。1986年,帶著副總理、大將虛銜的“大哥”被宣布退休。
2011年出版的《武元甲人生》,形容其作戰“總是最大限度地避免犧牲,并選擇傷亡最小的作戰方案”。然而,這并不符合事實,甚至他本人的敘述。1969年,在接受意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采訪時,武元甲聲稱:“全世界每分鐘都有成百上千、成千上萬人死亡,為了革命和國家統一,即便這些犧牲者是我的同胞,我也在所不惜。”
恢復中越關系的關鍵人物
1986年,“三哥”黎筍去世,和武元甲關系親密的長征任總書記。此時的越南,已被柬埔寨戰爭和中越邊境對抗拖到筋疲力盡。恢復中越關系、將戰略重心轉移到經濟上,成為越共黨內的共識。受長征、阮文靈之托,武元甲秘密奔走于中越之間,努力恢復兩國、兩黨關系。1990年北京亞運開幕式,一身戎裝的武元甲大將出現在主席臺上,引起全球媒體矚目。這被外界普遍認為是中越關系全面正常化的標志性事件。恢復中越關系的“戰役”,由“紅色拿破侖”圓滿完成。

1991年,年逾八旬的武元甲大將辭去最后一個公職——副總理。此后,他仍然發揮“余熱”:支持越共的“革新開放”,反對在經濟建設中忽視資源保護,反對倒向任何一個國家,主張改善越美關系等等。
早在戰爭時期,武元甲就是西方媒體關注的焦點。1966年1月、1968年2月和1972年5月,他曾3次登上《時代》雜志封面。他和法拉奇之間的對話更傳誦至今。直到2004年,他還接受法國《人道報》采訪,就“主權與人權”、霸權主義和世界和平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許多人都稱武元甲是“親華人物”,并羅列了許多理由。
在軍事生涯早期,他曾和國民政府合作;建軍初期,他和陳賡、韋國清等中國軍事顧問進行密切合作;越戰后期,他對黎筍“一邊倒”的親蘇路線不滿,提出“和大哥、二哥都要搞好關系”;中越戰爭前夕,他公開強調“要和中國同志緩和”,結果丟了國防部長的職務;中越戰爭爆發后,已經“半退”的他也仍不時提出批評,最終導致“全退”。亞運會前后,他為中越關系正常化的奔走,更是家喻戶曉。
但相反的理由也不在少數。
早在越南統一前夕,他就為越軍刊物題詞“全力以赴保衛越南島嶼主權”。這被認為是含蓄表明了其在島嶼主權問題上的“越南正統立場”;賦閑、復出和再度引退期間,他固然積極主張改善中越關系,并為之努力奔走,但同樣主張對外關系多元化和改善越美關系。他極力反對的西原鋁礦開發項目,原本與越南國有資本合作的外企,據稱就來自中國。
正如《人道報》所言,武元甲是一個比較純粹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凡是他認為對越南有利的方針、政策,他就會遵循,反之則會反對。在代表作《人民戰爭和人民軍隊》、《論游擊戰爭》中,武元甲雖然大談“中國革命的經驗”,卻是以引述胡志明論述的形式進行。不難看出,除了民族立場外,出于對胡志明的尊崇,他在許多軍事政治問題上,都刻意靠攏胡志明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