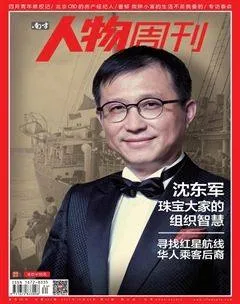學界神仙伴侶
大學時代我讀過靳凡的小說《公開的情書》。小說由43封書信組成,抒寫了當時一代青年對理想、愛情、事業和祖國命運的勇敢探索。我被小說中的主人公真真和老久深深吸引。1980年念大二時,又讀到了金觀濤和劉青峰的長篇論文《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一個超穩定系統》。那時候,我整天鉆在故紙堆里,讀完這篇論文就像呼吸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氣。
后來聽朋友說,《公開的情書》的作者靳凡、女主人公就是劉青峰,男主人公就是金觀濤。他們都是北大畢業生,觀濤在化學系,青峰在中文系,原先互不認識。1970年,觀濤分到杭州當工人,青峰分到貴州的一個縣城中學做老師。金觀濤關于黑格爾哲學批判的筆記在朋友之間流傳,傳到青峰手上,他們便開始通信。一天一封厚厚的信,后來就成為《公開的情書》的素材。兩人于1971年底結婚,1973年青峰調到鄭州大學,次年觀濤也調到那里,他們一起運用系統論研究歷史。1978年夫妻雙雙調到中國科學院,在《自然辯證法通訊》當編輯,并和包遵信聯手主編《走向未來》叢書,推動80年代中國的思想解放浪潮。可以說,他們夫婦是我們這一代大學生崇拜的思想偶像。
初識這對神仙伴侶是1985年夏,那次是為制定上海文化發展戰略進京走訪學者。在一間狹窄擁擠的辦公室里,見到了觀濤和青峰。時隔多年已經記不得談話內容了,但他倆的個性卻使我印象深刻。青峰熱情開朗,十分健談,有北方女子的豪爽。觀濤則沉默寡言,看上去有點靦腆冷漠,或者說自負。后來數十年的交往中,這種印象幾乎沒有改變。不過,在和觀濤熟識后才發現,他有時也很激情,尤其是談起他有興趣的學術話題時。在國內時,斷斷續續有些交往,但并不密切。印象最深的只是1988年,觀濤來上海出差,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和副部長劉吉知道后,要我請他見個面。在越劇團的飯館里,我們四人共進午餐。部長們表達了欽佩之意,不善言談的觀濤只是敷衍而已。唯一實質性的話題是觀濤為上海社科院哲學所的紀樹立說項。老紀在自然辯證法研究領域頗有盛名,但因“文革”中參加過“四人幫”的寫作班子,此時仍打在冷宮。
1994年夏,我到香港工作,觀濤夫婦也留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我們的交往就開始逐漸密切起來。當時我在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每星期要從港島坐火車趕到沙田上課一次。課前課后就常常去他們的辦公室聊天。青峰往往會放下手上的工作,和我天南地北地聊起來。我在傳媒界工作,算是消息靈通人士,她喜歡向我打聽各種小道消息,或者一起議論天下大事。觀濤則在一邊靜靜地旁聽,偶爾插幾句話,或是打個招呼,繼續埋頭做自己的事。此時,他正轉向思想史的研究,2000年完成《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接著轉入用數據庫進行觀念史探索,2010年出版了《觀念史研究》。后來還主持10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編纂。
那些年,我每逢周末都會去中環麥當勞道南懷瑾的寓所,觀濤夫婦也是那里的座上賓。大家圍著懷師七嘴八舌地閑聊。觀濤也很少說話,唱主角的永遠是青峰。有時候,觀濤在飯桌上也會和懷師討論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的話題。懷師總是夸他聰明過人。到了2002年,懷師移居上海,麥當勞道的圓桌也曲終人散了。我也早已結束了在中文大學的博士課程,和觀濤夫婦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
直到2008年,聽說觀濤和青峰都準備退休。當時青峰主編的雜志已成華人社會的學術重鎮。我很想接替青峰的工作,于是就和他們相約在中文大學見面。說明來意后,觀濤和青峰都勸我打消這個念頭,說是當編輯收入低,還必須天天來校坐班,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不值得把時間消耗在編雜志上面。收入低倒無所謂,當時我在經濟上已經脫貧,不靠這份收入,但一聽說要坐班,頓時就打了退堂鼓。此時他們夫婦已做好了退休的準備,在沙田買了一間工業大廈做工作室。我應邀跟隨他們參觀了那間堆滿圖書資料、但整理得井井有條的工作室,不勝羨慕,這大半應該是青峰的功勞。那次見面,觀濤說起他和我倆共同的好友嚴博非一起在浙江古鎮南潯創辦了一所“歸來書院”,邀請我在秋天江南菊黃蟹肥的時候,去那里作客。
8、9月間,觀濤夫婦、沈志華夫婦和我們夫婦一起從上海驅車去歸來書院。推開大門,踏著長滿青苔的曲徑,走過綠蔭環繞的觀妙亭,迎面而來一座浙派百年老樓。我們3對夫婦在那里剝蟹飲酒,徹夜長談。這是認識觀濤近三十年來,他談興最濃的一次,但話題還是離不開他最有興趣的哲學。直到月西斜,人已醉,大家才各自散去。后來觀濤夫婦去臺灣政治大學執教了,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