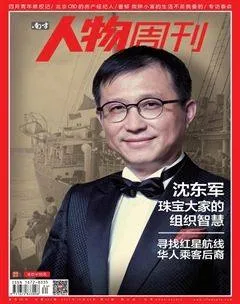一場推遲10年的荷爾蒙釋放

文馨和石可是校友,兩人在1994和1995年分別入讀北大英語系和光華管理學院。十幾年后文馨從華爾街歸來轉身為戲劇制作人,石可則在英國拿到戲劇博士學位,回國當了大學教師。文馨將石可介紹給她的搭檔張子一,后者由此讀到石可寫于2003年的劇本《新青猿》,她認為這是個好故事。一番合計后3人決定將此劇搬上舞臺。
2013年9月18日,《新青猿》媒體場在北京蓬蒿劇場開演。演員們在兩個月排練后面對第一批觀眾尚有些緊張。兩個故事看似互為夢境:游俠率一眾村民上山找盜賊尋回被搶走的兩頭豬,村民半途散去,游俠討賊失利;另一條故事線穿插其間,徐霞客與好友和尚欲赴雞足山未果,和尚客死他鄉。石可否認兩個故事間的關聯:“我有這樣暗示,但我不點明解釋這是不是互相做夢的狀態。”
此時距離劇本創作已過去整10年。《新青猿》原是一部案頭劇(主要為了放在案頭閱讀,而非在舞臺上演出的腳本文本創作),其時石可剛剛完成北大的電影研究碩士學業。宣傳頁寫道:法制文學和老軍醫的戲劇風格,內容奇異,保管讓小伙伴兒們各種深深地驚呆。前一句為1978年生人的石可所加,意在提醒中國文化界所謂雅俗文化的分野往往是無稽之談,“幽默感是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很缺失的一種能量。”他說。
實際上這兩個時代色彩分明的詞匯如今讀來已有些過時。兩個半小時的演出里科諢粗口不斷,一些時下熱點如“趙紅霞”、“夢鴿”也出現在臺詞中。或許因為觀眾多為媒體從業者,臺下對此類笑點反應冷淡。“觀眾是最奇怪的一種動物,”第二天的總結會上石可說,他設定的笑點“一個都沒笑”。
“這說明你不可以僅僅按照自己的想法預判人家,而是要把來支持你的人當活人,和他在現場心氣相通。”石可說。他要求演員們放松心態,呈現“自然本真的身體和意識狀態”。
時隔10年排演此劇,石可未對劇本做出較大改動,除了二度創作必須進行的刪減之外,調整的只有細枝末節。“這個社會也許有些表象變了,但實質沒變。”石可解釋,宣傳中突出《新青猿》寫于10年前,“純粹是為了說明它比《武林外傳》來得早。”兩者均以古裝角色現代談吐為特色,這種做法在50年代前就流傳甚廣。而另一方面,石可也并不希望他的作品只是嬉笑。
“說句實話,中國觀眾被慣了太久,需要自己動腦子投入能量的戲看得太少了。這是反抗宣教戲劇的時候矯枉過正留下的后遺癥。很多戲劇觀眾不適應需要自己去探尋的戲。”《新青猿》遵循古典美學原則,試圖再造一個世界,這小世界戲中有政治,有宗教,有文化沖突,有人生成長。石可稱觀眾“ 能拿到20%就可以據此建立起自己的理解了”。
劇本沒大改,但石可認為中國的戲劇環境變好了很多。10年間,小劇場戲劇在國內已漸成規模。“就像最開始大家覺得只有民族美聲那才叫唱歌,后來臺灣流行音樂進來了,讓人看到不同的可能性。戲劇在這20年間經歷了同樣的過程,觀眾的欣賞水平也在提高。”記者提到這意味著觀眾會更加挑剔,石可擺出了一種防衛姿態:“這當然是好事。不過作者對觀眾負責的惟一方式就是不媚眾,也就是說觀眾挑不挑剔完全不應該進入創作者的的考慮范圍。”
《新青猿》故事主干來自葉芝短篇小說,而“施恩者與受恩者關系”的母題也曾是是黑澤明《七武士》的核心內容。石可為《新青猿》列出了18本參考書目,所涉內容從佛學史到養豬技術不一而足,這顯然又是和本劇氣質一致的玩笑。“這是個非常主流的商業戲劇,有故事有人物有情節,”石可說,本劇是對文化自我的一種探尋。“中國的各種文化都被‘土洋’二元對立了,我們每個人的文化自我都是個大黑洞。這劇就是講的這個問題。”他表示自己沒有答案,只是提出了問題。
石可曾在二十多歲時經歷過一段抑郁和狂躁狀態,“有很大的烏云壓在頭上”。他反復追問一個問題:在一個人最應該幸福的時候,我為什么不幸福?“后來開始讀博,我做了好幾個行為藝術來試圖探尋這個問題,而不是試圖解答。《新青猿》也有這方面的內容:怎樣才算是解脫了?人的精神狀態,互相之間可不可以比較?還有在中國社會,為什么人和人之間這么殘忍,這么兇惡?為什么小時候,只要出現問題我就想暴力解決?”石可是青海人,他說在家鄉,暴力幾乎是很多年輕人解決問題的首選,后來他發現這是全國的普遍現象。關于“新青猿”這個名字,石可希望能和觀眾分享對于進步的看法,在知識界這是個老題目。“怎樣才算進步,為什么要進步?進步要付出什么代價?西方種族主義者罵人會說:你是猴子。意思是還沒進化過來呢。新青猿的意思就是我寧可呆在這,我不進化了,如果進化的邏輯有問題的話。我要站住看看自己過往的路。別像砍了頭的雞一樣蒙頭往前沖,盲目而愚蠢。” 在石可看來,他的任務是找到集體潛意識中被埋藏的部分,“那就是互相之間的仇恨和殘忍記憶,因為太殘忍,所以我們只有埋住才能過下去。”
首演后觀眾褒貶不一。有人表示“每一個設計甚至每一句臺詞都有出處,這戲有根,真難得”。亦有觀眾認為劇本太貪心,“除了臺詞華麗其余很潦草。”
另一位制作人文馨介紹,《新青猿》演員12人,加上其他人員整個團隊人數達到二十多。受限于小劇場座位數(蓬蒿劇場是北京最小的小劇場,座位僅120左右)和相對較低的票價,此劇排演的成本很高。“文本上也需要冒險,好多東西你細琢磨,會發現是對現實很大的諷刺。這東西可深可淺,既點透了你又得沒事兒。”
12位演員中不少是通過網絡招募來的,背景多元:有人是保險公估師,有人畫油畫,有人是業余拳擊手,還有籃球運動員。飾演公雞崽兒的孔恐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曾主演話劇《李小紅》,能看出經驗讓他比其他人在舞臺上更為自如。“為這個沒少跟導演打架,”孔恐說,從石可這里學到很多,“他帶來一些新東西,比如身體帶動情緒的練習,以前沒接觸過。他強調我們做一個動作,或者說一句話,啟動的時候那一剎那的動機。把這個動機放大成一個行為,而不是隨意去做動作。”不過,在談及某個具體情節中人物動機時,孔恐坦承“沒和導演把這場戲主旨聊得特別透徹”,“現在這樣是最好的,”他說,“導演給我的解釋比較含糊,他特別怕聊特別透——本來是個很寬泛的出口,一下變窄了。我們意思到就行了。”
做戲劇工作坊是石可的特長,但諸多線頭如何歸攏卻是個大問題。謝幕時,石可將贊美毫不吝嗇地送給副導演孫小杭。他稱自己提供了蛋糕,“上面最精美的幾朵奶油花是孫小杭雕刻的。”
制作人張子一也表示,兩位導演風格互補。“孫小杭很擅長細摳整個戲,然后提煉出戲劇沖突來。”
孫小杭比石可小兩歲,曾以作品《文明城市》獲首屆老舍戲劇青年文學獎。現在他的主業是電影編劇。除擔任副導演外,他還是劇中人物二十三的扮演者。孫小杭曾建議刪減一些角色,“石可的野心在那兒,他認為少掉一個就會怎么樣(有損失),”孫小杭說他很能理解這種“帶著青年荷爾蒙的、噴出來的”想法,“有些意識形態的東西可能我永遠不會做了。但年輕些的人想做,你又希望它能長出來開出花,我愿意在技術上給你提供幫助。因為文化的活性不是一個人能做出來的。”
展覽
《荒木經惟:感傷之旅/墮樂園 1971-2012》攝影作品展
時間:9月24日 至11月6日
地點: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
展覽作品始于荒木經惟“私寫真”創作的最早期作品《感傷之旅》,并以最新作品《墮樂園》結尾。通過對荒木與愛妻陽子最真實、最私密的生活記錄,觀眾將真切領略他的內心世界,體味他所說的“所謂攝影,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