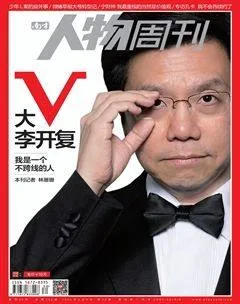全民編劇
老狼有首歌這樣唱:“一切都像是電影,比電影還要精彩。”這恰可以說明我們對過去半個月里幾件大事的觀感。無論微博、論壇還是現實中,針對這些事的評論里,聽到最多的就是“簡直像電影(電視劇)一樣”。
某件大事的男女主角和幾個配角,面對公眾講述了他們的人生沉浮以及情愛糾葛和家庭矛盾引發的悲劇,加上圍觀群眾的補充、議論,一部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個人生活史、家庭生活史躍然眼前。他們強烈的個性和表達能力,使得當事人的性格呈現得非常鮮明,對話精當而意在言外,讓許多編劇都自愧不如,“像美劇”、“《社交網絡》里的對白都被比下去了”之類的感嘆不絕于耳。尤其是他們的情愛悲劇,讓圍觀群眾唏噓感嘆,女人們慨嘆女性命運的跌宕,心理學家探討家庭成員和諧相處之道,總之,每個人都各取所需。
事情為什么會變成這樣?政治事件為什么會解釋為愛情和家庭悲劇?顯然,重點不在于發生了什么,而在于如何講述,以及人們會不會接受這種講述。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現實非常殘忍,簡直無法直視,但當事人又必須完成講述,于是索性創造一個故事,用猩猩和斑馬的故事來覆蓋現實。對于已經創建了“講故事”這種文化手段的人類來說,比“不是真相”更難以忍受的,是“不夠故事”。如果想讓一件事被人接受,一定得“夠故事”,最好的辦法,莫過于仿效影視規律,組織一個“像電影(電視劇)”的故事。
也有人不滿足于按照影視的方式進行最終呈現,一開始就根據影視的方式來設計自己的行為。楊麗娟被娛記圍追堵截時,惱怒地掛著臉說:“信不信我打你。”這并非西北礦區女孩的天然表達,這是她鐘愛的香港影視中的表達。浙江有個自制八十多件工具入室行竊的小偷,被警察抓住后,面對鏡頭,這樣回答提問:“人生就像一場戲,有人扮演警察,也總要有人扮小偷。”這也不是小偷的表達,而是明星處心積慮設計的金句。
丹佛影院槍擊案中,詹姆斯·霍姆斯闖進正在放映《蝙蝠俠前傳3:黑暗騎士崛起》的電影院向觀眾掃射,讓“許多人以為槍聲是電影的一部分”,他的家里則布置得像個高智商犯罪者的彈藥庫,引起媒體的極大興趣;謀殺中國留學生林俊的加拿大殺人狂,老早就開設博客,甚至在視頻網站上傳宣傳片,殺人現場經過精心布置,掛著《卡薩布蘭卡》的海報,還給殺人視頻配上懷舊勁歌。這不是罪犯的表達,而是電影人的表達。
這是一個全民編劇、全民電影人的時代,只不過人們是從電影中取材,來設計自己的言行。與此同時,人們也愿意按照影像的規律去理解他人的所作所為,“像電影”減輕了理解的難度。所以,一方面有著名編劇認為,編劇行業門檻太低,導致“全民編劇”,是行業災難。另一方面,電視劇《愛情公寓》卻在二季開拍之前,舉辦“全民來編劇”活動,邀請觀眾參與劇情設計。
法國哲學家埃德加·莫蘭在他的《時代精神》里對此有過論述,他認為,大眾文化對人們的行為和心理狀態產生了影響,也正是這種影響,才把人們變成了現代人。
文化貌似無力,卻通過改變人們的想象力,實現了對現實的改變。那些明朝的事,那些紅顏悲歌,都是被想象力、被敘述的藝術改裝過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