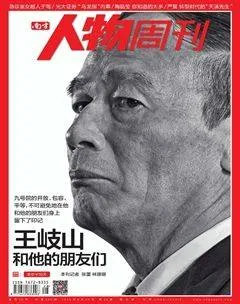嚴復 轉型時代的“天演先生”

著述滿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試其長
現在已經很難考證清楚,嚴復究竟是何時開始吸食鴉片的。世人也許很難想象,這位翻譯大師以典雅的文辭翻譯《天演論》,勉勵國人自新自強的同時,自己卻仍躺在煙榻上吸食鴉片。事實上他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在“過癮”之后身心舒緩的狀態下完成的。
不過,據族侄嚴家理回憶,嚴復吸食鴉片有一點異于常人,“他老人家……吸完鴉片后,從不久臥煙榻,無論讀書寫字,總要坐得端端正正。在逝世前一段時間,精神稍好,總是要坐起來,在床上橫放一張矮幾,扶案看書做事。”當時嚴家理不滿10歲,許多年后他仍記得,嚴復在煙榻之上還教他讀了一段《滕王閣序》。
很有可能,嚴復是在北洋水師學堂任職時開始吸食鴉片的。據說,上司李鴻章也知道這事,并說,“如此人才,吃煙豈不可惜!以后當仰體吾意,想出法子革去。”嚴復對此很感念,鴉片還是照吸。這是他一生中很不得志的階段。用他的話說,“北洋當差,味同嚼蠟”,上司并不重用他,水師學堂還有嚴重的南北派系之爭。
事實上嚴復的官場經歷兩個字就可以概括:不遇。
1854年1月8日,嚴復出生在福建侯官(今屬福州),原名宗光,字又陵。身為名醫的父親在他13歲時受病人感染去世,家道從此中落。他不得不放棄科舉,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沈葆楨主持的馬尾船政學堂。學堂分前、后兩堂,前學堂是有法語課的制造學堂;他讀的是有英語課的后學堂駕駛學堂,學制5年,畢業之后在軍艦實習。
1877-1879年,作為中國海軍第一批留學生,嚴宗光在英國留學兩年。歸來之后,將名由宗光改為復,將字由又陵改為幾道,以示一段新人生的開始。對他有知遇之恩的沈葆楨恰好在這一年去世。嚴復先回馬尾船政學堂任教,次年李鴻章籌辦北洋水師學堂,將他調去天津,擔任洋文正教習。
嚴復的教學似乎并不成功。后來當過清政府駐美公使的梁誠曾是北洋水師學堂學生,據他回憶,“我們的總教習,那位在英國受教育的,像其他的中國教習一樣不知如何施教”,“他照書本一字字往下念。”
長子嚴璩在他為父親撰寫的年譜中說,當時官場的習慣是到了道臺一級才能擔任水師學堂這類機構的長官,嚴復官階不夠。其實,水師學堂的組織和教學方式,都是他一個人設計的。1891年他升為道員,再過兩年,終于當上“總辦”(校長)。難以升遷跟不是從“科舉正途”出身有關,至少嚴復是這么看的。1885-1893年,他接連參加4次鄉試,均告無功而返。他想過投奔張之洞,后來因為公開批評張的“中體西用”說,這條路也斷了。
看上去最有希望的是1898年,嚴復得到急于改弦更張的光緒皇帝的召見。這次會面絲毫也沒有改變他的命運,事隔一周,光緒就因戊戌變法被慈禧幽禁。對于這場變法,嚴復多少有一點置身事外。他覺得康、梁太急進,恐難以成事,所以一直專注于翻譯《原富》,但后來還是因為被懷疑為“黨人”而受到排擠。
清政府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后,嚴復當過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憲政編查館、清理財政處的咨議官。1910年,清政府頒授優異留學生進士、舉人出身,入選23人中,名列榜首的是詹天佑,56歲的嚴復次之,得了一個不倫不類的“文科進士”。聞訊之后,除具帖向考核官致謝外,他只是讓夫人“分告各熟友”。
這種遠離政治核心的際遇在民國也未改變。同為翻譯大家的林紓曾為嚴復嘆惋:“君著述滿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試其長,此至可哀也。”
凡可以愈愚者,不問中西新舊
甲午一戰,對嚴復刺激至巨。中日兩國同一時期辦海軍。1870年代他在揚武號軍艦實習,曾經游歷日本各口岸,到岸時日本萬人圍觀。二十年后,一勝一敗,北洋水師竟全軍覆沒。殉國的鄧世昌、林永升、劉步蟾等人,都是馬尾船政學堂駕駛班第一期的同學,而他本人又是北洋水師學堂總辦。精英盡毀,如何不痛?
1894年初,戰爭陰霾漸濃時,嚴復已覺“一時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一年之后,戰爭尚未結束,他在天津《直報》上接連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四文呼喊改革。
嚴復引介了達爾文的生物學,稱《物類宗衍》(《物種起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爭自存》《遺宜種》兩篇。“所謂爭自存者,謂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而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焉。”能自存、遺種的,一定是適應天時地利及一切事勢的物種。這個法則既適用于動植物,人類亦然。
在他看來,中國幾十年里禍患頻仍,抗拒潮流,持貶斥洋務、驅逐西人之論者,可謂“自滅同種”。“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于通達時務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為此。”原因只能是出自私心,而結果可能是國家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嚴復列舉了兩種可能會提出解決方案的人。
一種人挽起袖子說,“為什么不讓我治理?要是讓我治理,馬上就可以實現富強,而且民風淳厚。中國之所以不振,不是法不好,而是執行不力。祖宗定好的制度都在,更有力地執行就行了。”嚴復批評說,天下大勢像高處的水流往低處,已經浩浩蕩蕩成為江河,這樣的辦法等于是要攔住江河,使其回到山上去。
另一種人說,制度就像祭祀用的草狗,只能用一段時間。天下大勢已日趨混同,我們想富強,西方富強的制度在那兒,跟著實行就是了。建立民主,開設議院,創辦公司,普選,全民練兵,收十分之二的稅充實財政。嚴復批評說,中國就像一個病夫,這是讓病夫每天跑馬拉松,只不過是讓他死得更快罷了。
好制度就像草木,需要有合適的環境。海關總署、船政、招商局、制造局、海軍、海軍衙門、礦務、學堂、鐵道、紡織、電報、出使,中國向西方學的都是“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強之機”,不料“遷地弗良,若亡若存,輒有淮橘為枳之嘆”。原因在于中國的民智、民力、民德跟不上。時人只知損彼利己,“不知彼此之兩無所損而共利焉,然后為大利也”,“而富強之政,亦無以行于其中。強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廢。”

嚴復相信,“社會之變相無窮,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質。”他把國家的富強和民眾的自治聯系起來,并認為國家要富強,不外乎實行利民之政,利民之政的基礎是民眾能自利,能自利的基礎是能自由;而能自由的基礎是能自治。
他常提到自由這詞,甚至說過“自由為體,民主為用”這類話,但有件事頗堪玩味。穆勒原著名為《論自由》,他先是直譯,而后改為《群己權界論》。在《法意》按語中他說,“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圖強,……為自存之至計。”
歸根到底,中國的大患是愚、貧、弱,而以愚最為嚴重。正因為愚,國民才日益陷于貧弱而不自知,所以最重要的是開民智。“凡可以愈愚者,……惟求之能得”,不問中西新舊。“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貧弱,雖出于父祖之親,君師之嚴,猶將棄之,……有一道于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療貧起弱焉,雖出于夷狄禽獸,猶將師之,……”嚴復師的道正是“夷狄”的西學。
他絕非“全盤西化論”者,中國傳統始終在他心里徘徊。后來他在《與〈外交報〉主人書》中說,“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所以必須“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后得之,其為事之難如此”。

1905年春,嚴復與孫中山曾在倫敦會面,據聞兩人有以下對話。嚴復說,“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之于乙,泯于丙者,將發之于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大不以為然:“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不知當日嚴復是如何答復的。假如從他文章中找,應該是:“制無美惡,期于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
“天演先生”的“第一急務”
1899年,嚴復致信張元濟(將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后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認為“譯書為當今第一急務”,“復自客秋以來,仰觀天時,俯察人事,但覺一無可為。然終謂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與夫后生英俊洞識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則炎黃種類未必遂至淪胥;即不幸暫被羈縻,亦將有復蘇之一日也。所以屏棄萬緣,惟以譯書自課。……以饗一世人。”
嚴復相當自信,“且彼中盡有數部要書,非仆為之,可決三十年中無人為此者;縱令勉強而為,亦未必能得其精義也。”事實上在此之前,他翻譯《天演論》已獲得超乎想象的成功,后來甚至有了“天演先生”的名號。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天演論》出版之后,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魯迅當時在江南水師學堂,“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甘冒長輩訓斥,“一有閑空,就照例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還在英國時嚴復就知道達爾文主義,當時他似乎已經獲得了一種革命性的認識,即在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富強之道。此后他一直對這類著作保持敏感。他譯《天演論》是在1896年,只比原著晚了兩三年。盡管自序中說“夏日如年,聊為迻譯”,實則他關切的無疑是“自強保種之事”。
赫胥黎原著名為《進化論與倫理學》,1893年初版,次年增補,全書6個部分,嚴復只譯了第一、第二部分,并將書名定為《天演論》,等于原名的一半。他說自己“取便發揮,實非正法”,“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難怪魯迅說他“做”過《天演論》。)此外他還加了許多按語,提出自己的見解。正如美國學者史華茲所說,按語與原文同樣重要。
赫胥黎原書宗旨是:自然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以致優勝劣敗、弱肉強食;而人類社會的倫理與自然法則、生命過程不同。人類社會的進展,意味著對宇宙過程的抑制。人類因為有天良,善于感受同情,足可以超越競爭。所以進化論并不適用于人類社會。
嚴復卻在按語中說,赫胥黎犯了倒果為因的錯。事實上人跟禽獸最初沒有分別,個人組成社會是為了安全利益,而不是因為有天良、懂同情。進化過程把能夠、善于組織社會的群體挑選出來,懂同情的群體,更有機會組織好社會,得以留存(不懂得同情的人類群體,在進化過程中被淘汰了)。適者生存的法則同樣適用于人類的種族和社會之間。
嚴復念念不忘的命題是“自強保種”。他翻譯《天演論》,用意只在激勵國人自立自強,爭為天擇的“適者”。“必其一群之人,……人人皆求所以強而不自甘于弱”,而后中國才有機會成為“強族大國”,種族和國家都得以保存。多半是因為這種意識,原文不具有的“國族競爭”的意義,《天演論》中卻呼之欲出。
《天演論》在當時造成怎樣的影響?
胡適是這么說的,“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累次戰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民報》則說,“自嚴氏之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于人心,中國民氣為之一變。”不但為救亡圖存凝聚了共識,而且還以基于科學的名義,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宇宙觀。

當時許多人以《天演論》中語為自己或子弟取名。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中說,“胡適那樣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為什么以‘適’為名,即從《天演論》的‘適者生存’而來。孫中山手下大將陳炯明,名‘陳競存’,即從《天演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語而來。魯迅說他的世界觀,就是赫胥黎替他開拓出來的。……優勝劣敗的自然律太可怕了。”
嚴復灰心喪氣過。1900年,致張元濟的另一封信中,他“自嘆身游宦海,不能與人競進熱場,乃為冷淡生活;不獨為時賢所竊笑、家人所怨咨,而擲筆四顧,亦自覺其無謂”。就在那年,他為避“拳亂”,離開已經生活20年的天津,開始了一段南北奔走、四處謀生的日子。他去上海講過邏輯學,做過復旦公學的校長;去天津做過開灤煤礦的華人總辦;去北京做過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又去安慶做過安徽高等師范學堂監督。這些職事,他大多只是應付而已,真正念茲在茲、精神所系的是他的翻譯事業。他相信那就是他的救國大業。
大約在十年之間,嚴復陸續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自由論》)和《穆勒名學》(前半部),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學淺說》。再加上《天演論》,8部譯作近兩百萬字,西方的進化論、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邏輯學,有了相對完整的呈現。
李澤厚認為,與當時的其他思想家相比,嚴復有突出的語言優勢。在他譯書之前,中國人讀到的“西學”,大體是《汽機問答》《格致匯編》《泰西新史攬要》之類。人們費盡心思也難以從中揣摩出西方何以富強。是嚴復第一個把西方的經典原著完整帶進了中國。故而目空一切如康有為,也不得不承認嚴復“中國西學第一”。
籌安會被發起人,不在位老政論家
“籌安會之起,楊度強邀,其求達之目的,復所私衷反對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當機決絕,登報自明,則今日受責,即亦無以自解。”寫給門生熊純如的信中,嚴復如此自解。此時是1916年4月4日,十多天前袁世凱下令撤銷帝制。
列名于籌安會,常被視為嚴復一生的污點。袁世凱的美國顧問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后第三天,楊度第一次來拜訪,大談自己幾天前一把麻將贏了上萬元,運勢難擋,嚴復沒聽懂他用意何在。次日,楊度又來,問嚴復有沒有看古德諾的文章,時下的政局與清朝比怎么樣,共和是否真的足以使中國臻于富強。
嚴復感嘆道,辛亥革命之際,清室曾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當時他主張學習英國實行“虛君共和制”(清帝國國歌《鞏金甌》是他作詞)。要是被接受了,國事不致像現在這么糟。楊度馬上說,他即將和幾位同志組織一個“籌安會”,專門就中國適合共和制還是君主制作學術探討,想請嚴復當發起人。
嚴復吃驚地表示,剛才不過聊備一說。國家的改良原本不是一蹴而就的。君主制賴以維系的人君威嚴已成覆水,貿然改回去只是添亂。“每謂國家革故鼎新,為之太驟;元氣之損,往往非數十百年不易復。故世俗所謂革命,無問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盡覆已然之局者,皆為仆所不取。”
楊度磨他說,籌安會只不過做研究,搞清楚君主制是否應當恢復,其他的事到時自然會水到渠成。嚴復就說,他固然認為中國此時仍應行君主制,問題在于根本沒有合適的人選。
沒等他說完,楊度就起身告別了。
次日,楊度約嚴復參加晚宴,請柬上其余籌安會發起人之名赫然在列,嚴復以病推辭。宴散,楊度三度到訪吃了閉門羹,怏怏而去,半夜忽然派人送來一封信,明說發起籌安會是“極峰”的意思。發起啟事第二天見報,“已代公署名,不及待復示矣”。
次日,啟事發表,嚴復名列第三。嚴家門口多了兩個荷槍的壯士,說是長官擔心匪徒來相擾,派來警衛。嚴復自此閉門不出。籌安會找他去議事,便托病推辭。
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質疑后,袁世凱派秘書夏壽田帶4萬元金票去拜見嚴復,請他寫文章駁難。嚴復既沒拿錢也沒寫文章。期間,他曾收到不下二十封信函,都說非駁梁不可,還有以刺殺相威脅的。嚴復拿著信去找夏壽田,表示,“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脫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
世人所謂的“籌安會六君子”,其余五人都有“勸進文”,唯獨嚴復沒有片言只字。當時有位英國人和朋友議論說,假如袁世凱見識過人,像嚴復這樣的飽學之士,最不應該將其牽連進政治漩渦,以免摧毀國家精英。不過袁氏沒有因為嚴復不順從而殺他,比中國古代的奸雄還是好多了。
有意味的是,袁世凱撤銷帝制當回總統后,獨立各省堅持要他退位,嚴復卻不贊成,并說這并不是出于私情,而是以國家為重,“項城此時去,則天下必亂。”
嚴復與袁世凱是舊識。袁氏總督直隸時,屢次請他做幕僚而不得,說過“嚴某縱圣人復生,吾亦不敢再用”的狠話。后來袁氏被免職,議論蜂起,只有嚴復為他辯護,稱贊他的才干“一時無兩”。袁氏不免有所動,成為民國元首之后,聘請嚴復執掌京師大學堂,擔任總統府顧問、參政院參政及憲法起草委員。后來歐戰發生,嚴復曾將外國報刊上的消息社論摘要譯成中文,作為袁氏的“參考消息”。前后約有一年多時間。
嚴復評價袁世凱褒中帶貶,說他固是一時之杰,可惜“無科學知識,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可嘆的是,時無英雄,竟沒有人比他更勝任總統一職。
嚴復并不諱言袁世凱當政4年來,“生性好用詭謀以鋤異己”,“多行不義,多殺不辜;而于外強內治兩言,又復未嘗夢到”,軍伍不整,財政紛亂,“至其他根本問題,如教育、司法,尤不必論”,簡直“毫末無所措注”。不過袁氏盡失民心,一敗不可收拾,并不是因為帝制自為,最致命的是財政危機以及暗殺傳言。
嚴復認為袁世凱當然有錯,但導致他日趨專政的是不良的民主政治。中國黨人,無論帝制派或共和派,大多把國事當兒戲。數年間“中國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復萌”。“黨人、參眾兩院之搗亂,靡所不為,致國民寒心,以為寧設強硬中央”,以至于袁世凱誤以為天命所歸。他已有人君之實,卻貪慕人君之名,以致得而復失。
之后袁世凱病逝,黎元洪取而代之。時人稱賞他是忠厚長者,足可平亂息爭。嚴復卻說黎道德有余強力不足,君子治國未必不會失敗。他相信馬基雅維利之法,“今日政治惟一要義,其對外能強,其對內能治;所用方法則皆其次。……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此自極端高論,殆非世界所能有。”
民國剛建立時,嚴復就認為民眾程度不足、共和時機未到,“天下仍需定于專制”。現在他更覺得“今日最難問題”是如何脫離共和。“自吾觀之,則今日中國需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類乎此之政治家,庶幾有濟”。國運飄搖之際最需要的是強人,名義上或許不好聽,卻能使國家安定,百姓安居樂業。“此語若對眾宣揚,必為人人所唾罵。”
不久北京風傳將懲辦帝制禍首,好友林紓勸嚴復乘夜逃亡,嚴復稱自己心中無愧,安然處之。據說,他是被家人按在竹椅中抬上火車才去的天津。事后新政府發布通緝令,“六君子”中唯嚴復、劉師培不在其列。
委心任化,惟適之安
此后,嚴復再也沒有踏入政壇一步。他已年過六十,衰年多病,每到冬天,哮喘便會加劇。歐洲亙古未有的血戰令其心境越發暗淡。他開始懷疑自己一向贊頌的西方,“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字。”萬物流變、演進,自由、平等、博愛,就像莊子說的“仁義”,“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既然如此,又何必向西方去?孔孟之道不是足夠好了嗎?
離開陽岐二十多年,嚴復鄉愁無盡。1918年底,借著為三子嚴琥辦婚事的機會,他終于返鄉,還親自去看了兒子結婚用的房子。大媒是末代皇帝溥儀的漢文老師陳寶琛,對方是臺灣板橋的林家。次年元旦嚴琥娶親,酒席擺了30桌,雖是雨天,許多親友還是來了。
不到10天,就是嚴復的生日。族親故舊為他祝壽。嚴復在家門口搭了一臺戲,唱了3天,送來太平面的鄉親鄰里,都有酒喝。鄉親們都要看一看二十多年沒回家鄉的他,他站在門口的臺階上向大家表示了謝意。
也許是因為連日操勞,1月21日,嚴復突然發病。此后,他輾轉福州、上海、北京求治,幾度病危,渾身肌肉都耗盡了,只能勉強支撐。
1920年10月末回到福州后,嚴復一度想補譯完《穆勒名學》,因病未果。夜里剛剛入睡,喉嚨就發癢咳嗽。
次年端午他致信熊純如:“還鄉后,坐臥一小樓舍,看云聽雨之外,有興時稍稍臨池遣日。從前所喜哲學、歷史諸書,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談時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長此視息人間,亦何用乎!以此卻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端午節后雖一度去山上避暑,嚴復卻自認“老病之夫,固無地可期舒適”。7月,他到陽岐鰲頭山去看了將來入葬的墓園。
10月3日,嚴復自覺病重,親手寫下遺囑。他感慨自己“天稟至高,徒以中年倏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辜負了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耳順之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隨而來”。最后,給子女留下6句贈言,第一句是:“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最后一句是:“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勿造孽。”
一個月后,嚴復病逝,除了次女嚴璆,其余子女未在身邊。兩個月后,他與原配王夫人合葬于鰲頭山,青石圍幛上是他生前親題的4個字:
惟適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