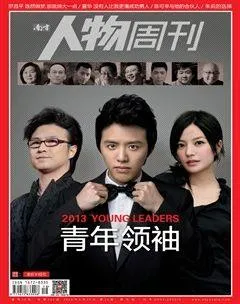王凱 干凈是公益的生命

13618639.38元,這是“愛心衣櫥基金”成立715天收到的善款。
每周二,這組公示的數字都會從千位或萬位發生變化。相對于官辦慈善機構動輒六七位數的受捐款額,這組數字從不以龐大為傲,而以苛刻的精確度撩動了人們心底的慈悲。
更為精確的是善款的使用明細。在“愛心衣櫥”啟動儀式上,王凱借用共同發起人馬洪濤的一條微博說:愛心衣櫥也許是郭美美事件之后啟動的第一只公募慈善基金,所以從誕生之日起它就知道,透明和干凈是它的生命。
第一屆慈善晚會前夜,王凱被描述成“已經起生理反應了,腦袋抬不起來”。“當晚所有拍品預估至多一二百萬,而一臺電視晚會的成本高達八九十萬”,差額讓王凱覺得對不起所有人——奔波了大半年的公益事業,請來的企業和同道好友,支持自己做公益的老東家央視,自己最初的壯志豪情……,“我對得起誰?如果結果是這樣,我就是身敗名裂。”公益的壓力最終還是體現在私利了。
當晚,現場拍出580萬元,遠超王凱預料。“愛心衣櫥”以火箭般的速度走上正軌,他也能繼續承諾“每年至少幫助20000名貧困地區小學生穿上溫暖的新衣”。
從脫明星的衣服到擠企業的錢袋子
尋呼機時代,王凱還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除了上課和在電臺主持節目,他經常在學校守著一部電話。
他對尋呼臺小姐一律說:“請回電話,我姓王。”那時知名配音演員多用漢顯機器。電話響,對方說:“王先生您好,找我有事嗎?”“老師,您好,我是廣院的學生,想跟您學配音。”王凱用準備了好久的嗓音請求。“啊,留個呼機號碼吧,有時間聯系你。”對方再無音信。
不記得四處尋到多少呼機號碼,每個號碼都是王凱進入影視配音行業的密碼。正確的開鎖密碼在朗誦藝術家徐濤手中。那之后,王凱決定“說話至死”,墓志銘就寫:此人最大的功績是一輩子說了八輩子的話,最終一口鮮血噴在話筒上。
配音對不安于現狀的王凱來說,終歸是一個愛好。依舊是對著話筒,對方卻不是觀眾。說了八輩子的話不是臺詞,而是理念灌輸和贊助乞求。
一個朦朧、美好的慈善念頭,讓他不得不再次不斷拿起電話,撥打企業老板的電話。
起初,他只想“脫下明星朋友的衣服”,進行義賣,善款用于為貧困地區的孩子添置新衣。他想做純粹的慈善,拒絕與商業行為扯上關系。但代價便是“愛心衣櫥”看上去只是一兩次慈善行為,而非慈善機構。
此時的王凱,已因央視財經頻道的《財富故事會》為人熟知。手機的另一端,是他在節目中講述的一個個成功的創業者。
“你怎么也干這個?我從來不沾這個。”多數人以“再聯系吧”為結束語,便再也不接王凱的電話。那時,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正在網上炫富。
啟動儀式上,王凱說:“感謝大家在慈善環境已經極其惡劣的情況下,還愿意相信有這么一幫人真心地在做一件好事,并且參與進來。”
面對多數人的觀望,王凱發狠:“我做公益正是時候,我要做一個最透明、走得最遠的的公益機構。”就像投資股票抄底一樣,冰點也是充滿希望的起點。
合作的起點從陳年的凡客誠品開始。
他把制衣廠商問自己的問題,拋給陳年:你有多少錢?你要做多少套?你想做什么樣的衣服?“我來搭建平臺,讓大家在這個平臺上跳舞”。
凡客提供了多版設計稿,最終“防風防雨保暖透氣,兒童沖鋒衣兩件套”被確定。男裝158元,女裝162元。而當時手中只有新浪CEO曹國偉贊助的100萬啟動資金,王凱找了個牽強的理由:想法萌生于微博,微博是140個字,你就給我每件140元吧。陳年說:“就算我捐了吧。”
不能因慈善造成不平等
王凱現在每天夜走,7公里、10公里,完全隨心所欲,“這在之前是不能想的,晚上必須睡覺,明早還要起來‘讀報’。”離開央視,他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他說自己找到了更好的方向——讓自己不從屬于任何機構,打造個人品牌。自媒體?個體戶?創業者?無所謂叫什么。王凱自媒體的第一期節目講的是辭職,只要可以自由地說“不”,他就“太滿意了”。
做配音時,他摔過廣告客戶的杯子,“對不起,你的錢我不賺了,另請高明吧。”那以后,拿腔拿調聽起來完全不是自己聲音的廣告配音他再也不接。
做公益時,他參透“公益就是公利。任何公益和公利,都不能對沖私利。一旦對沖你就無法長久”。王凱謹慎地謝絕要免費為愛心衣櫥幫忙的商家,“我要的是長線合作,不是一錘子人情買賣,公益不是不計成本的熱情玩票。”
“愛心衣櫥”在不斷自我修正,王凱對不斷的折騰有自己的理由:“沒有一檔電視節目能把企業的管理說透,我講的其實是企業家的精神。企業家精神就是堅持的勇氣和不堅持的智慧。當你彈盡糧絕時,不知道下一秒天會不會亮,堅持是抵御恐懼的能力。而預感到堅持下去是死路一條,那么思考變化。”《財富故事會》讓王凱學會了方向上的堅持和方法上的不堅持。
如果“愛心衣櫥”一直堅持起初被大家熱捧的小創意,那它今天就只是一個明星服裝回收再利用的“中介機構”,無法真正實現成立時的愿景:匯聚社會各方力量,讓貧困地區的小學生都有保暖新衣穿。
王凱對“愛心衣櫥”也規定了一個“不”——“不能因慈善造成不平等”。當有人說王凱是在發校服時,他說:我們的衣服防風防雨,比校服強多了,更重要的是、我們捐贈的對象已經是最貧困的縣,最貧困的鄉鎮、最貧困的小學了,再給他們分三六九等的話,那件衣服就成為打在孩子身上的烙印。
王凱演講時經常拿兩張照片對比,一張是孩子們穿著“愛心衣櫥”送去的衣服燦爛地笑著,一張是剛進城的孩子,見到母親被城管打,眼神中流露出讓人不寒而栗的仇恨。
他問:你想我們的孩子,與前面的這個孩子分享世界,還是與后面的這個孩子分裂這個世界?這也是王凱和“愛心衣櫥”堅持的初衷,“為了我們自己,不然,未來的社會太分化”。
人物周刊:你對自己的現狀滿意嗎?
王凱:不只是現在,我覺得沒有不滿意過,從來沒有過。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與他人分享?
王凱:我相信天道酬勤。許多人覺得不滿意是(感到)平臺或是工作沒有給自己應有的回報,實際上眼光應該放長遠,平心做事情,回報總是會有的,一分辛勞一分收獲。
人物周刊:對你父母和他們成長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們嗎?
王凱:理解。不能用現在的時代背景衡量過去,每個時代有不同的特色、不一樣的風氣、不一樣的輿論環境和政治背景,一定要放在當時去看待所有的現象。父母這一輩人,確實辛苦,趕上上山下鄉,社會動蕩。他們這一代人與那個時代一樣,相對封閉,接受新鮮事物的難度比我們要高,但并不影響他們活得精彩。
人物周刊:你對這個時代有什么話不吐不快?
王凱:這個時代挺偉大的。我相信技術改變人類生活,沒有印刷術的普及不會有宗教改革,沒有蒸汽機不會有現代民主制度的誕生。互聯網時代讓每個個體被無限尊重,個體走向成功之路會公平很多。
過去媒體人離不開任何一個媒體平臺,離開電視臺、報社、雜志社、網站,就變成一個被剝光衣服、沒有任何武器的士兵。人完全是依附于組織的。現在不一樣了,每個人通向媒體平臺的道路,和組織通向這個平臺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個人和組織之間的競爭從來沒有過如此之公平,更不要說個人和個人之間的競爭。
人物周刊:你對你所從事領域的前景怎么看?
王凱:愛心衣櫥的運作方式比較新銳。我對未來民間公益機構的成長方式抱樂觀態度。但這里也有一些障礙:制度的創新,讓民間公益組織有更多的話語權和自主權。當這個障礙被打破,民間公益機構在社會中起到的潤滑作用和縮小差距的作用會非常強大。
人物周刊:你覺得你的同齡人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王凱:一些年輕人牢騷太盛。牢騷本身是創新的開始,一切變革都是從牢騷開始。但是我們應該關注的是牢騷之后應該干什么。我們的社會、環境永遠不會讓我們滿意,為了牢騷我們多做一點事情,每個人做一點點也會發生很大的改變。牢騷派加上行動派,就是改變社會的中堅力量。
人物周刊:你認為什么樣的人稱得上有領袖氣質?在當下的人中,你最欽佩的是誰?你的同齡人中夠得上青年領袖的還有誰?
王凱:被說成領袖就是很危險的事。衣服的領子和袖子最容易臟,還是應該心懷謹慎。隨性而活,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我相信那些開拓嶄新技術并應用到人類生活領域的人。扎克伯格,通過互聯網平臺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這就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
人物周刊:權利、責任和個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個?
王凱:個人自由。沒有個人自由談不上責任、權利,一個人的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的時候,責任和權利是附加而生的。
人物周刊: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或者一部電影?
王凱:兒時影響我最大的是金庸小說,塑造了一個少年的人生觀,尤其是令狐沖為追求內心自由而選擇的方式和面對生活的態度,給我很大震撼。成年后,尤其是入職以后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我的經濟啟蒙教材,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它不單是經濟學著作,更多講的是人性,所以市場就是人心。
人物周刊:你幸福嗎?有沒有什么不安? 現在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王凱:挺幸福的。沒有個人生活的不安,最大的擔憂是民智的發展和市場的發展,與技術的前進進程和改革開放的程度,會不合拍。如果改革開放的程度能夠跟上整個歷史潮流的演進、技術的演進和人心所向的話,就沒什么擔憂。
曾是央視財經頻道名嘴的王凱,講過無數創業故事。他的第一次創業,獻給了公益事業—— “愛心衣櫥基金”,這是郭美美事件后啟動的第一只公募慈善基金,正因環境的惡劣,從誕生之日起,“愛心衣櫥”就視透明和干凈為生命。王凱對于公益,從一腔熱情的門外漢,變 成理智成熟的從業者。從躲避企業以避嫌,到懂得真正的公益要借力商業。從一身唐裝、手拿搖扇在央視直播間講述財富故事,到鞠躬作揖,四處求人,從財富故事主角那募得善款。 尷尬伴隨著喜悅一路走過來,打造了一個付出愛心的平臺,索回的是人之初的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