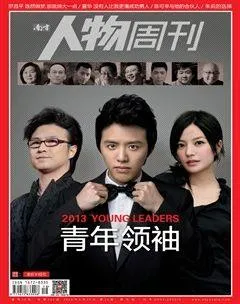陳可辛與他的合伙人

按照主持人的要求,剛剛看完《中國合伙人》的觀眾必須先回憶出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句片中臺詞,才可以向陳可辛發問。拿到話筒的女孩站起來,挑了這樣一句:我們一直想改變世界,最后才發現,其實是世界改變了我們。
“我想問陳可辛導演,這么多年了,你有沒有被這個世界改變?”
“你讓我想起我看過的一條微博,講的是一個美國老兵,每天都點著一支蠟燭在白宮前表達反戰立場,多年如一日。一個雨夜,有位記者問他:你真覺得你這么做就能改變這個國家?他告訴記者:我這么做,不是想改變這個國家,而是不想被這個國家改變。”陳可辛接著說,“回到你剛才的問題,我覺得我沒有改變世界,但也沒有被世界所改變。因為我不是一個成功的人。成功的人開始都想改變世界,但最后,都被世界改變了。”
這一幕發生在《中國合伙人》的武漢觀眾見面會上。影片首映式前,陳可辛一個人馬不停蹄地轉戰成都、武漢、上海等十幾個城市,開始公映前的宣傳沖刺。
“有人跟我說,這個片子可能會很難賣。所以我就自己先到這些城市,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告訴大家,《中國合伙人》到底講了一個怎樣的故事。”
4年前,他以監制作品《十月圍城》為首作,正式大舉北上,進軍內地組建公司。跟那時相比,他最明顯的變化是瘦了許多。新片是公司的第五部作品,由他親自執導,傾注的心血和投入的情感連身邊的朋友都感到意外。
“到目前為止,這是我最具個人風格的一部戲。它最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個人喜好和我的價值觀,甚至超越了《如果·愛》,更超越了《甜蜜蜜》。”
在中國發生的美國夢
兩年前,陳可辛正在籌備拍攝《武俠》,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將一個劇本交給他,希望他能出任監制。劇本出自新東方創始人之一徐小平,“它不是不好,而是不像在講新東方的故事,更像是徐小平的自傳。”
跟韓三平一樣,陳可辛也一直在尋找一個讓自己心動的現實主義題材的商業故事。盡管近年來他的名字差不多總是和古裝大片緊緊連在一起,但現實題材一直是他作為導演的個人強項。那些野蠻生長的創業經歷,在全世界都有共同的情懷。這種故事之所以遲遲沒能出爐,除了公司的整體戰略之外,他還有其他的顧慮。
“內地改革開放30年,有很多好故事,但很多不能拍,因為牽扯到官商政治,過審批很困難。”除了審查這個困擾中國電影的老大難之外,港人身份也讓他出手謹慎。“來內地拍戲也是很大的一個關口,你要學會在一個不同的文化環境里表達自己的喜好和訴求。”
雖然不完美,這個名為《中國合伙人》的劇本還是點燃了陳可辛的創作沖動。除了對項目品質和商業結果負責的監制身份,他更想成為這個創業故事的導演。只有導演,才能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投諸一部作品。
放眼國內影壇,他確實是一個理想的人選。12歲,他隨家人移居泰國,就讀國際學校;18歲,他赴美學習電影;21歲,他回到香港。很難再找到一個導演,會對是主是客的身份追問和夢想如何落地開花有著他這樣的深切體認。
《American dreams in China》,這是《中國合伙人》的英文片名。按照陳可辛的解釋,就是“發生在中國的美國夢”。
“美國夢其實就是equal opportunity,說白了就是機會平等、窮能致富。”陳可辛說,“American dreams in China,說白了就是中國夢。美國夢不是說一定要去美國,其實那里已經發生不了美國夢,因為社會飽和很久了,飽和之后就很難求致富。恰恰在過去這30年,每天發生最多美國夢的地方,就是中國。”
改編中,陳可辛在劇本里加入一個和自己最接近的角色,就是鄧超扮演的孟曉駿。當年在美國的餐廳打工時,一位婦人把20塊錢的小費塞到他手里,指著別的服務員告訴他:他們會在這里干一輩子,但你不一樣,你會有更大的世界。這個情節如實出現在片中。
最終成片雖在情節上跟最初劇本相去甚遠,但骨子里的氣質和血性卻一脈相通。他喜歡這個以新東方為雛形的兄弟故事,并且“教英文本身就非常有喜劇感”。尤其讓他心生共鳴的是徐小平從前在新東方負責的工作——簽證咨詢。在他眼里,這是新東方最有趣的部分,包含了新東方的所有強項。
“新東方的英文教學,說白了是把正能量給學員,就像書店販賣的那些心靈雞湯,那種東西永遠有市場。而徐小平的簽證咨詢,是幫助中國人建立自信,那是真正的跟國際接軌。西方文化永遠崇拜的是強者,而我們的傳統文化教育我們要謙遜。我們的傳統故事是孔融讓梨,西方不會讓,只會搶。面對簽證官的那5分鐘會影響很多人一輩子,每次都會問你,去美國干嘛?回不回來?不自信的人會心虛,而自信的人會理直氣壯。我去美國因為我成績好,學完之后我必須回來,因為我要回到最大的市場去賺錢、去工作。”
陳可辛一直認為,在一個剛剛開放的中國和與世界接軌的當下,新東方扮演了一個載體。他們選擇了一條跟封閉多年的中國相反的道路,幫助和教育新一代中國人認識理解西方價值觀。“對我來講這最有意思,因為我一輩子就在中國和美國的價值觀中間掙扎。所以,我才在這個跟我的生活完全無關的故事里,找到那么多地方,把我的價值觀和想法放進去。因為它跟我的成長經驗完全一樣。”
沒有永遠的合伙人
1992年,不到三十歲的陳可辛憑借導演處女作《雙城故事》在香港影壇嶄露頭角,亦師亦友的曾志偉也通過參演此片,第一次加冕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帝。他對陳可辛說:你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應該為自己打算了,不如我們開個公司吧。
這是曾志偉一直以來的情結。當年在新藝城影業公司,他和麥嘉、石天、黃百鳴、徐克、施南生、泰迪羅賓組成的7人小組,通宵達旦在工作室聊創意、談創作,11年時間用高產的數量、數部經典作品和現代企業理念在港片影史留下了濃重一筆。曾志偉希望再組公司,重現這種打拼影壇的激情歲月。
這是陳可辛電影合伙經歷的開端,由精神領袖曾志偉、負責行政的鐘珍和他組成的團隊應運而生。他給公司取名為United Film-maker Organization,縮寫是UFO。
公司開山之作是柯受良執導、梁朝偉和張學友擔綱主演的《亞非與亞基》,陳可辛出任影片監制。因為項目一波三折,影片在當時數天即可誕生一個劇本的快產快銷的香港影壇耗時一年才上映。
“不要說掙錢,公司寫字樓的租金都快交不起了,我跟志偉說,不行,壓力太大了。”陳可辛回憶,“我是個很慢的人,對品質又很較勁,這樣一來所有壓力都在我身上。我就跟他說,不如找幾個合伙人來吧。”不久,李志毅、張之亮、阮世生加盟了UFO。
一群初出茅廬的電影新人無權無勢,擁有最多的就是銳氣和干勁。當時的香港影壇流行的不是炒老粵語片的剩飯,就是功夫武俠、黑幫片和無厘頭喜劇。這群年輕人偏要獨辟蹊徑:為什么就沒有電影來拍一拍寫字樓里的那些年輕人?
后來很多次在不同的場合,陳可辛談及UFO歲月,都會說一句話:《風塵三俠》是我們當時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甚至《中國合伙人》在香港試片結束后,不止一個人建議他將片名改為《風塵三俠2013》。
這部由陳可辛和李志毅聯合執導的影片,云集梁朝偉、梁家輝、袁詠儀、周慧敏等明星,打著性喜劇的擦邊球,講述租住在同一屋檐下的3個年輕人的情感故事。兩千多萬的票房進賬雖然只有年度冠軍的一半,但它是UFO第一部大賣的影片,“就像今天一部不是通殺的《北京遇上西雅圖》大賣5個億。”那一年,公司共有6部新戲問世。
“1990年代香港的情形和今天的北京非常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去建立一個真正的中產階級。現在的80后或者75后在走向中產的過程中,開始建立自己的價值觀,開始喜歡跟自己有關的現實題材。所以《失戀33天》、《北京遇上西3OtRsT7Tb92MhKtt+J9CiA==雅圖》、《致青春》會大賣,說白了就是它們講出了你們心里的一些共鳴。當時UFO的所有電影,都是主打人文情懷,都是講情感共鳴。”
我問陳可辛:沒能將大好開局延續到底,UFO遭遇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最大的困難,其實是沒有永遠的合伙人。當企業合伙發展到不同階段,市場需求會變化,人的自尊也會變化。每個人的付出和回報,逐漸會在人心里產生不平衡。尤其在都是好人的情況下,不是賣錢的人覺得我拿少了,而是不賣錢的人會更敏感,覺得我不如退出。
“我不喜歡用藝術家這個詞,我們這些創作者都有情緒,都有壓力。開始一年6部很簡單,因為大家沒名譽沒地位,想到就拍了。逐漸有名之后,速度就慢了。下一年就沒有6部。但檔期沒戲不行,你慢就得讓他快,他為公司趕出來的一部戲,很可能也不是他喜歡的,慢慢矛盾就來了。一兩部戲不掙錢,公司就會面臨債務。掙錢了大家分都好說,但債務呢?怎么分?”
UFO的合伙歷史中,在陳可辛內心分量最重的合作不是六人團,而是和李志毅的搭檔。這是兩位惺惺相惜的好友,最初二人選擇聯合執導。“聯合矛盾就更多,尤其我們都很在乎對方的感受,有了矛盾也不拿出來說,累積下來就更有矛盾。沒名氣的時候,彼此可以講真話,片子里有什么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說。成名之后,大家有話都不會直接說,也聽不到真話了。”
1994年,陳可辛執導、也是他個人最不喜歡的《金枝玉葉》票房大獲成功之后,香港TVB電視臺用1000萬港幣一次向UFO購買了9部影片的播映版權。對于現金周轉困難的公司來說,雪中送炭的這筆巨款令陳可辛大喜過望,公司再也不會為現金發愁了。但曾志偉卻作了另一個決定:用這筆錢買樓置業。
曾志偉告訴各位合伙人:我看過這么多電影企業,沒有靠電影掙錢的。電影總是有賺有陪,賭完離場的時候,沒有人身上還有錢。最后賺錢的那些公司靠什么?地產!新藝城最后也是靠廠房賺的錢。
盡管私下陳可辛已經說服了其他合伙人,但走進會議室當曾志偉提出表決時,其他人還是都舉起了手。“他媽的我們不是都講好了嗎?”陳可辛心里在怒罵。
大家理念不一樣
UFO位于九龍塘的小洋樓當時總價2000萬,TVB的版權費作為首付之后,公司在拍片現金緊張的情況下又多了1000萬銀行貸款,原來每月5萬的行政開銷變成了10萬月供。后來那段時光彼此間充滿了太多怨氣。隨著公司被嘉禾收購,物業也以千萬作價出售,這次地產投資以慘敗出局。李志毅去日本拍《不夜城》,陳可辛去美國拍《情書》,UFO歲月結束了。
“我走的時候已經沒有憤怒了。在我心里大家早就散了,早就哀莫大于心死。所以他們最后搬離大樓的時候,我既沒有憤怒,也沒有唏噓。”陳可辛說。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武漢見面會上,一位提問的觀眾應主持人的要求,唱了一句《中國合伙人》里出現的歌詞。
“你應該唱后面那句‘外面的世界很無奈’,那才是經典所在。”陳可辛笑著說。
從外面的世界游歷歸來,陳可辛用《三更》系列熱身之后,便以《如果·愛》和《投名狀》兩部大制作試水內地。在主題并不大眾和通俗的《投名狀》票房大破兩億的2007年,沒有明星加盟的馮小剛電影《集結號》也在同檔期突破兩億,內地市場的潛力讓陳可辛作出了一個決定。
2009年2月,由他和內地導演黃建新合作的“我們制作”電影工作室,聯合內地發行公司保利博納創建了人人電影公司。
當時的報道這樣描述這次合作的前景規劃:未來3年,人人電影計劃推出15部不同類型的制作,包括星光熠熠的超級大制作,以及新晉導演的類型電影等,博納國際已特別為此撥備5億元。據博納國際總裁于冬估計:人人電影將于3年內,為內地及香港締造累計20億人民幣票房。
“最具商業頭腦的知識分子型導演”,這是很多人對陳可辛的評價定位。人人電影創業首作《十月圍城》,又是一部在商業和情懷上獲得雙贏的陳可辛監制作品。這是導演陳德森醞釀了整整10年的項目,他提出兩個小時的影片,最后一半的篇幅“60分鐘打戲無喘息”。項目啟動的前提,就是必須按照1比1的比例建一座城,重現1905年的香港中環。
“建城其實是一個策略,對于當時要上市的博納來說,它可以很快打出品牌。”對于電影拍攝來講,陳可辛也認為這座城功不可沒。《十月圍城》首次發布會是在香港國際影視展,“香港尤其懂什么是真正的明星制度,香港老百姓很清楚,《十月圍城》這個陣容跟《投名狀》根本沒法比。在發布會前3天,我們已經決定了要建城搭這個景,我就想到了這個城是最大的明星,要把這個景作為影片最大的賣點。”
根據這個思路,已經做好的發布會背景板全部推翻重做,發布現場的短片、設計圖全部圍繞建城做文章。10位主演從城里不同背景走出來,“那個氣勢一下就出來了,這個景就成了凝聚整個項目的力量。”
耗資4500萬搭建的這座城,的確如陳可辛所料,成為《十月圍城》第一主角。萬事開頭難,公司的首部影片拍得如此多災多難,遠超幾位合伙人的預計。因為雨季漫長,拍攝周期受到嚴重影響;不堪壓力的導演陳德森中途病倒,不得不暫時返港休整;因為跟基地施工方的糾紛,單日開銷七八十萬的劇組整整停工兩周……
艱難關機之日,陳可辛曾想:當著所有媒體的面,學習好萊塢的做法,把這座千辛萬苦建成的城炸掉。惟一能看見它的地方,就是在影片里。那是利用這座城做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宣發。權衡各種利弊之后,他放棄了這個想法。
如果不是有這座城,在租借影視城的傳統制片模式下,風波不斷的《十月圍城》幾乎沒有可能搶回進度,超支的數目將更加驚人。最終影片超支10%,票房2.93億。它是陳、黃、于這個備受看好的鐵三角班底合作的第一部影片,也是最后一部。
“于冬覺得那個城可以不建,而且他以前做發行,也不會像這次這樣辛苦。”分手的原因,陳可辛和于東從來沒有坐在一起聊過。“大家理念不一樣,這個可能是分開的原因。”
我寧可自己和自己打
《十月圍城》之后,“我們制作”最大的兩個項目依然是古裝大片:《武俠》和《血滴子》。兩部影片都被他稱為“公式電影”,希望復制的是《十月圍城》的成功之處,但最終雙雙遭遇票房口碑失利。
“我這個年紀,如果還對友情樂觀,那我才是有病。”陳可辛說。盡管如此,在《武俠》失利之后,他本可以叫停《血滴子》,但面對多年好友劉偉強和他已經為片子付出的半年心血,陳可辛還是選擇了如期開機,出任監制。“那個時候叫停,可能對公司帶來的損害,比不賣錢還要大。”

《中國合伙人》無疑將成為陳可辛近年來最漂亮的一戰。公映首日,它的排片超過了《泰囧》和《致青春》,創下了國產片排片最新紀錄。上映4日,票房1.32億。在一片叫好聲中,它將毫無懸念地刷新陳可辛個人票房紀錄,并很可能成為同檔期冠軍和年度贏家之一。
突然間,中國電影不約而同地開始了洶涌的集體懷舊。“今天大家對很多東西不滿,貪腐、食品安全、空氣質量、發財機會……對現實不滿就會懷舊。”
51歲的陳可辛依舊近乎偏執地用自己的方式來做電影,那就是始終尋求和專業資本及資源的合作,始終為導演身份贏得表達的尊嚴和話語權。用他的話說,“與其和一堆不專業的人在談判桌上打來打去,我寧可關起門來,自己和自己打。”歷經數段合伙經歷,知天命之年的他將在接下來選擇新的合伙方式:尋求更多的資方,共同分擔風險。
陳可辛一直醞釀著一個更大的古裝題材,那是他心目中真正合格的大片項目。陳德森當年想復原一座城,而他要用電影魔術復活的是一個朝代。票房超過十億才可能回本。當然它完全具備發展成為系列的資質。在《武俠》失利后,陳可辛暫停了這個項目。他很清楚:國產電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市場需求正在轉向。接下來他將連續拍攝幾部現實題材,這是他擅長的領域,那種輕松不較勁的自如狀態是每個導演的幸事。更重要的是,眼下市場正在如饑似渴地等待優質的現實題材。
“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在采訪的隔壁影廳,《中國合伙人》片尾曲傳了過來。“其實當年志偉買樓沒有錯,如果能扛到今天,就是好幾個億。”
《十月圍城》大獲全勝那年,我收到陳可辛公司送給媒體的一件小禮物,是一個魔術馬克杯。倒進滾燙的熱水,杯身便浮現出這樣的字:10年前,陳可辛、黃建新、于東和我探討何為悲劇。我說,悲劇就是,導演缺錢,監制缺人,發行干盜版。10年過去了,中國電影在腥風血雨中逐漸壯大,悲劇兩字于我不可同日而語,今日再道何為悲劇,我會說:欲求人人看好電影,不得不信人人電影好看。若不信,就是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