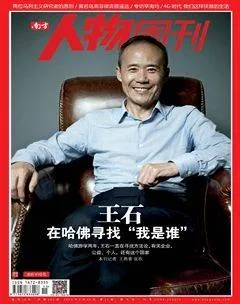薩特拯救我
說實話,我沒有一位確切的夢中情人。按前法國第一夫人布魯尼的話說:“我從不同的男人身上吸收精華,沒有人是完美的。”就如同我比較分裂的生活和愛好,我喜歡的人也各自不搭界。實際上,比起男人,我受那些強大、獨特、傳奇的女性影響多一點。比起女人,我又更愛音樂和電影。每部我喜歡的電影主角,我都會愛上5分鐘,僅僅5分鐘。我必須誠實地說,我也想有個夢中情人,可是……是誰呢?

從最初到現在一直喜歡的人包括薩特、科特尼·洛芙、巴西名模吉賽爾,還有許多沒法在這里寫出他們名字的人。他們應該也有共同之處吧,那就是,我替讀者總結出來:他們都具有不甘平庸的精神,都在他們的事業范圍內做到了極致,都充滿精神或肉體的魅力(二者很難結合在同一人身上)。
15歲開始讀薩特,坐在職業高中的教室里,我翻看《惡心》。中間有段時間疏遠了他,直到最近又把書架上的《薩特文集》拿出來重讀。初讀時看不懂他的小說和理論,只是他筆下那些個受苦的“存在主義者”太像我當時的心態,“生活是痛苦的,活著是荒謬的”。我的小說《2條命——世界上狂野的少年們》中提到了薩特的《惡心》,“惡心是因為看到了不美好的存在。”最近的一本長篇小說里,我引用了這段薩特的句子:
“我躺在地上
微風吹在我的臉上/
遠處有人正在吹口哨/
此時天正下著雨/
那是柔和而平靜的雨。”
什么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呢?如何在生活中體現出來?我相信這里面是有誤讀的。比如,薩特說“人是無用的激情”,這句話怎么理解?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里寫道,“這個名詞目前被人們隨便用來指許多許多事情,幾乎弄得毫無意義可言了……這個哲學完全是為專業人員和哲學家們提出來的。”
“人性是沒有的,因為沒有上帝提供一個人的概念。人就是人。這不僅說他是自己認為的那樣,而且也是他愿意成為的那樣。人除了自己認為的那樣以外,什么都不是。”
這段話同樣可以說明為什么我對存在主義有好感,并愿意在生活中實踐這一哲學理論。薩特說,人要對自己是怎樣的人負責。換言之,你現在的樣子完全應該由你自己負責,那是過去的你讓你現在變成這個樣子,而未來的你也只能由你自己負責——他的意思是不要抱怨任何人讓你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因為你是自由的,你完全有責任為自己負責。這理論并非不考慮環境的影響,因為薩特認為環境如何也取決于個人的選擇和努力,“他的選擇牽涉到整個人類”。我就是這么做的,如果有人把自己不幸的生活完全歸咎于別人,如果有人把自己的生活讓別人負責,我會對這個人充滿蔑視。
每每需要作出選擇的時候,我就會想到薩特。別的詩人和作家都很難讓我把他們的作品與我自己的個人生活聯系起來,海明威偶爾我會想想,別的作家幾乎都被我當成生活里的反面教材,比如菲茨杰拉德和楚門·卡波特。薩特總會主動作出選擇,并讓所有人知道。往往他的選擇是正確的,或者是酷的,比如拒絕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這可太法國,太薩特了。
我以為當一個生活中的“存在主義者”很簡單,實際上很難。我越來越發現它的難處,我知道其理論,可我常常做不到。我把薩特當成夢中情人,完全是因為我常想對他哀嚎:臣妾做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