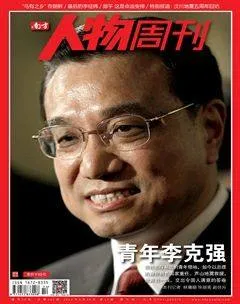削山填海平墳的瘋狂
為了獲取更多的土地,各地竭力爭取增加土地。
為了獲得土地收益與爭取中心城市地位,投資已經達到瘋狂的程度。
湖北十堰在老城區的東、西兩面大規模造城,“東部新城”的規模將達到40平方公里,“西部新城”的規模將達到46平方公里,與目前80平方公里左右的十堰城區面積相當,削山再造一個十堰。據《中國經營報》調查,僅是“西部新城”,截至目前已經削掉一百多個山頭;自2007年以來,十堰市已經“向山要地”6萬多畝,“十二五”期間還將“向山要地”9萬畝。以目前的削山速度,達到86平方公里不必等十二五期末就能完成。
延安的情況大同小異,甚至連面積、時間都差不多。從去年4月開始,延安實行 “中疏外擴,上山建城”的發展戰略,通過“削山、填溝、造地、建城”,將用10年時間,最終整理出78.5平方公里的新區建設面積,在城市周邊的溝壑地帶建造一個兩倍于目前城區的新城。
對削山造城充滿雄心壯志的蘭州,從今年4月24日起,城區周邊所有削山造地項目一律停工整頓,整改后經國土、城管執法、環保等部門審核驗收,并經市政府批準后方可開工。
造地獲得了工業項目,但各種或明或暗的隱性成本被有意忽略。據十堰工業新區管理委員會一位負責人披露,目前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約為每畝22萬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萬畝的土地整理成本就達到300億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遷安置、市政配套設施建設等,十堰市建造東部新城和西部新城的成本可能超過千億元規模。
十堰預計全年財政收入76.8億元,政府不吃不喝把十年的財政收入全都用于削山造城,也無法承擔千億元的成本規模。
政府只能靠三件事,賣地、借錢與新增收入。
從2011年開始,十堰市財政局公布市級土地出讓金收入,此后3年預算均未超過20億元,2006年至2010年則均低于10億元。若加上縣級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依照其出讓金分成比例估算),無法與土地開發的成本持平。從生地到熟地、從工業用地到住宅用地,是土地價格逐漸上升的過程,絕大部分城市工商業用地價格低廉,意在吸引投資資金。而十堰當地近年的土地供應計劃顯示,85%的供地性質系工礦倉儲用地。因此,十堰短期內想靠土地獲得巨額收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政府投融資平臺預支未來的錢就成為了首選,十堰既有十堰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這一市屬平臺,也有約10個縣級政府注資的企業。2010年的一項數據顯示,其占據了全市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近40%。這些平臺的風險不容小視。當然,十堰可以到全國或者全球引資,但它已經為支付融資利息與BT項目回購而頭疼。
更值得關注的是隱性成本,十堰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核心水源區,中央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此推出以退耕還林為主的水土保持工程,投入巨資修復遭過度開發的自然環境,現在因為開山造城,生態投入大打折扣。當地的生態是否能夠支撐如此巨大的削山投資,該城是否會成為生態災區,值得密切關注。
十堰新區的開發,并沒有伴隨著周邊縣市土地的高效利用,一個個新區空空蕩蕩。
微觀的高效可以同時千部挖掘機轟鳴,宏觀的低效,大規模生態投資的浪費、整體布局的失衡,已經在十堰這只麻雀上顯現。
可以理解十堰在東風總部撤離后的刺激,可以理解地方官員在GDP壓力下的瘋狂,可以理解初級市場經濟的人對生態的漠視,但欠缺最起碼的成本收益意識,不管子孫后代的環境,數百年后的人將驚奇地審視這個時代的瘋狂、無良與浪費。
河南平墳算什么,看看削山的城市已經平了多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