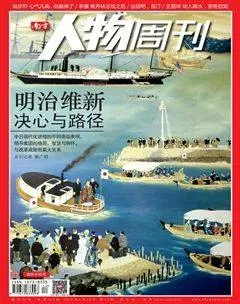沒有“萬能政府”
中國公眾通常認為,我們的政府機構重疊,人浮于事,辦事推諉,效率低下。但這只是一方面,實際上,無論公務機構怎樣龐大,公務人員怎樣敬業,他們都不大可能完成自己訂立的目標和任務,至少是表面上聲稱的那些目標和任務,因為那本身是無法完成的。
新的一年,中國政府繼續“調控房價”,國務院的政策有“新國五條”。誰都知道,房價是在調控過程中暴漲的。官方總結任何工作的時候,若對下級有批評,常常是說工作不力;下級對上級的報怨,最多說“政策不配套”。都只是表面,都不深說,不往本質上說,上下都在表面上做文章。例如就房價而言,說穿了政府上下的利益是一致的,尤其是下級政府需要土地款滋養,官方卻不便說破。
但確實有“政策不配套”的時候,而政策也不太可能真正地配套,不配套就可以給地方政府留余地,給出路。要說“政策配套”,中央政策只要一句話,各地就知道如何去配套了。這句話就是:把效果作為政績考核。這樣,各地就知道給你報一個符合要求的“效果”。這次跟“新國五條”配套的,就有這句政令。
然后,就是各地五彩繽紛的落實“新國五條”的盛況了。據《法制日報》報道,江蘇高院近日發布了《關于“新國五條”對法院工作的影響及對策建議的報告》。調控房價的政策,對“法院工作”會有什么影響呢?中國法律不是寫著依法判案么,各地法院需要獲得什么新的對策和建議才能判案呢?
“新情況”就是人們以“離婚”規避“新國五條”增加的稅種。輿論稱為假離婚,報道中引江蘇高院的文件,也稱假離婚。如果沒有引錯的話,這種措辭不太應該。沒有“新國五條”的時候,應該也有人會離婚,會涉及房產分配,不能不針對具體的案情,就預先給一個籠統的“假離婚”的判詞,這一定會冤枉了“不假”的人。
法院即便集中了全球最優秀的心理大師,也很難判斷人家離婚意愿的真假是吧?何況,人家愿意假離婚,真同居,法律管不著,法院管得著嗎?如果有人為了避稅這樣做,可能不“高尚”,如果你認為這稅“高尚”的話。但如果人家不認為這稅種高尚,愿意高調地規避它,法院能給他們一個道德判決嗎?
江蘇高院的志向,無非是要懲罰“假離婚”,“假離婚更改房主后要求復婚不予支持”。它還“建議全省法院,準確把握‘新國五條’精神實質,妥善運用法治化裁判方式,保障房地產新政有效落實”。
說白了,這是指示下級法院必要時把婚姻法獻給“新國五條”。這么說,已經非常難聽了,可是,實際上各級法院一直就是這么干的。我們在這里紙上談法,如果你去看看各地法庭上方懸掛的標語,就覺得以上的話全是迂闊。它們的標語常常少不了的是,“努力貫徹”當時流行的黨政方針,甚至徑直聲稱要把它們擺在“至上”的位置。因此,婚姻法獻給房價調控政策,刑法讓位“嚴打”,程序屈服破案率,就不太奇怪了。
當一項政令被確立為中心工作,連法律都要圍繞著它,行政手段也會曲意拱衛。據《新京報》報道,在北京,新建商品房報價“偏高”將不許發售。“偏高”怎么確定?即“明顯高于之前成交價格或周邊同品質樓盤成交價格”;那么,“明顯”怎么確定?“周邊”和“同品質”是什么意思?這真是語言的迷宮。
魯迅曾說,“有關當局”4個字,得在“當局”,而不是“有關”。有關當局不干正事就干假事,不干假事就干傻事。在這個過程中繼續消耗政府業已告罄的被信任度。
同時,公務員在這個過程中拖得很累,以至公務員的抑郁人數比例,比很多辛苦的行業高。誰都知道,給自己樹立一個漂亮的目標,包裝一些民眾向往的說辭,就能贏得期待和喝彩的時代已經不再,必須要改一改了,但政府還是愿意充當一個貌似萬能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