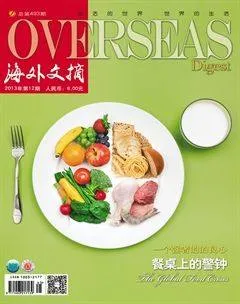迷失在人臉的海洋

雅各布·赫德斯躺在沙發上,看老劇重播。今天輪到他的室友桑尼·辛格做晚飯,他們位于布魯克林的公寓彌漫著印度食物的香味。辛格在廚房里手忙腳亂地忙活,這時有人敲門,辛格開門,一名年輕女子走了進來。“你好。”她對赫德斯說,赫德斯假裝沒注意到,將身子更深地蜷縮到沙發里,眼睛盯著電視。“也許我是認識她的”,赫德斯自言自語道,“但我實在想不起她是誰。”
“臉盲癥”從赫德斯兒時起就一直困擾著他。患這種疾病的人無力認出本應熟悉的面孔,一些患者的病情僅影響到人臉的識別,另一些人的識別困難則延伸到其他物品,如汽車和動物。嚴重的臉盲癥患者甚至可能認不出自己的父母和親戚,他們只能依靠頭發的顏色、走路的姿態、語音語調等非面部信息來識別不同的人。臉盲癥患者也沒法看電視,因為他們無法區分電視里的人物,無法將劇情繼續下去。
在全球醫學文獻中,記錄在案的臉盲癥只有大約100例。然而,達特茅斯學院、哈佛大學和倫敦大學臉盲癥研究中心的科學家們都在質疑這個病是否真的那么罕見。最新調查發現,全球2.5%的人有這種障礙,也就是說,每50個人中就有一名臉盲癥患者。如此看來,這種病一點都不罕見。
格倫·阿爾佩林自幼患有臉盲癥,他打了個非常有趣的比方,“每當看到一張面孔,大多數人用他們的大腦拍照、存儲、然后沖洗出來,而我則是拍照后,立即把膠卷扔進垃圾箱。”每個臉盲癥患者的癥狀都有所不同。他們想方設法解決問題,比如仔細注意別人穿的衣服,讓親戚們總是佩戴明顯標志物,或者學習如何發起對話、保持溝通,從而弄明白自己在跟誰說話。但這些策略并非完全奏效。
阿爾佩林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母親就經常對他進行測試,希望能刺激兒子的辨識能力。“我母親不斷改變發型,這使我很沮喪,因為我常常認不出她來。”阿爾佩林說,“但現在我們倆都老了,她知道我的病不可能真正治愈,她只是在后頸處盤個發髻,用挑染的頭發繞發髻一圈,這樣我就能認出她了。”
如果將臉盲癥的嚴重程度從低到高劃分為十個等級的話,阿爾佩林認為自己屬于第九級。他發現,甚至連認識鏡子中的自己都有困難。“我不喜歡花時間去看自己現在到底長什么樣子,因為我不在乎。”34歲的阿爾佩林說,他又高又瘦,留著長長的紅色胡須,經常把玩它。“我簡直要瘋掉了。”他母親說。很長一段時間里,她一直試圖勸說阿爾佩林刮掉胡子。“但生氣歸生氣,畢竟留長胡子是他能認出自己的唯一方式。他的協調能力不是很好,所以剃胡須肯定會自找麻煩。”
雖然因為疾病,臉盲癥患者大多是“社交白癡”,阿爾佩林卻盡力讓自己外向一些。每天回家時,他都會在家附近的老唐甜甜圈店買一份肉桂卷和草莓味牛奶。“這里的人都認識我,雖然我不認識他們,但我也會盡力和他們多打交道。”當收銀員問阿爾佩林還想要別的什么時,他笑著說,“再給我來一百萬美元就好,謝謝。”臉盲癥最令人沮喪的是使患者漸漸進入孤立狀態,阿爾佩林正在與此作斗爭。“對我而言,獨處遠比扎在人堆里要容易得多,因為我永遠無法記住那些面孔,試想一下,當你走到一個地方,每個人看起來都像孿生雙胞胎,那是什么感覺,而這是我在社交場合的必然經歷。對臉盲癥患者而言,互聯網或許是最好的東西。你可以在無需看到或記住他人面孔的前提下與之交流,建立并維護關系。”然而,缺乏直接的社交互動也導致他走上歪路。大學時,阿爾佩林就對一款在線賭博游戲上了癮,直到一張張高額的賬單點醒了他。
臉盲癥可以由嚴重腦損傷引起(如中風),也可以是先天的。
臉盲癥常常伴隨著其他缺陷,如色視力缺乏、路盲等等。阿爾佩林和家人一起去滑雪時,他就找不到從停車場到旅店的路。“但是,他在山里滑雪的時候辨別方向毫無障礙。我想是雪的緣故,白茫茫一片,讓他的腦子里遠離所有雜亂的噪音。”哥哥佩吉說。同樣的,阿爾佩林更習慣夜晚,因為晚上更安靜,辨別方向更容易。“我希望有人為格倫發明一副眼鏡,讓他只看到黑白的世界,這會使他的生活更加方便。”佩吉說。
雅各布·赫德斯就讀于紐約城市大學新聞系專業,他和室友桑尼·辛格已經在布魯克林的這所公寓里住了五年了。一開始,他常常認不出辛格,讓對方感到很困惑。“有一天,我們在街上巧遇,他卻一副完全不認識我的樣子,我在想‘咋回事?’”辛格邊說邊笑。但自從在2012年8月的一期電視談話節目中露面后,赫德斯成了臉盲癥名人。如今他的大部分同學和教授都知道了他有臉盲癥的事,讓赫德斯喜憂參半,因為周圍人總以玩笑的口吻問他:“你能認出我嗎?”
雖然從出生起赫德斯就患有臉盲癥,卻直到19歲時才確診,當時他還在念大學預科,父母正在鬧離婚,于是他借助了學校的免費心理咨詢服務。除了談論他的家庭,赫德斯還告訴咨詢師自己認識人有困難。“就在那時,他們說我可能有這種障礙癥。”當晚回到家,他上網查了很多關于臉盲癥的資料。比爾·崔歇爾患臉盲癥多年了,他在博客上分享自己的經歷,赫德斯回憶說:“我邊哭邊讀著比爾的文字,因為我多年來的抑郁經歷終于找到了解釋。”
赫德斯報名參加了波士頓臉盲癥研究中心的測試。功能磁共振成像表明,他的大腦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就是無法識別出測試中的人臉。“我能認出不同的馬、房子甚至槍,但對于人臉,我卻怎么也認不出來。”赫德斯認為自己至少需要和一個人碰面30次,才能認出對方。不過,社交網絡幫了他大忙。“臉譜網真的很有用,因為當我和某人有幾個月沒有見面時,通過該網絡平臺,我可以看到他的長相。”
位于布魯克林富爾頓街的康涅狄格松餅店是赫德斯經常光顧的地方。他坐在椅子上,將一條腿蹺在扶手上,啜飲香茶。“我喜歡旅行”,他說,“我曾去斯里蘭卡看望和我約會的女孩,那個地方真的很美。”患有臉盲癥的他是否會為旅行和維持戀情而感到害怕呢?他笑了笑:“不,沒有。但是,和我約會的女孩不停地改變發型讓我很是抓狂。那就好比每天醒來,發現身邊躺著的是不同的人。”
[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
臉盲癥患者無力認出本應熟悉的面孔,一些患者的病情僅影響到人臉的識別,另一些人的識別困難則延伸到其他物品,如汽車和動物。嚴重的臉盲癥患者甚至可能認不出自己的父母和親戚,他們只能依靠頭發的顏色、走路的姿態、語音語調等非面部信息來識別不同的人。臉盲癥患者也沒法看電視,因為他們無法區分電視里的人物,無法將劇情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