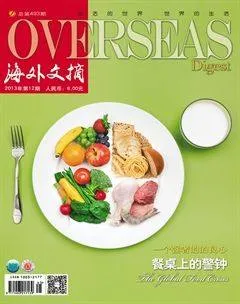醫學史上的“英雄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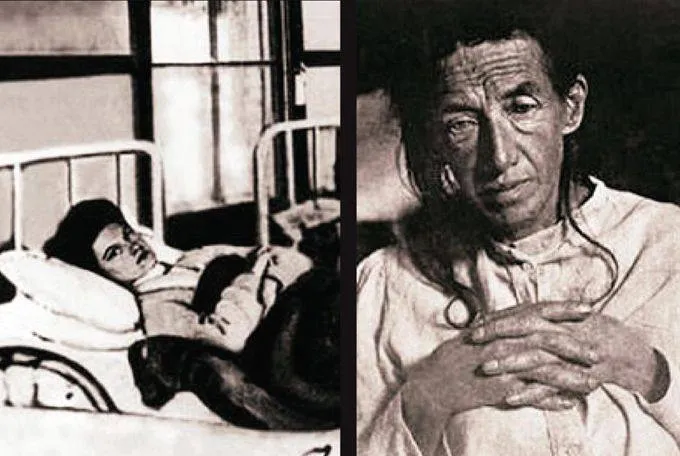
1907年,美國紐約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品行正派的女人瑪麗·馬龍因生病被捕:她體內有大量傷寒病毒病原體,并將其在人群中擴散,而她自己沒有絲毫癥狀。給她帶來厄運的疾病卻推動了傷寒研究,從而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后來,馬龍以“傷寒瑪麗”的名號被載入醫學史。
然而,就醫學怎樣對待它的英雄而言,瑪麗·馬龍的例子卻不典型。因為在那些為了醫學道路上的進步、突破而忍受痛苦的病人中,像“傷寒瑪麗”這樣著名的只是極少數。成名的大多是醫院醫生或是實驗室研究人員,病人消失在醫院檔案或實驗室記錄中,或是像瑪麗·馬龍這樣成為嚴密監禁的囚犯(她的故事至少還在以聳人聽聞為特色的街頭小報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些忍受新型未知疾病帶來的痛苦的病人,他們的命運常常被人忽略。后世知道他們,多半因為醫生把他們極其不尋常的病例記入教科書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病人的名字也常常精簡為一個字母代號。而有些病例本身就帶來了很多新認知,從而帶來醫學界的突破。它們幫助醫生理解單個器官的作用,而這正是每種醫學治療的前提。有些病例使得無法治愈的疾病變得可以治愈,有些對社會的影響遠遠超出醫學范疇,比如在司法判刑領域。直到今天,它們都還在向人類提出疑問:人類究竟是什么?
在“傷寒瑪麗”被監禁了一個世紀以后,像傷寒這樣的傳染病已經毫不重要。醫生們在每一個病例的基礎上學習,以前不敢想象的如今已是醫學常識。而那不知名病人的痛苦歷史,最多只有醫生或研究科學史的歷史學家才知道。那個本應在醫學中處于焦點位置的人,卻往往被人遺忘。
接下來我們將介紹七個醫學史上最重要的無名人士,他們每一個都代表了現代醫學史上的里程碑。
“傷寒瑪麗”瑪麗·馬龍(Mary Mallon,1869—1938)
瑪麗·馬龍是一個好廚師。她是傷寒病原體沙門氏菌長期帶菌者,自己卻沒有一點病癥。1897年到1915年,她至少接受了十家雇傭,期間至少傳染了47人,其中三人死亡。
疫員喬治·蘇培爾在瑪麗的糞便中檢出傷寒病菌后,紐約市衛生部門出于“保護公共安全”監禁了她。這件事情公開后,瑪麗·馬龍被稱為“傷寒瑪麗”,收獲了很多罵名。在那個年代,“健康帶菌者”還是一個聞所未聞的概念。瑪麗身體一直很好,她完全無法理解這突如其來的懲罰,做出了激烈的反抗。這個果敢的愛爾蘭女人曾用一個糞耙反抗監禁,卻沒有成功。一位在場的女醫生記錄:“她有著可怕的力量和效率,斗志高昂、罵罵咧咧。”
三年后,她被釋放,并被禁止從事食品相關工作。
就在她似乎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的時候,曼哈頓一家婦產醫院爆發傷寒。調查發現,瑪麗·馬龍化名為瑪麗·布朗,成為該醫院的廚師。她再次被隔離。除了短暫的間歇,她前前后后一共被關了27年,后來,她漸漸認識到傳染病的危害,也配合醫生治療,但是她體內的傷寒病菌一直頑固存在。1938年,69歲的她因肺炎去世,尸檢結果證明,她體內仍有很多活體傷寒病菌。
19世紀,傷寒被認為是不可治愈的,約占死亡人口總數的10%。而瑪麗·馬龍的例子清楚地告訴人們,就是健康的人也可能通過不干凈的水和食物傳播病原體,所以將來必須在食品生產和餐飲行業頒布衛生條例,要求衛生證明。
菲尼亞斯·蓋奇(Phineas Gage,1823—1860)
1848年9月13日,點燃爆炸裝置時的一次事故,使得一根小鐵棒飛起來穿透了鐵路工人菲尼亞斯·蓋奇的頭骨。他幸存下來,卻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腦前額葉。他的家人和朋友發現,事故后“他仿佛變了一個人”。過去那個平和的男人突然變成了一個極度情緒化的家伙,對同事毫無尊敬,愛說下流的語言,缺乏道德感,沖動、易怒。“他的理智和獸性之間的平衡被摧毀了。”他的醫生約翰·馬爾廷·哈爾勞寫道。
自蓋奇的事故之后,我們知道,腦前額葉對人的思維活動與行為表現有著十分突出的作用, 是與智力密切相關的重要腦區。哈爾勞記錄,蓋奇原本非常熱衷于按計劃辦事,手術后卻完全不同,常常因為一閃而過的念頭輕易拋棄計劃;在智力上,他只相當于一個孩子。
那之后蓋奇還活了十一年半。1860年,他死于癲癇發作。自1867年起,他的頭骨和那根鐵棒就被列在哈佛大學華倫解剖學博物館中展覽。蓋奇的病例帶來了對腦功能的認知,他成為腦外科的開路人,而在那之前人們對腦部的認知處于蠻荒階段,腦部手術幾乎都是渾水摸魚。直到今天,他還以全名出現在很多心理學書籍中。
亨利·古斯塔·莫萊森(Henry Gustav Molaison,1926—2008)
這個直到死亡都認為自己才27歲的男人,向我們解釋了什么叫記憶力。
1953年9月1日,亨利·古斯塔·莫萊森接受了一次腦部手術,有效減少了他長期忍受的癲癇的痛苦。然而,自那開始,他陷入自己的過去不能自拔。
神經外科醫生威廉·斯科維爾在他額頭兩側鉆了兩個小洞,用一根金屬吸管吸出了大部分海馬組織、一部分扁桃體以及海馬周圍的部分內側額葉組織。莫萊森也因此成為20世紀腦手術歷史上最著名的病人,他讓我們知道,海馬組織是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之間的中繼站。他能夠記起手術前發生的事情,新信息卻只能在他腦中保存幾分鐘。他的時間靜止在1953年。對他而言,就是在他2008年去世的時候,都還是1953年。問他多少歲,他永遠都說自己27。
莫萊森的命運告訴我們記憶的工作方式和分子結構。他死后,他的大腦被掃描,腦部組織為后世留存。2009年12月,歷時30多小時的莫萊森大腦切片的全過程在網上播放,全球超過40萬人觀看了現場直播。莫萊森應該感到高興。他曾說:“斯科維爾從我身上學到的,可以幫助其他人,我很高興。”盡管他很快就不記得自己說過這樣的話。
亨里耶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1920—1951)
那個患上絕癥的女人,用她患病的細胞拯救了幾百萬生命,而她也依此獲得了永生。
1951年2月1日,哈瓦德·瓊斯醫生在亨里耶塔·拉克斯的宮頸中發現了一種茄子一般大小的腫瘤。瓊斯進行了活體組織切片,證實腫瘤是惡性的。
隨后,喬治·格醫生從她的宮頸癌細胞(后被稱為“Hela細胞株”)中提取了一些樣品,結果讓他目瞪口呆:拉克斯的宮頸細胞迅速繁殖,這種細胞分裂方式是他以前從未見過的,如果不加阻止地讓腫瘤細胞分裂生長,如今它會覆蓋整個地球。
醫學界早就希望找到能夠在實驗室中持續分裂的人類細胞株。“Hela細胞株”全天24小時都在產生新一代細胞,即使對它們進行射線照射、施毒或其他方式的操縱,也絲毫沒有影響。自1951年至今,Hela細胞已有60多年歷史,分裂了18000多次,至今沒有停止的跡象,并且仍有強烈的致瘤性。即使和其他癌細胞相比,此細胞株增殖依然異常迅速,一般兩天左右即可長到3500萬到4000萬個。基于它們的研究結果,數不勝數。不管是在醫學實驗室、核測試站、太空任務中,還是在小兒麻痹癥疫苗的培育方面,它們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全球所有細胞培養實驗室里都有她的細胞。
長期以來,拉克斯一家對“Hela細胞株”來自亨里耶塔·拉克斯的事實并不知情。這個非裔美國人被埋在她工作過的煙草農場對面一個簡陋的墳墓中。直到2010年,她才獲得了一個墓志銘:“這里安息著拉克斯,她不死的細胞永遠在幫助人類。”
奧古斯特·迪特爾(Auguste Deter,1850—1906)
1901年,奧古斯特·迪特爾進入德國“法蘭克福精神病和癲癇病療養院”的時候,她的疾病可謂迷影重重。這個女人在那之前一直非常健康,既沒有遺傳病,也沒有創傷史。她的丈夫因為她荒唐的想法送她去看家庭醫生,而醫生很快把她送去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醫生阿茲海默和她的第一次對話記錄,寫進了醫學史。“您叫什么名字?”“奧古斯特。”“姓什么?”“奧古斯特。”“您的丈夫叫什么名字?”“我想是叫奧古斯特。”
迪特爾接連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她方向感喪失、記憶力減退,有閱讀和書寫障礙,發展到最后出現了幻覺和智能缺失癥狀。對她的大腦進行研究后發現,她的腦皮層比正常腦組織薄。阿茲海默注意到她的腦組織中有兩種異常現象:一個是老年瘢塊,這是他曾在老年人腦中發現過的病變,另一個是她的腦皮層組織切片中的神經元纖維纏結。神經元纏結是一種新現象,據此他確定了一種新的疾病,也就是“老年癡呆癥”,后來被命名為阿茲海默癥。
1906年,迪特爾去世時,阿茲海默寫道,她“已經完全糊涂了”。他在她大腦中發現了很多死去的神經細胞。阿茲海默認為,這證明了他的理論,精神疾病有器質上的原因。那時候,阿茲海默被人蔑稱為“拿著顯微鏡的精神病醫生”。直到1910年,精神病學教科書才第一次提到阿茲海默癥,而奧古斯特·迪特爾的名字始終沒有出現。
直到1995年阿茲海默逝世80周年時,當代醫學界開始尋找最初的文件記錄。奧古斯特·迪特爾的病例才得以重見天日。偶爾清醒的時候,她曾寫道:“可以說,我把自己弄丟了。”好在將近90年后,科學界重新找到了她。
路易斯·瓦希堪斯基(Louis Washkansky ,1913—1967)
這位54歲的蔬菜商在治療后并沒有痊愈,相反,手術導致了他的死亡。
1967年,在他轉院到南非開普敦的醫院時,已經多次心臟病發作。外科醫生克里斯提安·巴納爾德建議他接受心臟移植手術。這是醫學史上第一例由人到人的心臟移植手術。瓦希堪斯基同意了。12月3日,24歲的女孩丹妮絲·達爾瓦爾因車禍腦部嚴重受傷而去世,她的父親同意捐贈女兒的器官。當天晚上,巴納爾德就開始手術。經過一整夜的奮戰,手術于12月4日早上7點結束,接著就是更加讓人擔憂的術后護理。
術后第9天,病人出現了胸痛。此時的巴納爾德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為了阻止丹妮絲·達爾瓦爾心臟的排斥反應,醫生給他服藥,以加強抑制其免疫力。結果,18天后這顆心臟還是停止了跳動。第二天的尸檢結果讓巴納爾德懊惱不已,病人并不是死于排斥反應,而是死于肺部感染。他當時的應對,事實上加重了感染,加速了病人的死亡。另一方面,這第一次由人到人的心臟移植手術實際上成功了。它打破了心臟作為靈魂之所的神秘面紗,病人路易斯·瓦希堪斯基的名字也出現在新聞中,他成為媒體的寵兒,被昵稱為“瓦希”。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穆雷之后說,第一場心臟移植手術翻過了“移植醫學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塞爾蓋·潘克杰夫(Sergei Pankejeff,1886—1979)
塞爾蓋·潘克杰夫是俄羅斯一位貴族和大地主之子,長期患有精神疾病。1910年,私人醫生送他去維也納看一位專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根據他追溯根源的精神分析療法,認為自己在潘克杰夫的夢中找到了答案。潘克杰夫告訴弗洛伊德,四歲時他從臥室窗戶向外看到一棵樹上滿是白狼,他害怕自己會被它們吃掉。弗洛伊德對這個夢的詮釋舉世聞名:潘克杰夫一歲半的時候曾見過他的父母穿著白色內衣性交,他的神經官能受到了影響。
弗洛伊德認為,每一個成年人的神經癥都可以在其孩童時期找到源頭。這樣,有著“狼人”之稱的潘克杰夫成為他理論的主要證人。他于1918年發表的文章《摘自一例幼兒精神病史》成為潛意識研究的重要突破點。
1914年,弗洛伊德認為潘克杰夫已經痊愈。但是,他情況的改善只是暫時的,命運的打擊使他的病癥越來越嚴重,弗洛伊德的學生魯特·布倫斯維克也不能幫助他。1971年,潘克杰夫對弗洛伊德的解釋進行了反駁:他稱自己不可能看到他父母,因為他根本不和他們睡在一個房間。他使經典的精神分析學說處于質疑之中。塞爾蓋·潘克杰夫在維也納度過了他生命最后的日子,直到去世都患有抑郁癥和神經機能癥。
[譯自德國《時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