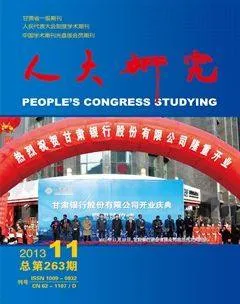調查研究與發言權
“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同志的這句名言,被人們普遍認可和接受。如果我們對這句話中調查研究與發言權的關系作一番思辨,對我們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依法履行職責頗有啟發。調查研究與發言權之有與無的關系,可以有多種組合。這里選擇其中的三種予以分析。
第一,“有調查研究,才有發言權。”這實際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另一種說法,只不過后者是以否定的句式加強語氣罷了。它強調的是,開展調查研究是有發言權的必要條件,亦即只有對事物有了深入細致地了解,提出的意見才有價值,才有將意見進行表達的必要。對于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來說,開展調查研究是依法履行職責的前提和基礎。按照監督法規定,人大常委會在審議專項工作前,可以組織常委會組成人員和代表,開展對專項工作的視察和調研。人大常委會對法律法規執行情況的檢查,也是調查研究工作的一種方式。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要圍繞監督議題,采取正確的方法,多角度、多側面地調查收集專項工作情況和有關資料,了解法律法規執行情況及其效果,厚積薄發,點面結合,客觀公正地對專項工作和執法工作作出判斷,使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有理有據,事實坐得穩,觀點拿得出,這樣才能在審議發言中有充足的底氣。
第二,“有調查研究,未必就有發言權。”從邏輯上講,調查研究只是獲得發言權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也就是說,沒有調查研究,必定沒有發言權,而有了調查研究,不一定就有發言權。要將這個必要條件變為充分條件,關鍵是通過調查研究提出意見和建議要有深度、有質量、有價值,通過實施能夠取得積極效果。一般來說,人大在組織開展的調研視察中接觸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數據和實例,感覺經驗性的東西比較多。而感覺經驗性的東西往往比較直觀、膚淺和偏面。列寧說,在社會科學領域內隨便找一些數據和實例,那簡直連兒戲都不如。因此,面對在調研視察中獲得的情況資料和數據、實例,一定要從理論上進行把握,把握那隱藏在數據和實例背后的看不見的手,也就是要深入分析決定行政執法和司法機關及工作人員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的思想前提,這樣的分析和綜合才能有深度,也才能抓住實質和根本。否則,如果只是憑感覺經驗說話,或者只是講一些空話、套話、老話,或者提一些你不講人家按照工作職責和常規也會做的事,這樣的發言權就真的沒有履行的必要了。
第三,“沒有調查研究,也可以有發言權。”這不是很荒唐嗎,沒有調查研究,沒有對工作事項進行了解,怎么能隨便發表意見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一概而論。首先,生活在現代社會,人們獲取信息的途徑是多渠道的,并不是只有搞專題調查研究一途。能對有關工作事項集中地開展一些調查研究當然很好,但對沒有機會或條件參加專題調查研究的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來說,只要平時對此項工作有了解,或者有過相關的工作經歷,或者從其他渠道也掌握了不少的情況,就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實際上,我們不能也無必要做到每個監督議題都讓全體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去開展調查研究,否則就剝奪他們的發言權。其次,沒有參加專題調查研究的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還可以針對別人的意見發表意見。比如可以思考別人了解到的事實和數據是否可靠、是否有代表性,別人的歸納是否符合邏輯、是否符合事物的發展規律,別人的觀點是否客觀公正、是否符合法律政策,別人提出的建議是否有可操作性、是否切實可行等等,只要能以理服人,就完全可以有發言權。實質上,就意見發表意見,還可以把現場辯論引入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議審議之中,使各種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互相碰撞,活躍思想和氣氛,產生智慧和真理的火花,這對提高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審議質量和水平無疑是有意義的。
調查研究與發言權的關系,有著十分豐富的內容,我們不必執其一端、不計其余,無視沒有對相關工作開展專題調查研究的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的意見,即使他們的意見不那么全面和正確。畢竟法律賦予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審議發言權,并不是僅限于他們講正確的話的權利。
(作者單位:甘肅省慶陽市人大常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