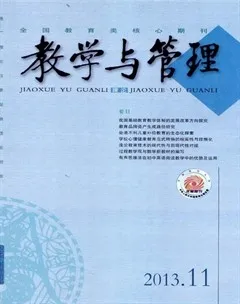數學理解的至善追求
柏拉圖對數學理解問題及數學理解的層次有過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指出,理解是從假設(較低級的形式)出發,上升到絕對原理、上升到世界的最高目的——“善”的過程,是一個從形式過渡到形式、最后停留于形式的過程,并明確地指出,這種“善”是高于幾何學推論的真正的理性。[1]他還進一步指出,數學中的“善”是一種發自人的經驗但又脫離人的經驗的純形式的理想化的境界。他的這段精彩闡述不僅粗略地揭示了數學理解的一般過程,而且提出了數學理解的最高層次是達到“善”這一重要思想。不足之處在于他的“善”的概念非常籠統,對于“究竟是什么‘善’”、“‘善’包括哪些具體內容”等問題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也許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數學思想方法這一概念,也許是因為其它原因,柏拉圖并沒有明確提出“數學理解的至善追求是數學思想方法的理解”這一命題。
此后,對“善”的研究最有影響的人物要數英國哲學家、數學家懷特海。193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所做的一次題為“數學與善”的演講中,懷特海不僅對柏拉圖始終強調的一個重要思想——“善”的思想(又稱理念)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對達到善的途徑和善的最終狀態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他從“有限”(有限的識別力、有限的知識)與“無限”(無限的宇宙)的相互關系出發,提出了“善”是一種描述無限豐富的數學世界的理想模式的思想,他指出所謂“善”,是一種理想的東西,具有無限的性質,人們正是通過模式這種有限的東西而達到對無限的宇宙——“善”的認識的。這樣,在柏拉圖眼里抽象、玄妙、讓人始終不可捉摸的“善”,通過懷特海精辟透徹的分析,使人們第一次對“善”有了一個具體而直觀的認識,那就是“善”本質上是一種描述無限豐富的數學世界的理想模式。[2]從柏拉圖與懷特海對“善”的闡述中我們也逐漸演繹出“數學理解的至‘善’追求是數學思想方法的理解”這一重要觀點。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點,下面從四個方面來具體闡述。
一、從數學理解的本質看,數學思想方法處于數學理解的最高層次
數學理解是每一個從事數學教學和數學學習的人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但究竟什么是數學理解卻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對一個事物本質的理解,就是指該事物的性質以一定的方式在學習者頭腦中呈現并能迅速提取。而數學理解就是對數學知識的正確、完整、合理的表征。”[3]也有人認為,“一個數學的概念或方法或事實被理解了,那么它就會成為個人內部網絡的一個部分。”[4]還有人認為,“學習一個數學概念、原理、法則,如果在心理上能組織起適當的有效的認知結構,并使之成為個人內部的知識網絡的一部分,那么就說明是理解了。”[5]但若從聯系的觀點來進行考察則可以清楚地發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數學理解的本質就是要在新、舊數學知識之間建立一種非人為的、實質性的聯系。
明確了數學理解的本質以后,我們再來進一步闡述“數學理解的最高層次是數學思想方法”這一觀點。為了更好地闡述這一觀點,有必要先明確一下數學思想方法的概念。關于數學思想方法,目前比較公認的說法有兩種:其一,“數學思想方法是數學概念、理論的相互聯系和本質所在,是貫穿于數學的、具有一定統攝性和概括性的概念。”[6]其二,“數學思想是指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系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它是對數學事實與數學理論的本質認識。”[7]盡管兩者的表述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把數學思想方法看作是人們對數學知識和方法所形成的規律性認識或基本看法,認為數學思想是在對較低水平的數學知識進行不斷概括、反思基礎上提煉出來的中心思想、原理或總綱。比如人們在對現實世界的數量關系進行抽象的基礎上產生了自然數的概念以及自然數的運算法則等,對自然數進一步抽象又可以將自然數用字母來進行表示(比如用N表示自然數),這樣就產生了字母代數的思想;而字母又可以進一步抽象為變量,這樣又會產生變量的思想。
由此可見,數學思想方法不同于數學概念、數學命題等理性知識,它更多表現為一種整體的、直觀的認識,它屬于理性知識但又高于通常所說的理性知識,它是一種至“善”的知識,這種知識追求的是一種數學的統一美、和諧美、簡潔美,這種知識作為一種高層次的思維形式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同時它又具有很強的直觀性,它往往會在人的頭腦中留下非常清晰的直觀形象(常常被稱為心理意象),會讓人產生清晰明確、天經地義的(被懷特海稱為自明的)感覺。若從聯系的觀點來看,數學思想方法本質上是構建各種數學知識有機聯系的方法或線索。
這樣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數學理解的至善追求是數學思想方法的理解這一命題了。從聯系的觀點來看,數學理解是在數學知識之間建立聯系,而要在眾多數學知識之間建立聯系又必須首先找到構建數學知識聯系的方法或線索——數學思想方法。可以說,數學思想方法(作為線索和方法)既是構建聯系的前提,同時又是構建聯系的目標。這樣,數學思想方法層次理解的本質就是要能夠用某個思想方法作為線索將所要理解的知識“串聯”起來,從而達到奧蘇貝爾所提出的“綜合貫通”境界。
二、從數學發展歷史看,數學思想方法是數學發展的高級階段
從數學發展歷史看,數學思想方法經歷了從模糊的感性認識到精確的數學刻劃再到形成數學方法直到最后上升為理性的數學思想這四個發展階段。
在萌芽數學時期,原始人的思維還僅僅處于主客體分化的邊緣。其內部意識活動和外部信息活動的區分是極不確定、極不明晰的,原始人的思維以模糊的感性認識為主要形式。考古研究表明,在原始人那里并沒有真正的數詞,使用的僅僅是執行數詞的功能詞。而且數本身尚未形成同類序列,還只是一種“數-總和”的混合物。[8]比如,在很多原始部落,原始人只能認識到“5”,而大于5的自然數都統稱為“多”。
進入常量數學時期,為了更加精確地刻劃研究對象,科學進入了分門別類的研究階段,人們開始利用演繹方法來探究事物之間的各種聯系,其最典型的表現是數學的公理化和推理的嚴密化。
進入變量數學時期,數學的發展從對事物靜態聯系的考察進一步發展到對事物動態發展過程的考察階段。而要全面、深入地考察事物的動態發展過程就必須準確把握事物的發展脈絡。于是,數學從過去僅僅著眼于對具體數學知識的研究逐漸過渡到關注數學知識背后的數學思想并進一步發展為立足于數學思想發展變化的高度來認識數學知識這一新階段,如用函數的思想、變換的思想來重新審視代數學和幾何學的本質等。
到了現代數學時期,數學思想方法的研究又得到全新的發展。數學思想方法的研究逐漸從幕后走到了臺前,現在,數學思想方法不再僅僅只是研究數學知識的手段或工具,數學思想方法已經直接成為數學研究的對象并迅速發展成為一門重要的數學學科——數學方法論。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過程,我們通過極限思想的發展歷史來說明這一點。
如果大家對極限的發展歷史有一點了解的話,那么應該知道極限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運用模糊、直觀的日常語言對極限思想進行定性的描述的階段
極限思想起源于無限,最初表現為對無限這一概念的模糊、直觀認識。在我國,《莊子·天下篇》中曾經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形象地反映人們對極限的直觀認識,而劉徽提出的“割圓術”則是極限思想的直接運用。在西方,無論是亞里士多德、德謨克利特等人提出的無限概念和無窮小量觀念,還是攸多克索斯提出的窮竭法,抑或牛頓、萊布尼茲提出的無窮小概念,都還只是對極限的一種直觀認識。盡管牛頓已經發明了微積分,但對極限的認識還沒有脫離直觀,還存在著很多模糊的地方。英國大主教貝克萊就曾對牛頓的無窮小概念提出了尖銳批評,并指出,“這些瞬時變化率既不是一給定的量,也不是無窮小的量,它什么也不是,它只是消失了的量的靈魂……。”[9]
2.借助于精確的數學語言對極限思想進行定量刻劃階段
微積分產生以后,人們發現微積分的基礎存在很多漏洞。為了完善其基礎,柯西采用“無限的趨近”、“任意小”等帶有模糊性的自然語言來描述極限,但這仍然不能徹底解決微積分基礎不嚴格的問題。后來,德國數學家魏爾斯特拉斯采用了精確的數學語言——“?著-N(?啄)”語言來刻劃極限,從而把微積分奠基于算術概念的基礎上,徹底解決了微積分中存在的漏洞。這樣極限從原來模糊的定性描述逐漸轉變為精確的定量刻劃并因此而導致了數學分析的產生。
3.極限成為解決問題的一種重要方法
極限的產生不僅促進了微積分基礎的嚴格化,而且還導致了諸如“?著-N(?啄)”語言、“lim”等一系列數學符號的產生。同時極限本身在解決問題中也顯示了巨大的作用,用極限既可以求導、求積分、還可以解方程、求收斂級數之和等等,其應用涉及現代數學的眾多分支,隨著極限在各種問題求解過程中的廣泛運用,極限已經成為解決數學問題的一種重要方法。
4.極限升華為一種理性的數學思想
隨著極限應用范圍的不斷擴大和應用層次的不斷加深,人們對極限的價值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逐漸形成了運用極限的思想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態度,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以直代曲”思想、“逼近”思想等重要數學思想。這表明極限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數學思想方法。
三、從人類認識數學的過程看,數學思想的理解是數學理解的最高層次
從人類對數學的理解過程來看,數學思想方法通常起源于人們的認識活動。洛克認為,理解過程從事物刺激感官所得到的簡單觀念開始(這時理解大部分是被動的),然后運用心中的主動性對簡單觀念進行合成、聯想和抽象而得到復雜觀念,大大增加人的理解力(這時候是知覺能力),理解便運用各種觀念作為材料,依照這些觀念的契合或相違(以此為范圍),通過感覺的、直覺的和推論的途徑,達到對個別事物、一般原則和上帝等對象的知識。[10]康德認為,一切人的認識都從感覺開始,再從感覺上升到概念,最后形成思想[11]。
通俗地說,數學思想方法的理解需要經歷從具有不確定性的數學活動經驗中抽取出具有確定性的數學知識,產生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然后再運用這些知識和方法來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現象,并在這種解釋世界、解決問題的數學活動過程中形成解決數學問題的觀念和態度——數學思想方法這幾個階段。
比如,在學習二分法時,一些有經驗的老師就先采用“幸運52”游戲來讓學生體驗二分的過程,當學生積累了一定的感性認識以后老師再出示具體方程讓學生猜測方程根的分布情況。如讓學生模仿“幸運52”游戲來猜方程“x5+5x-3=0”的根,先構造函數f(x)=x5+5x-3并任取兩個函數值異號的點如x=-1,x=1,由此斷定在區間(1,1)內一定有根,接著看其二等份點x=0處的函數值,發現f(0)<0,從而斷定在區間(0,1)內有根,然后再看0與1的二等份點值x=■,發現f(■)<0,這樣又可以將判定范圍縮小到區間(■,1),這樣的程序可以不斷進行下去直到找到方程的根或近似根為止。到了這個時候,老師可以“象這樣一種方法我們給它取個名字叫二分法”來點出二分法的本質。在老師的啟發與點撥下,學生頭腦中對二分法的認識從模糊、直觀逐漸變得清晰、明確,能夠逐漸理解和掌握二分法的含義及其操作程序。
學生在對二分法本質獲得更加清晰的理解以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能夠靈活運用這一方法解決各類問題,如用二分法求方程的近似解,求曲線的近似交點等。
而對二分法認識的最高階段則是形成運用二分法思想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態度和數學觀。如果學生能夠將二分法進一步上升為逼近這一重要數學思想,并能運用逼近思想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那么對二分法的理解就達到數學思想方法理解這一至“善”層次[12]。
四、從專家與新手的解題對比看,專家往往更擅長數學思想方法的理解
數學思想層次的理解是高水平數學理解的體現。德格魯特(deGroot)在對專家與新手解決問題的過程比較后發現:專家知識是圍繞核心概念或“大觀點”(bigideas)來組織的,專家解決問題常常涉及到核心概念或“大觀點”的思維方式。相反,新手的知識則極少按“大觀點”來組織,他們更多的是通過自己的日常直覺尋找正確的公式和貼切的答案。[13]腦科學的最新研究也充分揭示了這一點,一個領域的專家和新手的區別表現為專家傾向于(由于有大量的經驗)用更大的組塊來組織信息,而新手則以孤立的小塊信息來處理。[14]而是否能夠很好地進行組塊的關鍵在于解題者能否找到組塊的線索和方法——數學思想方法。這就難怪雅克·阿達瑪會認為,如果一個人習慣于在較深的層次上進行思想組合,那么他就偏重于直覺型;相反,如果某人習慣于在較淺的層次上工作,他就偏重于邏輯型。[15]比如在解“由△ABC兩邊AB、AC分別向外作正三角形ABD、ACE,求證:△ABD≌△ACE”這一問題時,新手往往只能看到這兩個三角形全等這一點,而專家則往往還能看到可以通過旋轉變換將其中一個三角形變換到與另一個三角形重合這一面。前者僅僅著眼于三角形全等判斷定理的具體運用,而后者則能立足于變換這一重要數學思想來處理數學問題。
可見,新手或初學者往往比較關注細節,而專家或復習舊知時則更關注思路或方法等宏觀方面。專家之所以比新手高明就在于專家往往能夠借助于數學思想方法或站在數學思想方法的高度來認識所研究的問題。這就難怪日本數學教育家米山國藏為什么那么看重數學思想方法,為什么始終把數學思想方法的理解作為數學素質的核心,并提出了“不管學生畢業以后從事何種工作,唯有深深銘刻于頭腦中的數學精神、數學的思維方法、研究方法、推理方法和著眼點等(若培養了這方面的素質的話),卻隨時隨地發生作用,使他們終身受益。”這一至理名言。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數學思想方法的理解是數學理解的最高層次,是數學理解的至“善”追求。
參考文獻
[1] 張學廣.維特根斯坦與理解問題.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
[2] 鄧東皋等.數學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 喻平.知識分類與數學教學.數學通報,2000(12).
[4] [美]D.A.格勞斯:數學教與學研究手冊.陳昌平等譯.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5] 李士锜.數學教育心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6] 曹才翰,蔡金法.數學教育學概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
[7] 蔡上鶴.數學思想與數學方法.中學數學,1997.
[8] 李曉明.人類認識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 M·克萊因.西方文化中的數學.張祖貴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10] 張學廣.維特根斯坦與理解問題.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
[11] 喬治·波利亞.數學的發現.劉景麟等譯.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12] 鐘志華.數學思想方法的理解探索.教學與管理,2009.
[13] [美]約翰·布蘭斯福特等.人是如何學習的.程可拉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14] [美]PatriciaWolfe.腦的功能——將研究結果應用于課堂實踐.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5.
[15] [法]雅克·阿達瑪.數學領域的發明心理學.陳植蔭,肖奚安.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