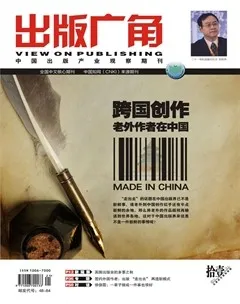童話作家的思考

兒童文學與教育的關系,實在是每一位寫作者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不同之處大抵只在于:是顯性出現還是潛性存在,是主觀訴求還是自然生成。
作為崛起于上世紀60年代的一代童話大家,孫幼軍經歷了20世紀下半葉以降所有有關兒童文學教育性的爭論。有些爭論甚至還與他的作品有所關聯。當然,孫幼軍沒有直接參與其間的論辯。他多以自己的創作給予回應,或者在自己作品的前言和后記上、為他人作品作序、座談會發言時闡釋自己的觀點,包括自己的困惑。
對于兒童文學教育性的認識,孫幼軍有一個從困惑到逐漸清晰的思考過程。
20世紀60年代初,孫幼軍將平生創作的第一部長篇童話《小布頭奇遇記》投給出版社,未被采用,出版社在退稿信中云:這部作品“主題思想不突出”,“小布頭這個主角只是作為一個反映社會的聯系物,他的思想和行動,我們也感到缺乏鮮明的教育作用。”對此,孫幼軍自己是這么認為的:“小布頭在我心目中只能是個幼兒形象,要他的‘思想行動’生出‘鮮明的教育作用’卻是我無法做到,也不想做的。所以我一時不知該怎么處理這部稿子。”該著后經小幅修改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孫幼軍曾援引金燕玉《中國童話史》所述:“在童話理論領域,從五十年代末期起,出現了一種極‘左’理論,并很快地取得主宰地位。持這種理論的人提出庸俗社會學的觀點:童話要更直接、更迅速、更深刻、更完滿地反映時代精神,表現重大主題。”這是當時童話創作的大環境。
孫幼軍說:“我面對面童話創作的這種政治要求,同時又面對孩子的審美要求,時時感到其中的矛盾。我只能在這種矛盾中求發展,一方面照顧到‘時代精神’和‘重大題材’,一方面想著孩子們,竭力使我的童話寫得‘好玩’些。這種情況持續得很久,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后一段時間。”這是一位想有所作為、想真正為兒童而寫的作者在時代潮流中苦苦尋覓方向的心靈寫照。
“我是給自己的孩子講一些‘好玩兒’、‘真逗’的故事的。但一進入創作過程,便覺這些東西無法稱得上是‘教育兒童的文學’,于是全部拋開,一心去尋找‘教育’了。時間一長,不免產生疑問:何以成人茶余飯后可以捧上一本《隋唐演義》或《福爾摩斯探案》去消遣,而孩子便無權看一篇只使他感到快樂而無需回答‘你受到了什么教育’的童話?這樣想,也就這樣說出來了。”
所幸,孫幼軍不僅這樣說出來了,還這樣寫出來了。這就是進入80年代后孫幼軍創作的《小狗的小房子》、《怪老頭兒》等作品。關于《小狗的小房子》,孫幼軍說:“1981年暑假我鼓足勇氣,寫出了《小狗的小房子》。和以往寫童話不同,這一篇沒有一點兒‘主題先行’的情況。……動筆的時候我有些猶豫,不知道人家看了這樣的東西會說什么。兩年以后,我在一篇小文里回憶當時的心情說:‘我寫了二十幾篇童話,多數都被認為‘有教育意義’,其中有那么一篇沒有的,也不至于構成什么‘傾向性’的問題。’這是在給自己壯膽兒,看得出我當時的不安。”果然,作品發表后遭到指責批評:作家究竟想告訴孩子什么?但這次的整體大環境已完全不同了。除了有評論家力挺,作品還榮獲《兒童文學》“優秀作品獎”,影響甚大的《兒童文學選刊》也給予了轉載。尤其讓作者高興的是,作品受到了小讀者們的真心喜歡。這更堅定了孫幼軍強調“真正為兒童而寫”的決心。
孫幼軍很清楚兒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孩子糾纏著要聽故事,那光景大抵也如糾纏著要吃巧克力,要買玩具,當家長的對此是心領神會的。雖說是下意識的,卻真正承認了文學社會功能之一的審美作用。于是講起來也就設法適應孩子的要求,適合他的趣味,使他得到快樂,得到美的享受。”孫幼軍這里強調“審美作用”是文學的社會功能之一,強調“趣味”“快樂”“美的享受”,顯然是在呼吁創作者擯棄狹隘的兒童文學教育觀。他認為:不宜把對孩子的教育理解得過于狹隘。“如果考慮到文學作品(尤其是童話)的功能,考慮到低幼兒童的特點,那恐怕還不僅僅是‘不夠’,怕是還‘不妥’。”
基于此,孫幼軍提出了自己的大教育觀。他指出:想象力、幽默感、美感、同情與愛等同樣具有“教育意義”。
這是一位有著重要創作實踐的童話大家的理論思考,值得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