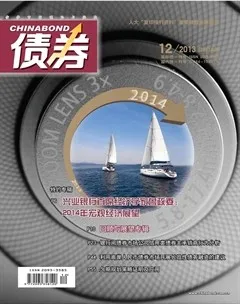利率市場化背景下債市盈利模式的思考

印象中,國內的債券市場從來沒有像2013年這樣吸引如此多的關注。先是爆諸于各大財經媒體的行業稽查,接著是登上新聞聯播的銀行間流動性問題,再到超日債違約危機等引發強烈輿論反應的信用事件。除此之外,不能不提的還有國債期貨的隆重登場,以及隨后的“犀利”走勢,國債收益率刷新九年新高,政策性金融債發行受阻……2013年,債市的話題可謂不勝枚舉,以至于市場上由此引發了一輪“文藝創作”熱潮,大家紛紛借詩詞歌賦以抒懷,抒發對市場的無助,以及對現實的難以置信。
盡管2013年的債市幾多風雨,但無論如何,過去的終將過去,在嶄新的2014年即將開啟之時,我們需要的更多是對問題的反思與認知——2013年債市的瘋狂與絕望究竟在講述什么?我們是否已經充分汲取了慘痛的教訓?是否已經有能力去收獲債市的2014?我認為相比投資收益而言,這些問題同樣價值千金,雖然在短期之內我們可能無法找到標準答案,但個人仍然希望拋磚引玉,通過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引發更廣泛的業務探討。
讓我們從今年6月份的銀行間流動性問題說起,時至今日,隨著越來越高層次的政策導向,坊間再也沒有“技術性問題”、“小概率事件”等自信說辭,轉而選擇自我調整、主動適應。原因何在?如果僅僅是認為短期內貨幣政策向著“緊平衡”一側傾斜,就未免太過單薄了。隨著三中全會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發布,以及權威部門的政策解讀,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國內的利率市場化進程開始向著“最后一公里”扎實推進。而今年9月初國債期貨的推出則給予了看漲利率者以歷史性的市場話語權。這些意味著什么?
對照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意味著越來越多觸動既得利益的改革措施開始一浪接一浪地沖擊金融機構的心理底限。以美國為例,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導致美國的實際利率長期為負,嚴重影響了社會資金的配置效率。為此,美國在1980年至1986年堅定地走完了利率市場化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放開了銀行存款利率。就貨幣政策而言,期間也發生了方向性的轉變,貨幣主義開始替代凱恩斯主義登上歷史舞臺。在沃爾克(Paul Volcker)的帶領下,美聯儲開始嚴格控制貨幣總量的供給,而將利率波動的容忍度大幅提高。不得不說,現時的中國有著非常類似的境遇。就物價而言,我們以統計范圍更加廣泛的“GDP平減指數”為例,金融危機以來,即使全球經濟增幅放緩,國內2007年至2012年的平均水平也在6%左右,相比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美國7%的CPI均值,我們沒有任何可以樂觀的資本。同樣,在此過程中由于利率管制,中國也出現了長期的實際負利率,全社會的資金配置效率亟待提高。如此一來,國內2013年6月至今的貨幣政策操作就顯得理所當然了。
不過,對于債券投資而言,除了關心貨幣政策的邏輯,大家更關心政策操作的節奏。這一問題,就國際經驗看,將主要圍繞實際利率水平展開。仍以美國為例,1年期國債實際利率水平從1981年開始轉正,最高到1984年的6.6%,而后開始逐漸回落,20世紀90年代穩定在2.5%左右的水平,可以說利率市場化帶來的實際利率攀升給美國經濟的轉型和繁榮提供了有利的市場保障。
現階段國內的情況是,經歷了半年的痛苦調整,以1年政策性金融債的收益率為例(因為我國國債的稅收制度與美國不同,所以無法直接比較),扣除物價因素,目前的實際利率也已經接近2.5%,這是除2009年物價負增長以來的歷史新高。大家可能還要問,明年實際利率會不會像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樣繼續上躥?這一問題的答案顯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我個人更傾向于認為“不會”。
原因在于,當1982年美國的實際利率首次上6%時,隨即帶來了GDP的負增長,而后實際利率的繼續攀升主要是因為物價的大幅回落,名義利率已經實質處于下降通道之中。對于中國的國情,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7.2%的經濟增長對就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個人判斷實際利率短期不太可能過快地上升,從這個意義上講,貨幣層面對于債市的第一波沖擊很可能已經結束,但就此預期收益率開始向下顯然也不現實,因為一個合適的實際正利率可以給經濟轉型增長提供“防護欄”作用,利用價格杠桿淘汰掉缺乏競爭力的低效生產,這是當下中國必需的。
至此,我們初步討論了第一個問題,即實際利率水平。但還有一個問題更加重要,那就是利差水平。眾所周知,金融企業盈利的根基在于賺取利差,當利差可靠時,還會通過主動負債來放大利差帶來收益。這一行業基礎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改變,無論利率市場化改革與否。唯一的區別在于,利率市場化以前,這一利差是受保護的,因而也就容易產生尋租,效率低下;在市場化之后,利差水平會急速收窄,攫取高利差將成為一件高技術含量的事,迫使金融機構進行技術轉型,無法適應者勢必被淘汰。
自今年6月以來,國內金融機構賴以生存的利差開始加速收窄,初步估算,債券市場融資成本較今年前5個月上升了200BP。銀行的負債成本也隨之快速攀升,理財產品收益率維持高位,以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的崛起,也加速了對銀行存款的蠶食。同樣,今年以來監管機構對債券市場的大稽查從本質上講也是對以往存在于債券一二級市場上的不合理利差進行擠壓。
作為應對利差收窄的武器,部分銀行開始躲避監管,加大杠桿配置高收益高風險資產,例如當下監管層高度重視的同業業務。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看,這樣的行為在利率市場化后期司空見慣,但其未來對應的必然是金融機構資產質量的迅速惡化,特別是當存款市場的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可以想見,如果當前不對此類行為及時規范,隨著國內銀行牌照的放開,類似的系統性風險已不再遙遠。
2014年,我們假設銀行此類無視風險及追逐高收益的行為將隨著相關法規的出臺得到控制,那么接踵而至的問題可能將是,銀行轉向配置債券,從而進一步擠壓債券投資業務的利差空間。一旦如此,國內的債券市場依舊乏善可陳,一方面實際利率水平難以回落,另一方面利差的收窄愈發明確。可以大膽做出預測,以往債券市場上多數賺錢的門路未來都將失去意義,該如何應對?
應對之策涉及盈利模式問題,這方面既引發熱議,同時也諱莫如深。但個人認為,有些事情還是顯而易見的。例如,當市場缺乏系統性的機會時,alpha策略往往是一個占優的選擇。這種尋找超額收益的策略從本質上講是對市場數據的深度挖掘,這種挖掘將不僅僅停留在找趨勢、找分位點等初級的操作,而是更進一步向著二階距、三階距的深度邁進。
過去在國內的債券市場上最主流的投資模式就是通過對宏觀經濟數據的趨勢預判給出一個所謂“合理”的評級、杠桿和久期的搭配。但實際上,這種合理性是存疑的。舉個例子,假設國內債券牛市出現的無條件概率是0.15,已知當債券牛市出現時有一種經濟現象同時也會以0.8的概率出現,但在非債券牛市的情況下這種經濟現象也有0.2的出現概率,那么當我們看到這種經濟現象時,意味著債券牛市出現的概率有多大?可能多數人都會據此認為債券牛市將會是個大概率事件,其實不然,這個概率僅有0.4而已。如果就此將組合配置得過于激進,顯然缺乏合理性。但這種不合理情況在以往的投資過程中卻屢見不鮮。
再有,假設我們已知各個債券品種的風險和收益屬性,我們該如何確定相互之間的比例關系?我們知道在博彩中有一個凱利公式(Kelly criterion),那么相應地,對于投資而言,是否也應該存在著一個基于數據分析得來的最優配置比例?這些都將是未來我們在債券投資過程中值得深入挖掘的內容。
另外,對于發達債券市場運行規律的研究也將會逐步顯現出其應有的經濟價值。例如,在美國投資級的債券與國債的利差比國內今年6月以前的水平要窄很多,這對于利率市場化后期的中國債市會有哪些啟示?關于信用債的違約風險,有數據顯示,尚德的債權回收率約30%,溫州目前的銀行貸款壞賬率約4%,這些數字純屬偶然嗎?對國內的信用利差定價又有哪些啟示?再加上國債期貨這一嶄新的風險管理工具,相信未來國內債券投資一定會有新的盈利模式登上歷史舞臺,它依仗的將不再是人脈、資源,不再是傳統的關系型金融(Relationship Finance),而是高超的投研技術,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金融。
毋庸諱言,2013年的債券市場給了我們太多深刻的記憶,也許很多年以后大家仍然會熱衷將其作為一個經驗分享的絕佳素材,原因就在于它內含的大量信息,以及對未來中國債市發展的標志性意義。在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對于債券市場的建設也有專業而深刻的規劃,要求“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國債收益率曲線”,這對于債券市場的參與者而言,既是動力,也是壓力。所以即使已經談了很多,我仍然不禁想問,2013年的債券市場還可以引發我們哪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