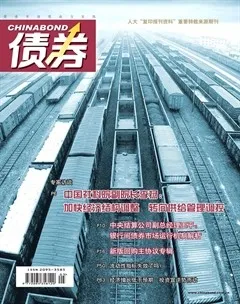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加快經濟結構調整 轉向供給管理調控

《債券》:今年一季度GDP增長率為7.7%,這一數據大大低于市場的普遍預期。您是如何分析一季度經濟形勢的?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增長數據?
李揚:今年第一季度的基準數據出來之后,總的感覺理論界和業界有點吃驚。因為2月份的數據出來后,大多數機構預測GDP增長率能達到8.2%,結果一下降到7.7%,降幅比較大,所以對于形勢需要認真地分析。
一季度大多數宏觀數據是下降的,除了GDP增長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回落2.4個百分點;3月份CPI增長率也下降到2.1%;與其相關聯,PPI也是下降的,同比增長率為-1.9%。讓我們感到比較吃驚和有壓力的是財政收入增長率的下降,1-3月累計,全國公共財政收入32034億元,同比增速只有6.9%;其中中央財政收入同比負增長,為-0.2%,這是多年以來首次出現這樣的狀況。一季度出口數據總體來看情況還可以,同比增長18.4%,但3月的數據與2月相比急降至10%,比前兩月累計出口增速回落13.6個百分點,也比較令人吃驚;固定資產投資數據走勢比較平穩。
我們把眼光放到全球來看,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出現的這樣一種下降是一種全球現象。大家知道,在4月1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調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從國際機構對中國的看法來看,也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甚至一段時間以來,國際社會“唱空”中國變成了新的時尚:先是惠譽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調降了一等,繼而穆迪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由“正面”下調至“穩定”。最近有些評級機構還在醞釀對中國的主權信用及增長前景進行下調。這些都是客觀的情況。
考慮到中國整體的潛在增長率是在向下走的,連續30年高達兩位數的增長已經創造出了奇跡,在這個基礎上如果說經濟增長速度能夠達到7.7%,能夠在7.5%-8%這樣一個區間水平上持續一段時間,也是相當好的。
社科院在去年甚至前年,就談到中國經濟在略低的或者稱之為次高的平臺上運行一段時間是很正常的,這是經過35年高速增長之后的一次正常調整。應該這樣看,在確認經濟增長企穩并有一定下滑的同時,應該認識到增長速度進入了新的常態。
《債券》:既然是“新的常態”,就有與以前不同的地方。您認為在次高平臺的這種增長與以前的增長有什么差別?
李揚:在名義增長下降的時候,當前我們更加追求沒有水分的增長。過去幾十年來在這么高速的增長過程中,也出現了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情況,現在我們把沙淘了、把水分擠出來,如果能做到,那么比過去低一兩個點的增長率是我們的福氣,代表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階段。擠出水分、比過去低一點的增長速度其實是這么多年我們孜孜以求的,只不過過去速度太快,穩不下來。現在我們有機會穩定、切實地去解決過去增長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比如增長中的水分,很多是與投資有關。一邊是很高的增長率,一邊是產能過剩,這兩種矛盾的現象已經并存很久,而且愈演愈烈。矛盾并存的背后與傳統的增長方式有關——投資拉動,要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就投資,不管投資以后會怎樣。但是不計后果是不行的,投資下來第二年要么沒有形成生產力,要么形成更多的閑置生產力,所以矛盾就這樣產生了。
一季度的情況是個非常好的案例,用另外一種方式再次深刻揭示了我國經濟中的問題和矛盾,再次讓我們深思,再次促使我們下決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把提高質量、提高效益、可持續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債券》:面對經濟增速的下滑,目前有一些人士表示出一定的擔憂,并提出要刺激經濟的主張。對此您是怎樣看待的?
李揚:我本人是堅決不主張這樣的政策取向。
分析當前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究竟居于什么位置?是刺激的、中性的還是緊縮的?從數據看得非常清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相當擴張的。
先說財政政策,比較容易看,在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長步伐放緩的情況下,財政支出增速仍然達到12.1%,顯示當前財政政策較為積極,仍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種狀況看起來還將延續。
再看貨幣政策。在貨幣信貸領域中,從數量指標來看,一季度M2同比增長15.7%,超出年初設定的13.8%的目標,而且現在看起來還很難壓下去。3月份,M2余額達到103.61萬億元,M2與GDP之比高達191%。貨幣的擴張是可以確認的。從貸款來看,一季度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4.9%,也是超出預期。更重要的,大家越來越多關注的社會融資規模,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長2.27萬億元,增長得令人可怕。從價格指標看,當前同業拆借利率、回購利率雙雙下跌,國債收益率曲線整體下移,顯示市場化的利率都在下行,這也是貨幣擴張的明確指標。
所以說,一季度GDP7.7%的增長率是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雙雙擴張的背景下出現的。因此就得警惕了:還要不要刺激經濟?如果要,我們是怎么走?沿著這個路再放水?再放貨幣?財政上不管收入怎么增長,進行更大的支出?不能夠這樣做。
《債券》:您剛才提到要改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宏觀調控政策應當如何促進這一進程的展開?
李揚:全世界這么多年來,尤其是危機以來,一直在大劑量地使用需求管理手段,包括財政刺激和貨幣擴張。對于我國而言,積極財政政策、穩健貨幣政策,說來說去都是需求的變化。接下來是延續這么多年來的需求管理還是拋棄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我本人的政策建議很明確:必須立刻止住需求管理。要排除萬難,把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放在第一位。否則以后怎么辦?
《債券》:您能具體談談需求管理所帶來的負面作用么?
李揚:需求管理本來是可以有很多作用的,而現在完全變成了經濟維穩、止瀉的手段。維穩的另一個含義,就是它延緩了結構調整。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全球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就在于結構出了問題、經濟發展方式出了問題。不調整經濟發展方式、不調整結構,這個危機是過不去的。但是,大劑量地使用需求管理手段,使得計劃之中的結構調整無限度地向后推延了。
比如我國在2009年推出的4萬億投資計劃,雖然有助于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但有一批已經被停掉的項目又被拿出來上馬,因為要先把速度搞上去。一擴張就是投資,投資沒有錢就貸款,結果出臺4萬億投資計劃的當年,新增貸款接近9.6萬億元。從M2與GDP之比,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從有統計的1982年開始,這一數據為24%,之后逐漸攀升,到2005、2006年止住了,開始出現下降。而2009年出現了跳躍式增長,2010年、2011年、2012年跟著又漲。在中央的擴張政策之后,又有地方版的擴張政策政策,需求管理非常過分。
因此,應該有這樣的判斷:這種宏觀調控方式的負面效應已大于正面效應,風險效應已大于收益效應,需求管理已至末路,必須止住。配合宏觀經濟的轉型和結構調整,宏觀政策應該轉向供給管理。
《債券》:供給管理又是怎樣的一種調控方式?
李揚:所謂供給管理,不是說管理供給,而是要使得供給機制進一步市場化。從主體來說,供給管理就是政府少干、讓企業多干,激發企業調整的活力,企業承擔調整的責任,當然企業也獲得調整的收益。從要素層面來說,就是要解放各種對要素價格形成的束縛,讓勞動力、資金、土地等要素能夠自由地流動,其定價能夠反映供求關系,能夠提供準確的信號。比如利率放開后,到底是升還是降?對此有不同看法。通過利率市場化,讓資金要素的供應和需求力量充分展示,給出準確的定價數字,才能更好地安排我國的金融戰略。
宏觀調控政策應轉向供給管理,現在也基本成為共識。不過大家對供給管理的理解也不相同,還存在一些誤解。說到供給管理,很容易將之歸于產業政策,針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給出一個正面菜單、負面菜單;在控制的范圍內嚴格控制,在鼓勵的范圍內給出稅收優惠、利率優惠,增加貸款。這些只是形式。供給管理的核心目的,是激發企業和市場的活力;它是制度化的,不是政策化的。
總之,供給管理和最近黨中央、國務院強調的一個事情有關:改革。釋放改革紅利,就是供給管理的要義。經濟上的改革,最主要就是要劃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能由市場做的交給市場做。李克強總理說:要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說得很清楚了。所以供給管理管理的要求不是說進一步加強有些管理部門的職能。現在我發現有些部門一說供給管理很高興:又該批了。供給管理又變成批文經濟,那就失敗了,比需求管理還壞。供給管理就是政府多做一些提供環境、提供標準的事情,少做一點自己直接當運動員的事情。
《債券》:談到調控方式的轉變,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并非中國所獨有,當前主要經濟體的央行都在“放水”,是否全球都面臨政策調整的問題?
李揚:放眼全球,的確主要經濟體都在進行需求管理:美國連續祭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利率連續多年在0-0.25%;歐元區原來是不放水的,隨著歐債危機的惡化,不救助整個體系就崩潰,歐洲穩定機制實際上增加了歐央行的調控能力,使其有能力增加貨幣供給、有能力調低歐元區利率。日本安倍晉三高調出場,沒上臺時就說要搞負利率、搞正的通貨膨脹,上臺之后更是采取競爭性的日元貶值,以致于其美國盟友都頗為不滿。
然而,這些經濟體存在的種種問題——以過高的消費率、過低的儲蓄率和過濫的福利制度為特征的消費拉動型經濟發展方式,以產業空心化和服務業過度發展為主要弊端的深層次結構扭曲,金融業過度放松管理和濫用金融創新形成的過高金融杠桿率,這些問題豈是簡單地增加需求所能解決的?這些痼疾依然存在。
從全球視角看,刺激政策也已經走到末路。由于需求管理長期過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遞減,恰似強弩之末。各國均實施需求擴張政策,極易引發國家和地區間的貿易戰、貨幣戰等惡性競爭。
這里不妨注意一下美國的情況。美國只要一有可能,馬上把政府的權力放下去。危機中美聯儲做了非常多的事情,買了很多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的債務、股份等資產以維穩;只要情況稍微好轉,就立刻賣出,立刻讓它回歸市場。另外鼓勵創新,強調結構調整、進行第三次工業革命等,都是供給管理方面的措施。
我覺得哪個國家比較清醒地看到這個趨勢,并且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進行轉變,哪個國家未來將會占得先機。
專家簡介
李揚博士,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副理事長。第三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2011年被評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城市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海洋研究會副理事長。
曾五次獲得 “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和論文獎。已出版專著、譯著23部,發表論文400余篇,主編大型金融工具書6部。主持國際合作、國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項目40余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