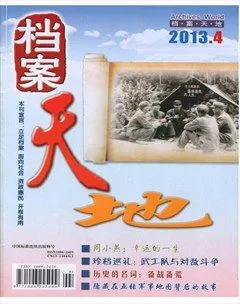備戰備荒
20世紀60年代,新中國面臨腹背受敵的嚴峻國際形勢,在這種背景下全國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規模空前的戰備活動,歷史上稱為“全國大備戰”。這次戰備,以“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為指導方針,整個國家建設以“準備打仗”為中心,國防和軍隊建設由和平時期轉入臨戰狀態。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對中國國民經濟作一次重大的區域性布局調整,對東部(“一線”)和中部(“二線”)經濟建設項目實行“停”、“壓”、”搬”、“幫”,重點開發和建設西部(“三線”、“戰略后方”)。
以這一戰略方針為基礎,后來毛澤東又根據時事情況加以補充完善,最終概括完整的口號為“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個口號后來多與“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連在一起使用,成為冷戰時期我國國際戰略防御構思的總概括。備戰備荒,由毛澤東首次提出,周恩來總結概括,后再次經毛澤東親自闡述后,于1964年作為毛主席語錄在我國大江南北廣泛傳播,成為婦孺皆知的一項全民防御口號。這一戰略口號使全國經濟建設的中心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備戰,出現了舉國備戰、全民皆兵的景象。
腹背受敵的國際環境
上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當時面臨的國際環境,可謂是內憂外患,四面楚歌,國家安全環境持續惡化,戰爭危險客觀存在,要求新中國領導人必須加強反侵略戰爭準備。
內憂外患。內憂——美帝國主義多方支持國民黨特務騷擾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妄圖建立大規模進犯大陸的“游擊走廊”,不僅如此,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政權企圖利用大陸的暫時困難不斷地進行軍事騷擾,叫囂反攻大陸;外患——帝國主義加速了對新中國實施戰略包圍的進程,世界兩大軍事陣營都對新dnE8n+/LLUJhD1OYSTvUgA==中國虎視眈眈。
東西南北,四面楚歌。在東面——一方面,我方尚未和侵略我國長達八年之久的日本恢復邦交正常化。另一方面,美帝國主義在大力支持臺灣當局加緊對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武裝襲擾和破壞的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和駐日本、菲律賓等國以及臺灣地區的美軍,每年都要在太平洋上進行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聯合軍事演習,并密謀策劃對中國的核計劃進行武裝攻擊,明目張膽地向中國炫耀武力。在西面——1962年10月,印度軍隊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悍然向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入侵,意圖蠶食我國領土。國際社會對這種公然侵犯他國領土的可恥行為不僅不給予譴責,美帝國主義居然還暗地里支持印度當局,繼續與我國為敵,使我方西部、西南部邊疆再次處于侵略戰爭威脅之中。在南面——美國于1964年8月在北部灣(又名“東京灣”),利用美艦“馬多克斯”號虛構戰斗,制造戰爭挑釁事件,史稱“北部灣事件”。這一事件使美國在侵略越南戰爭中推行逐步升級戰略,把戰火迅速從越南南方擴大到北方,將戰火引至中越邊境,并以攻擊越南為借口,時常以飛機入侵中國領空,使我國南邊的戰略形勢告急。在北面——60年代初期,隨著中蘇關系破裂惡化,中蘇邊境出現緊張局勢,昔日老大哥變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蘇修”,蘇聯對我國亦是垂涎三尺。于是,蘇聯自1964年起,在中蘇、中蒙邊境地區大量增兵,多次在邊境地區挑起事端。1966年2月,蘇蒙簽訂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蘇聯軍事力量加緊向中蒙邊境推進,在蒙古建立軍事基地和導彈基地,將戰略武器對準中國。此后,蘇聯不斷加大針對新中國的軍事威脅,僅在中蘇邊境地區的駐軍就陸續增加到40多個師。1969年前后,蘇聯又先后派出20多個軍事代表團,到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活動,企圖組織針對中國的所謂東南亞國家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當時,新中國同時面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圍堵,腹背受敵,周邊安全環境急劇惡化,在這一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面前,使國家領導人不得不把國家安全問題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去考慮,不得不高度重視國防建設和戰備工作。在1964年5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把國防建設看成是和農業并重的“一個拳頭”。同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一份批示中明確指出:必須立足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我們不僅要在戰略部署、后方設施、作戰準備和國防工業建設等方面充分注意這個問題。同時,也要在國民經濟建設方面充分注意這個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1月4日,中央軍委在關于貫徹軍委辦公會議第七次擴大會議精神情況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我們的戰備工作,必須從最困難、最復雜的情況出發,多準備幾手。要以臨戰的姿態,立即行動起來,認真加強戰備工作。1969年3月發生的蘇聯武裝入侵珍寶島事件,加上美蘇爭霸愈演愈烈的國際形勢,更加堅定了新中國領導人對“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判斷,并認為“世界大戰可能提前到來”。1969年4月,“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指導思想正式寫入黨的九大政治報告之中,成為全黨、全國、全軍一切工作的基本指導方針,全國進入臨戰狀態,全民開始搞備戰。
1965年制訂的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特別突出了戰備工作的重要地位。毛澤東提出在原子戰爭時期,沒有強大穩固的后方是萬萬不行的。由此,他提出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下決心搞好三線建設。從此,一場規模空前的全國性大戰備拉開帷幕。
“備戰備荒”的正式提出
1953年8月,毛澤東為公安部隊功臣模范代表會議題詞:“提高警惕,保衛祖國。”這個題詞隨即成為那個歲月中國人民最流行也是最關心的口號。喊著這一口號,中國人民外御強權,內以自警,轉眼到了1964年。這一年,由于上述總結的嚴峻國際環境,中國的備戰工作突然變得緊張起來。
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關于“三五”計劃初步設想的匯報后指示說:計劃要考慮三個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國家計委又對“三五”計劃的投資項目和主要生產指標進行了調整,于當年7月21日向國務院作了匯報。匯報中提出:“三五”計劃實質上是一個以國防建設為中心的備戰計劃,要從準備應付帝國主義早打、大打出發,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搶時間把三線建設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戰略大后方。
8月2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158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說:“主席要我們注意三句話,注意戰爭,注意災荒,注意一切為人民。這三句話,我把它合在一起順嘴點,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的最早提出。
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在關于各省發展農業機械化問題給劉少奇的信中,對“備戰、備荒、為人民”這一戰略口號做了具體解釋:“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蓄,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從毛澤東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備戰也好,備荒也好,一切都是為了人民。1967年4月,“備戰、備荒、為人民”作為“毛主席語錄”在全國廣為流傳。
“三五計劃”推動“三線建設”
“三五計劃”的出臺,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順利,歸納起來應該是經歷了從1966年的“起”,到1967、1968年的“落”,繼而到1969、1970年的“再起”,這樣一個跌宕起伏曲折的歷史過程。“三五計劃”的指導思想也隨著起起落落,由“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到以戰備為中心轉變。
按國民發展計劃,“三五計劃”本應在1963年到1967年實行,但是為何計劃1966年才算正式推進?又經歷了怎樣的歷史演變?
1962年,中共中央曾設想“三五計劃”主要目標是調整和恢復國民經濟,但毛澤東提出,1963年至1965年作為過渡階段,應當繼續調整打下底子,從1966年起再搞“三五計劃”。但是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出乎了毛澤東的預料,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來,正式的“三五計劃”沒有來得及形成。但歷史問題并不能阻止時代的發展,經由多方努力,在沒有正式形成計劃的歷史背景下,新中國的國民建設也在不偏離基本的軌道上繼續前進。1966年,也曾一度出現了預計提前兩年完成計劃的良好發展勢頭,但1967年、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破壞,計劃完成情況連續出現倒退,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1968年還成為我國建立計劃經濟以來惟一沒有年度計劃的一年。1969年,中蘇邊界武裝沖突使全國進入了戰備高潮,“三五計劃”以臨戰的非正常狀態取代了前三年無政府主義的非正常狀態。1970年的高投入,才使“三五計劃”勉強完成。
以上是對“三五計劃”發展脈絡總的概括,那從1962年討論計劃開始到最終具體實施,到底又經歷了什么呢?
這個計劃從1962年開始討論起,一直的設想都是要抓“吃穿用”。由于新中國剛從特大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中走出來,全國經濟形勢極其惡劣,因此,在“三五計劃”的初步設想中,主要是著眼于解決老百姓的生活問題。毛澤東對此也一度很認同。當時,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報告中強調第三個五年計劃必須以農業為基礎,毛澤東還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說:“各級計委必須克服屁股坐在工業上的毛病,要首先抓農業發展計劃和支援農業的計劃。”轉眼到了1964年,當年5月10日,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向毛澤東匯報“三五計劃”初步設想時,毛澤東除對個別項目不能上有意見外,總的看法還是一致的。但半個多月后的5月27日,毛澤東關于“三五計劃”的構想發生了徹底的轉變。27日,毛澤東顯然對編制已進行三年之久的“三五計劃”安排不滿意。這天,他找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彭真、羅瑞卿等人聽取匯報“三五計劃”的編制情況,聽說主線一是農業,二是國防,三是基礎工業時,非常生氣。毛澤東認為,前一個時期,我們忽視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來經過提醒,注意了,最近幾年又忽視“屁股”和后方了。“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這樣大幅度的改變讓與會的同志吃了一驚。
這20天中到底發生了什么,使毛澤東決定要搞“三線建設”?
原來,在國家計委向毛澤東匯報“三五”初步設想前后,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根據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的指示進行了調查研究,1964年4月,軍委總參謀部提交一份報告,讓羅瑞卿將報告送給了毛澤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報告對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進行了專題分析,認為有些情況相當嚴重。報告中說:我們對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專門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問題很多,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報告詳細列舉了全國工業過于集中、大城市人口過多、主要交通樞紐和港口碼頭過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問題,認為這些問題是關系到全軍、全民和直接影響衛國戰爭進程的一些重大問題。因此,建議由國務院組織一個專案小組,根據國家經濟的可能情況,研究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積極措施,以防備敵人的突然襲擊。這份報告引起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而當時的國內外艱險情勢也在為報告作注腳。艱險的形勢加觸目驚心的調查報告,讓毛澤東的主導思想迅速發生了變化,他的態度也很快扭轉了大家的認識。1964年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議,周恩來、鄧小平、朱德等高層領導都陸續講話,對毛澤東的看法表示支持。
1964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搞“三線建設”的主張,并且表示:“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要打仗。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沖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毛澤東的講話激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共鳴,大家一致認為,應在加強農業生產、解決人民吃穿用的同時,迅速展開三線建設,加強戰備。1965年4月12日,針對美國侵越戰爭不斷升級的趨勢,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要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盡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1965年9月初,國家計委重新草擬了《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匯報提綱》要求把建設重點放在“三線”地區,指出把“三線”建設成為初具規模的戰略大后方,是關系“三五”計劃全局和國家安危的大問題,也是解決長遠和當前備戰任務的一個根本問題。自此,全國戰備的氣氛日趨濃厚,“三線建設”全面啟動。
“三線建設”的全面開展
“三線建設”,何謂“三線”?如何劃分?“三線”的劃分主要考慮國防建設和國防安全問題,但在具體實施中也不純粹是軍事的考慮,在允許的范圍內,也盡可能地考慮了經濟的合理布局。而“三線”的范圍,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邊疆地區向內地收縮劃分三道線。一線指位于沿海和邊疆的前線地區;三線指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等西部省區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省區的后方地區,共13個省區;二線指介于一、三線之間的中間地帶。其中云、貴、川和陜、甘、寧、青俗稱為大三線,一、二線的腹地俗稱小三線。根據當時中央軍委文件,從地理環境上劃分的三線地區是:甘肅烏鞘嶺以東、京廣鐵路以西、山西雁門關以南、廣東韶關以北。這一地區位于我國腹地,共約318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土地面積的1/3,離海岸線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國土邊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別有青藏高原、云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山脈作天然屏障,在準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成為較理想的戰略后方。用今天的區域概念來說,三線地區實際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國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
所謂“三線建設”是對國民經濟所作的一次重大的區域性布局調整,就是對東部(“一線”)和中部(“二線”)經濟建設項目實行“停、壓、搬、幫”,重點開發和建設西部(“三線”)。大政方針既已確立,中共中央決定迅速展開三線建設,一是在三線建設新的工廠,擴建部分工廠;二是把一線的“獨生子”(即全國僅此一家的重要工廠)和配合后方建設所必需的工廠搬遷到三線;三是組織好全國的工業生產,為三線建設提供設備和材料。全國動員,協調完成。國家計委組織新廠建設;建委組織一線的“獨生子”的搬遷;經委組織生產三線建設需要的設備和材料。一、二線的一些省區,根據中央精神迅速行動起來,發揚局部服從整體,小局服從大局的精神,組織精兵強將支援三線建設,并在自己的腹地山區部署了一批新建和遷建項目,包括軍工、民用、交通、電力、通訊、文教、衛生等事業的建設。
對于“三線建設”,毛澤東這次卻有些憂心地說:“‘三線建設’搞不好,睡不著覺。”由此可見,當時的“三線建設”對中共中央、對毛澤東、對全中國是何等重要。重大的戰略決策一旦確定,舉國上下即以只爭朝夕的緊迫感行動起來,建設計劃以驚人的效率執行著。
三線建設,工廠搬進山溝的消息不脛而走,地方政府對這個決策既有拍巴掌的,也有皺眉頭的。拍巴掌的:工廠進山溝,無疑會給貧窮的山區帶來意想不到的經濟繁榮。皺眉頭的:眾多的工廠擁進狹窄的山溝,勢必會侵占大量的農田,在臉朝黃土背朝天的中國農民的心目中,土地就是命根子呀。無論是拍巴掌也好,皺眉頭也好,方針既已確立,向大三線搬遷工廠的備戰行動也就隨之開始了。一、二線搬遷的工廠以及援建的人員,紛紛整裝出發,浩浩蕩蕩,奔赴西北、西南,幾十萬人馬從條件優越的東部、中部,從城市、院校來到了偏僻、荒涼、落后的大西北、大西南,開始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模宏大的西部大建設。1965年開始,大小三線幾乎同時動工,可謂是舉全國之力,集全民之才,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投入之多、動員之廣、行動之快,在中國建設史上是罕見的。“三線”建設的重點項目有:修筑連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貴昆、襄渝、湘黔等幾條重要交通干線,建設攀枝花、酒泉、武鋼、包鋼、太鋼等五大鋼鐵基地以及為國防服務的10個遷建和續建項目;煤炭工業重點建設貴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盤縣等12個礦區;電力工業重點建設四川省的映秀灣、龔嘴,甘肅的劉家峽等水電站和四川省的夾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電站;石油工業重點開發四川省的天然氣;機械工業重點建設為軍工服務的四川德陽重機廠、東風電機廠,貴州軸承廠;化學工業主要建設為國防服務的項目等。在隨后的十六年中,國家總計投入2052.68億元,動員了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上千萬人次的民工建設者,在祖國的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峽谷、大漠荒原,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三線地區大范圍、大規模的建設,有力地促進了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內地與沿海的差距逐步縮小,為應付可能發生的外敵入侵、立足于打大仗筑牢了戰略大后方。三線建設,既是為了解決好防敵突襲問題、以提高國家對大規模戰爭的持續支持能力,也是“將過去背靠蘇聯建設的項目進行一次大調整,重新安排國家工業建設的布局”。三線建設規模宏大,經過十余年努力,在我國戰略后方建成了一大批機械工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等重點企業和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鐵路、公路干線和支線,建成了完整配套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電子工業基地、戰略核武器科研生產基地、航空工業基地,形成了雄厚的戰略后方生產基礎;使國家經濟布局更趨合理,增強了國防工業支持大規模反侵略戰爭的能力;調整了國防潛力布局,提高了國防的穩定性;也為邊遠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大大改變了內地經濟落后局面。“三線”地區的綜合開發,也為內地的長遠建設打下了基礎,直到今天,“三線”建設的成果仍在發揮著重要作用。
舉國備戰,全民皆兵
為把“備戰備荒”戰略方針落到實處,還需要具體的行動來實現。毛澤東隨后提出“全黨抓軍事、實行全民皆兵”的號召,指示各級黨委都要認真地抓軍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批判那種“只搞文不搞武”,“只要錢不要槍”的錯誤傾向。
1962年,毛澤東向各級黨委重申做好民兵工作要做到“三落實”,分別是組織落實、政治落實和軍事落實。首先是組織落實,要有基干民兵,有普通民兵,有兵有官;要有組織,有班、排、連、營、團、師。第二是政治落實,要做好政治工作,要設政治委員、教導員、指導員;要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壞人。第三是軍事落實,要有手榴彈,有輕武器;要搞訓練,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國際形勢瞬息萬變,1968年美蘇兩大軍事集團發生顯著變化。美國被越南戰爭所累,無暇他顧。蘇聯借機迅速擴大自身軍事力量。在此期間,中蘇兩國邊境摩擦不斷,中蘇關系迅速跌入冰點。另外,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使我方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來自與自己接壤并擁有龐大軍事力量的蘇聯的威脅日益增加,蘇聯已經接替美國成為中國國家安全最新最大的危險。有鑒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國戰略防御的重點,逐漸由南向北轉移,轉移到華北、東北、西北地區。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3月2日,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上,毛澤東又具體地談到了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戰爭的問題。1969年下半年,蘇聯的反華戰爭輿論明顯加強,蘇聯還私下里向美國等國家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外科手術式”突然襲擊的可能性,中國更直接、更嚴重地感受到來自蘇聯的戰爭威脅。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了軍委辦事組《關于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報告要求:在地方各級革委會統一領導下,吸收駐軍和地方有關部門人員,組成各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小組下設辦事機構,承辦日常業務工作。報告規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的基本任務是:組織和進行對機關、部隊和人民群眾戰略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識教育;擬制對空防御作戰計劃并組織實施,等等。為保證戰備工作的盡快展開,以適應當時十分嚴峻的戰備形勢,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發布命令,這個命令既是一個廣泛、緊急的戰爭動員號令,又是一個措辭嚴厲、態度堅決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形勢的命令。命令下達后,全國各地立即出現了傳達、貫徹命令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開各種會議,宣讀命令,布置、檢查、落實各項戰備工作。
中國的緊張的備戰工作在國際上產生了反響。1969年9月11日,應蘇聯方面的要求,周恩來在北京機場會見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雙方討論了兩國關系中的緊迫問題,特別是邊界問題。蘇聯方面表達了緩和邊界形勢的愿望。雙方商定,同年10月在北京開始中蘇邊界談判。但是,林彪等人,無視事實,仍繼續對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做出越來越嚴重的估計,認為大戰在即。10月中上旬,為防止大規模突然襲擊,中央負責人及一些老同志陸續疏散離京。10月19日到20日,許多大中城市也進行了緊急疏散或防空演習。10月中下旬,整個國家處于臨戰狀態,戰備活動進入高潮。
隨著中蘇邊界談判以后,兩國關系有所緩和,立即爆發戰爭的跡象逐漸減少,全國全軍備戰活動逐漸走向緩和。此后,各地戰備工作重點已從臨戰在即的緊張中解放出來,轉移到戰備教育、戰備動員、戰備訓練、戰備組織、物資儲備、人口疏散等方面,具體內容有:首先是戰備動員、教育。按戰時要求組織指揮機關,疏散城市人口、物資。這是當時各地普遍開展的活動之一。北京、上海、廣州、長春、鄭州等大中城市的一批高等院校或被外遷,或被裁并,或以辦五七干校、試驗農場、分校、進行革命教育實踐等名義,疏散到農村。與此同時,大批中等專業學校被裁并,教師和干部被下放。其次是修建地下防空工事。最后是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實。這是當時各級革委會普遍重視的一項工作。把工人、農民、機關干部、學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組織形式組織起來,實現全民皆兵。
轉年到了1970年,國際形勢趨于緩和,中國領導人在和平與戰爭的問題的認識上發生了一些相應的變化,“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在一些文件中更多地被代之以“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全國的戰備工作也逐漸趨于平穩發展。
“備戰備荒”的歷史影響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這場聲勢浩大的全國性戰備,使整個國家建設以“準備打仗”為中心,從六十年代中期國防和軍隊建設由和平時期轉入臨戰狀態開始,直到1985年國防和軍隊建設再次回歸至和平建設軌道結束。期間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更使得這次戰備在共和國歷史上顯示出特殊的復雜性。
決策必然有得有失,對歷史的認識,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新中國領導人向來重視戰爭準備,在戰爭年代,“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戰”是最基本的作戰原則。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始終把做好反侵略戰爭準備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并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樹立常備不懈的戰備觀念。開展全國大備戰,是新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面臨戰爭威脅、保衛國家安全的必然反應。就全國大備戰決策本身而言,其正確性不容置疑。
總的來說,全國大備戰歷經近二十年風雨,對新中國的國防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新中國的國防和軍隊建設在艱難曲折中取得了顯著成績,頂住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軍事威脅,遏止了敵人的大規模入侵,有力地保證了幾次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實現了國防的穩定,創造了相對有利的國際戰略態勢,不僅增強了我國國防實力,而且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更加有效地維護了國家安全和主權領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