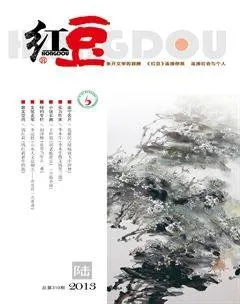一封寄不出的家書
父親:
地下好!
你呆的那個地方,可否亦是霧霾天氣?除夕夜,守夜么?放鞭炮么?煮年夜飯么?路邊一堆一堆的人,正在燒著紙錢。我不耐,這也不是悖逆。你在時都不會花錢,你走了我給你燒紙錢,我怕燒痛我的哀思,而父子之間和他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最好沒有思念,而是共度人生的歡樂與苦難。
父親,這封家書就算寄出,我估計你也是收不到了。因為我知道自己犯了理智上的錯誤。其一,你不識字,沒有閱讀能力。就算你現(xiàn)在身邊的鄰居,有閱讀能力,他也不會幫你。其二,你現(xiàn)在所屬的行政區(qū)劃,與我陰陽相隔,沒有門牌號,沒有郵政編碼,就算是神仙來當郵差,這封家書又該寄往何處,何處?
我寫這封家書,并不是因為自己腦子進了水,神經(jīng)分了叉,而是那一縷思念,不依不饒,像一頭固執(zhí)的公牛,差一點就用牛角頂翻了墓碑,非要向你傾訴。
父親,思念是一種另類鴉片。他也會上癮。等疼痛到了瘋狂的程度,這種疼痛的燃料是眼淚。眼淚也有燒盡時。而用眼淚當作語言,這種語言,真實。但一些香甜的句子,過去曾上升到一種謀生的手段,現(xiàn)在則不大有市場了。現(xiàn)在的一些香甜話一旦失去鈔票的火力支援,說得越香甜,越讓人討嫌。香甜話就是假話。為了生存,也就是為了一己之私,我有時也學會了去說,對別人,對自己,甚至對上帝。但是對你不能,我的父親。所以父親,我亦曾想到一些關于你的句子。只是這些句子,總來惹我生氣。因為屬于父親的,只有一句:種了一輩子玉米,最后累死在玉米手里。所以后來再見到玉米,我常懷愧疚和敬畏之心。而在這個句子里,就算道萬千珍重,也不再珍重。父親不是一個概念,父親就是父親,用更多句子堆砌起來的父親,根本就不是父親,為此,我還找出了另外一些原因。我之所以對一些唱爛了歌子的歌手,說爛了句子的主持人,講爛了思想的思想家,還有來自他們臉上不是來自生活的微笑,從不埋單,而是記住了父親臨行前說過的一句話:不要相信生活以外的任何東西。所以父親,我本不想把你我之間的一些事情,用一篇文字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而是讓它貓在玉米地里,一直到地老天荒。
父親,上寫到這里,我已不忍。你一生以土結緣,睡土炕,穿土布,吃土糧,走土路,土事情,土話訴。你給我留下的唯一遺產(chǎn),是你的遺照,臉上也寫滿了苦難的土色。我把其視作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最讓我動容處,是你的嘴角,居然留下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你從來不關心自己,卻不容自己不關心孩子。你的微笑,是給我留下的一份期待,一份祝福。
父親,你沒有文化,所以文化一輩子跟你過不去。村里滑舌人,使勁編排你,說你讀小人書,倒著讀。邊讀邊自語:書里人集體犯了瘋病,在集體拿大頂呢。這是文化給你的一種恥辱。所以你的人生詞典里,關于父子關系這一章,你口里從來沒有叮嚀訓斥、教訓、囑咐這些字眼。但是我知道,我身后你的眼神時時跟蹤并丈量我人生的高度。當我七歲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們的輩份還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我不敢把你當成學弟,你卻自覺把我當成了學長,樣子很是虔誠。一年四季,你從不離開土地。就是遇到沙塵暴,鋤頭也不離身。后來就有了例外,每逢聽到我的讀書聲,就扔下鋤頭,還跑到別家垅里,說:快聽!我兒在讀書呢!然后還喊將起來:最美的聲音聽了甜!有夏青,有戈藍。還有我兒小硯田。你未曾想,你兒的聲音是什么?不過小學一年級的課文《大雁朝南飛》。大字不識的父親,當了一回一句詩的詩人。父親,什么叫沒文化?沒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另類文化。就算自卑,距離自信也只差了一步。真理的前身其實只是一個又一個的錯誤。積極探索或者大膽的想象,往往是一個或另一個可能的基石。當我教你學會了書寫自己的名字,你不是也張揚了一回,把耷拉了的帽沿正了正,挺起胸,無師自通地走了一回學者的步子么?當然,那只是在月色中,無人處。本來你還能走遠一些,只是為了讓孩子懷揣著非農(nóng)民的向往走得更遠,你才甘愿與玉米為伍。用殘缺縫補殘缺,縫補出的完美才完美,從那個時候,我就認可了你,這種認可是一種申張,你是一個會寫自己名字的文化人。還有一件事。父親大煙量。平時看到任何類型的紙張,都會撕扯下來當卷煙紙。但是對我的課本和作業(yè)本,你卻把它當成圣經(jīng),從不去觸摸。有時我粗心遺失它們,你會精心收起來。幾張離群落單的鈔票,別人可以拿走,但是妄動我的書本,你會犯急。一個敢撕語錄書卷煙的人,卻對兒子的書本若此真愛,你是把不會走路的漢子,當成了兒子的腿腳。
父親,很多時候,風來,雨來,霜來,雪來。別人從地里朝屋里跑,你總是反方向,從屋里往外跑。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年夜飯,能吃上一口肉。飯上桌,你就開溜。到了夜間,總有一雙大手,在撫摸我的肚皮。那是你的手問,問兒子吃到肉了沒有。至于你自己,是空著肚皮,還是只吃了一盤白菜,你卻從不經(jīng)意。有一回,你用木輪手推車推我去趕集。你跌了,膝蓋處就血肉模糊起來,臉上痛哭萬狀,卻不是為自己,而是把毛發(fā)無損的我,緊緊抱在懷里,問:兒,你疼么?接著又說了一句只有哲學家才能說的話:農(nóng)民的兒子,不光是兒子,更是兒子。到了后來,等我也有了孩子,我才明白,有了孩子的人,自己就不是自己了。有時走在路上,看到跟你一樣年歲,一樣衣著,一樣言行,一樣操勞的農(nóng)民,我就有了一種沖動,想含淚叫人家一聲父親。父親哪!地上走著六十歲的兒子,地下睡著六十歲的父親。地上地下,永遠不會是同齡人,但卻共同承擔著父親的責任。
父親,如果把學位、官位、地位兌換成玉米的收成,我有所收成。這一點,順了你的心。但我自己卻不如意。有時有惆悵,有時有憂傷,有時有彷徨。有些事想起來,甚至有恐懼感。盡管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離職,但離職可不是離心。做文、做官、做人,一旦做到另一方面,不光是害了自己、眾人。眾人,才是一個了不得、惹不起的生命量子群。豬胖了是為了挨殺,人胖了又是為了什么?真的要問問那些失去和將要失去良知的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一人相對眾人,但愿一人也成眾人。如此想來,我認定農(nóng)民是一個干凈的職業(yè),我也真想當一回你那個版本的農(nóng)民,雖然腳上沾著牛糞,心里卻是一個干干凈凈的人。子操父業(yè),該有多好。
父親,我給你寄這封家書,其實是一個試探。如果你能收到,我會比照你的生活習性,比如:不識字,所以不讀書。無私欲,所以求靜不求動。不斗勝,所以從不爭辯。存善念,所以愛生命,愛動物。我會給你寄一臺高倍數(shù)的望遠鏡,冷眼看世界,四野盡青山。你會看到,蛇在爬,那是我們的同行者中,另一種行走。細水上飛行的鳥子,一口一口,在捕撈著純凈的日子。在一條無水之河里,一尾魚在游。我仿佛聽到了你嘿嘿的笑聲:壞小子,到大了還精靈古怪,看老子孤獨,就變成一尾魚,來騙老子一句笑聲。父親,只要你可心,豈止是魚,我還可以化作故園那一角凈土,永遠陪伴在你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