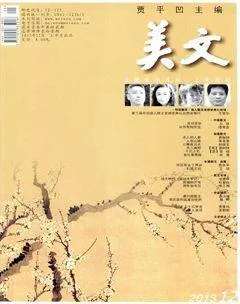芳鄰翠翠

東珠
1978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敦化市黃泥河鎮五人班村,為吉林省作協會員。現任吉林市電視臺新聞綜合頻道《財富江城》欄目組編導。
翠翠又要走了,還特意囑咐我,不用等她吃晚飯,她今晚不回來了。可愁死我了!她有一個老姨在市里一家醫院上班,每到周末她就去老姨家改善伙食、吃香的喝辣的。我最頭疼的就是翠翠不在家,真愁啊!我懷疑我的白頭發,都是趁翠翠不在家的時候,背后偷襲我并占領了我的腦殼。翠翠是我的芳鄰,睡在我的右側。她在,我還有人氣。她不在,我極有變成鬼的可能,因為我這屋里住著一群畫皮。先前我是把她們當人看的。可是一個月后,這群畫皮成天在我的房間不定時出沒,導致我的觀念漸漸轉變了,我得把她們正式當鬼看了。我都是記者了,得有這個覺悟。翠翠臨走時向我使了個眼色,意思是讓我到別的房間避避難。她剛剛扶正的睫毛俏皮又真誠,她的睫毛患有先天性“倒睫”。我從來不知道,睫毛還能生病。現在,她的睫毛被當醫生的老姨扶正了,一根一根都很敬業。我苦笑,我最討厭寄人籬下了!我曾經有過這樣一段經歷:那年我幾歲,我記不得了。總之我先被火車托運到山東,寄存在一個冬天凍死人的土屋里。又被火車托運回東北,寄存在外公家。而后,又被轉運到二姑家,繼續寄存。不到一年的時間,我被倒了三倒,差點吐血。現在這床就是我的家,哪也沒有家好。但是翠翠走了,這《聊齋》版的女子宿舍,就剩我一個觀眾了,我還必須得看,要命!我是一個膽小的人!
紅娘子,又在侍弄她的腳丫。大紅睡袍,像一個大寫的“L”裝著她。她這英文的造型,與她那侍弄腳丫的農夫形象合二為一,感覺真的很二。我發現了,她最大的領地,就是她那十個腳趾——她的十壟地。她還有一個毛病,就是總在地頭逗留,那腳趾甲修了又修。她如此珍愛自己的腳,路還是沒有走好,居然也離婚了。所以現在,一修腳,她就會想起男人。或者說一提起男人,她就一定得摸腳。現在又開始了——唉,你知道嗎?我有一次坐出租車回家,那司機相中我的腳了,說什么也不讓我下車!唉,你知道嗎?我家那個賤人,當初也是相中我的腳了!唉,你知道嗎?我是凈身出戶啊,我就是要這口志氣!唉,你知道嗎?現在那個小娘們就住在我們家!唉,你知道嗎?是我把她接到我們家的,我這樣做,他還是不滿意,他這個賤人……賤人,是她的結束語。每次說到“賤人”,我們就有指忘了,因為這時已經修到小腳趾了。然后,她稍稍停頓一下,又開始修另外一只腳,同樣把男人踩在腳下——唉,我告訴你,男人沒一個好東西,咔嚓!男人是什么德性,我最知道了,咔嚓!全世界的男人都死絕了,那才好呢,咔嚓!她說話總是帶音效,咔嚓咔嚓個沒完,剪碎的紅腳趾甲到處亂飛,長發像門簾子一樣垂到床上。我就等著她那個小腳趾來救我。我很想弄來一把鍘刀,把那孱弱的小指甲刀替下來。我覺得,只有鍘刀才能配得上她的恨。我的肚子鼓了好幾次,我想讓她閉嘴,因為我還沒有嫁人呢!她這樣把男人咔嚓得一無是處,就等于把我嫁人的決心活埋了一樣。我的話骨碌到舌尖,又咽回去了。我想她不是三只腳,兩只腳剪完自然會閉嘴。紅娘子,是我給起的名。她年紀不大,比我大十多歲。在這種情況下,我叫她娘,那是背叛。我叫她娘子,又沒有那個許可證。所以我叫她紅娘子,既符合她春心蕩漾的外形,又符合她結婚又離婚的現代史。紅娘子在我們女子宿舍,是床笫派的掌門人。她黑天白天都穿著那件大紅睡袍,從來不換,也不輕易走出女子宿舍一步。眼圈紋著眼線,眼線不褪色,比她的婚姻長壽。她就睡在我的左側,一個紅衣畫皮。
白娘子,在吃麻辣燙。一只手緊拎著裝麻辣燙的塑料袋口,一只手用筷子把里面的菜,一葉一葉地像吊寶一樣吊上來。她很怕紅娘子的腳趾甲混進口袋里,所以盡量縮小自己的就餐范圍,一直躲在門后偷吃。門后,一張小木桌,一個垃圾桶。但是,吃粉條很不成功。那粉條是滑頭!路途稍一遙遠或是坎坷一點,就容易半路改道,掉到垃圾桶里或是小木桌上,拜拜了。如此,白娘子的嘴就得伸得老長,才能把粉條收入胃袋,又是吹又是親,連哄帶騙。一根粉絲把她折騰得直淌汗珠。白娘子表面很人煙,與紅娘子恰巧睡對床。她頭發向后盤著,不是向上盤。皮膚是咖啡色,單眼皮。她對衣服的要求非常苛刻!最喜歡穿白色的連衣裙,裙子上什么綴飾也沒有,針腳都不能拋頭露面,最多只是一粒扣子。白娘子的嘴很守譜,一直喜歡麻辣燙。白娘子,也是我給起的名。因為在女子宿舍,這些離了婚的女人們,多是隱姓埋名住在這里,你無論如何是得不到真名的。真名太容易出賣她們。她們經過一次情感的搶劫,已經多多少少學會了一點自衛的基本常識。她們被婚姻一腳剔出家門,手里沒有什么像樣的武器,一切皆空,就只剩下一個真名是真的了,再也不能弄丟了。隱去真名還有很多其他的好處。比如,那些曾經與真名同生共死的稱謂——潑婦、精神病、黃臉婆、小破鞋、潘金蓮、糟糠、怨婦、蕩婦等等,也確實需要回避一下。再比如,面對一些臨時產生的新男友,假如用真名去赴約,極容易泄密,礙手礙腳。情史不同于創業史,一個女人經歷太多總讓男人胡思亂想、左右猜疑、上下打聽,然后就是放棄,怕是一個爛貨或是一個賤貨。關于爛貨和賤貨的問題,她們曾開會研究過,我是旁聽。當時白娘子的觀點非常明確——哪個爛貨不是男人制造?哪個賤貨不是男人收購?這個世界最大的悲哀就是,男人渴望外遇,又害怕遇到爛貨和賤貨。她那醫生的嘴,就是手術刀,割向男人,恨不能把他們閹割了!但是,白娘子顯然受過高等教育,說起自己的家事不像紅娘子那樣口無遮攔,歇斯底里。她的嘴也很小資,男人在她的嘴里,是另一個版本。等到紅娘子的兩只腳都修完了,她開始說了。首先,從脖頸處發出一串笑聲,預示這是喜劇——你們知道嗎?我前天回家,我就這樣笑嘻嘻地給我們家老萬打個電話,我說老萬啊,我想我們的兒子了,我還有一雙高跟鞋落在家里了,我要回家一趟,你趕快準備一下。你們知道我為什么給他打這個電話嗎?因為我怕那個女的也在我家,哈哈哈!我們家老萬忙得滴溜溜轉,像接圣駕一樣!你們猜怎么著?老萬說我還是一朵狗尾巴花,哈哈哈!那不就是得瑟嗎?便宜嗎?賤嗎?走了不說了!她總是這樣戛然而止,很抽風。她是醫生,手術刀用錯了地方,一刀一刀,把自己的婚姻宰割得清湯清水,最后只剩下了一種顏色、一張床、一碗麻辣燙。除此之外,她還有幾個臨時男友,她今天如此談笑風生,笑傲圍城、把前夫老萬玩成皇宮的太監,全是那幾個臨時男友的功勞。愛情不空巢,才能叫得更歡。謝天謝地,紅娘子和白娘子,均沒有說出“尸體”的字樣,這就等于救了我了。
但是到了晚上,我依舊不敢睡覺。因為紅娘子沒事就去廁所,啥也不做,一去就是半個小時,然后踩著朦朧的月色,晃晃悠悠地飄上床。她推門的聲音特別瘆人,一小寸一小寸地刮我的心,一根一根地抽我的筋。陰風又度鬼門關,我這個大活人死的心都有了!白娘子晚上根本不脫衣服,隨時準備接圣駕。手機短信像蛤蟆一樣,一個一個地往里蹦,叫得一樣歡,也不知道誰家的澡堂子更大。睡覺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把這樣的夜,當大年夜過了。兩個鬼一個人,我得好好想想,我這個人是怎么一失足走進了鬼屋呢?我又把自己刷新了,我是記者了。這樣,我就迎來了我生命中第三次大遷徙——從江北岸遷到江南岸。距離是一座橋,橋下是一條江。我對江沒有感覺,因為江上人煙稀少,而我需要削尖腦袋往人堆里扎。我扎進去,才有活路。我的腳趾不被踩掉,才能跑得更快。上學時我是學校里的長跑冠軍,長發飄飄。現在我也是,我從農村跑出來,甩掉一大批鋤友。我從褲店跑出來,甩掉一大批褲友。我又從手機大市場跑出來,甩掉一大批機友。再往前推算一下,我也是第一個從俺娘的肚子里跑出來,我是老大。我這樣不停地逃,不停地跑,不停地刷新自己,是因為我不想如此短命。世上最無情的就是商業,想甩你,理由是鈔票。想愛你,理由還是鈔票。它只認得錢。與它萬里長征,年景好的時候,它是人民幣。年景不好,它就是冥幣。這些短命的營生,拖著我的長腿,早晚得把我拖垮。我的終級目標是與筆友同伍,與他們賽跑,最好孤獨求敗。但是現在的我,充其量只是一個簡易的鉛筆擰、或者是殘缺的橡皮擦——經過一次考試,我是記者了!電視臺的大門向我敞開了!要到達那扇門,需要經過一條江和一座橋。那江叫松花江,那橋叫吉林大橋。我依舊很矜持,面對江,我沒有投懷送抱。我只是對出租車司機說慢點開。我的眼淚嘩嘩地流,我知道松花江有這個承載能力。那個司機說,到電視臺上班,應該高興啊,你說你怎么還哭上了呢?我不做聲。那個司機又問,是走后門去的?能在電視臺工作可不容易啊……我還是不做聲。在我百感交集的時候,我不太喜歡第三者。過了橋,我便不再哭。因為我知道,離開了廣闊的水域,我的眼淚將無處安放。我把自己刷新了,我要換一個女子宿舍。電視臺的椅子有我的一把,江南岸的床卻沒有我一張。一想到這里,我就苦笑:全身上下,只有屁股高枕無憂。再一想,這城市里大多數人的情況都是這樣的——看局部,很精彩。看全部,很荒唐。我還記得我剛來時,房東問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說我是記者。房東想了一下,就把我安排在了這里。唯一的好處是,這間房子向陽。可是,與這群女鬼畫皮住在一起,向陽有什么用呢?
晚上不睡覺,胃也不睡。大腸小腸都在胃的指揮下值夜班。天還沒亮我就餓了。一餓,我就很想翠翠。只有天快亮的時候,那兩個女鬼才會睡著,她們非常遵守鬼的規則。房東也養了幾只雞,但不為鬼服務,從不會起大早打鳴,一直與人保持著相似的作息。我依舊不敢看她們,用俺娘的話說,看到眼里就挖不走了。我只能看天,天空的星,被黑夜吃得所剩無幾。碎星殘片,就等著陽光來收拾。我就等著翠翠來收拾,翠翠是我的陽光。我一直認為我很強悍,遇到翠翠后我才知道,我也會柔弱。是她的出現,讓我身上雪藏了近一年的女性元素日益凸顯。因為在以前,我雖然是頂著一張女人皮,卻一直是以老爺們的悲壯行走人世的。翠翠來自附近的一個小山村,她還有一個妹妹。她家是養兔專業戶,滿山的兔子,特能生育,賣個十幾只就夠過活一陣子。所以,翠翠沒有太多的生存壓力,她唯一需要做的,是以長女的身份贍養父母,在村里大聲說話,扛起父母沒有生出男孩的遺憾。翠翠很努力,也很獨立。翠翠有一個口頭禪——哈西得勒。與扎西得勒只差一個字。遇到翠翠,與我相依為命的吃、住、行這三大件都被她改善了。我在吃上是個天生的相思苦命,我一旦相中什么,就會一吃到底,從不思改換。特別是那些青梅竹馬的食物,野葡萄、大煎餅、餃子、面片、疙瘩湯等等更是相思甚苦。目前我想吃餃子沒有條件,因為我剛當上記者,剛從手機市場來到電視臺,收入上正處于青黃不接的時候,我把里外兜翻遍,也湊不出一碗餃子。再說,今年過年我回過家,我把所有的積蓄給了俺娘。我只有交上“錢”這個公糧,俺娘才能安心,有錢作證,她知道我會生活得很好。我是借了一百元錢,交了六十元的房租。余下的四十元,我給自己下命令,不許吃午飯。一個饑餓的我,昏沉沉地掙扎在中午,不管是回憶早晨,還是期待傍晚,都有食物在等著我,我很受用這種安排。在這樣的情況下,翠翠要帶我去認識一種飯菜身兼兩職、且相對實惠的食物——麻辣燙。她七拐八拐把我領到一個小屋子里,她請我。我吃了一口,吐出。我說這是豬食嗎?她說,你再接著吃。我很餓,一碗還是剩下了很多。那確實是豬食的味道,也是豬食的做法。我做過豬食,野生的灰菜、柳蒿、蒲公英等等,還有新磨的玉米面一起下鍋,心情高興時我會加上兩根胡蘿卜。我是豬最好的廚師,同一口大鐵鍋,我給家里人做完飯,直接填上水,再給豬做飯,然后再給狗做飯。牛不用,牛喜歡吃鮮草,滴著水珠的那種——那都是小時候的事了。第二天,翠翠還要帶我去那里,她用耐心循循善誘,希望我變成她的麻友。我這次沒有吐,居然有一點點適應了。第三天,翠翠又帶我去,她改變我像改變沙漠,一定要長出綠洲來。這回我吃著吃著突然有感覺了,舌頭開竅了,結果湯也沒剩。第四天,我主動要求再去。她大笑著說哈西得勒,我說什么來著?只用三天保證讓你上癮!我也笑,豬就是這樣喂肥的。接著,她又帶我到東市場吃皇后。她說芒果是皇后。我被長相另類的皇后吸引了,我瞬間變成朕了。翠翠買了兩個富態的,親手剝了皮遞給我。一口下去,我又馬上吐出來了,這皇后身上,有一股濃烈的松油子味。松油子,在俺的老家,俺用它引火,聞著味道一直不錯,可那只是鼻子的專利,把嘴插上去就不行了,屢戰屢敗。翠翠還不死心,說你再吃一口,再吃一口試試吧。我是說什么也打不開我的嘴了,牙在那緊緊咬著,像護欄一樣圈著舌頭。怕不保險,我的唇也緊緊閉著。看來讓這個皇后下榻我的身體很困難,翠翠最后把兩個皇后全吃了。我說我只喜歡吃那些宮女——李子、沙果、香水梨等等。后來,我果然吃到了!還是南方的宮女,又漂亮又珍貴。翠翠在一個花窖上班,她的專業是園林。一有時間,她就帶我去花棚里拈花惹草。這一行是一舉兩得,一是我可以在這花房草窩里,緬懷一下逝去的童年。二是我可以吃到金橘。偌大個花窖,只有兩棵金橘樹,那是翠翠的領導格外寵愛的。但是,翠翠更寵愛我。她囑咐我不能一下子全吃光,要一個一個地吃。我說領導發現了怎么辦?她說如果發現了,就說金橘樹生病了。我笑得不行了,她的意思是說,金桔樹生病了,孩子夭折了,一個一個往下掉,誰也沒招兒。
房東咣咣敲門。她在敲門這件事情上,一直堅持得很好。房東一進屋,便揮舞著大粗胳膊說“你你”晚上別走,我有事。她說了兩個“你”,而我的屋里有三位房客。我明白了,她是讓那兩個女鬼別走隨時待命。白娘子在吃五香瓜子,紅娘子在看一本言情雜志,研究男人為什么不著調。白娘子吃瓜子非常執著,不管買回多少,只要一開吃,必須見底。從吃瓜子這件事情來看,她比較適合去挖井或者抓虱子。我有很多次看見她,手里拎著瓜子,一邊吃,一邊大搖大擺地行走在夕陽里,身后的瓜子皮像小蛾子一樣飛舞。人約黃昏后,要是不讓她吃完,約會也會溜號。我躺在床上看一本純文學雜志,里面寫到了面包圈,我一看到食物,胃就會條件反射。我無法控制我的胃走出身體,到樓下的小吃鋪里去采購。本來,我的胃是很不待見面包圈的。因為我這中式的嘴巴,一直拒絕西洋景。但是今天,這本雜志改變了我。一個面包圈,書上寫的,一元五角錢一個。書上并沒有對面包圈的味道做出細致的描寫,但這并不妨礙我去想象它的味道。我小的時候,吃得最隆重的一次甜食,就是半根麻花。那是在一個非常炎熱的中午,為了吃麻花,我先吃了四張大煎餅,把胃墊得高高的,讓饑餓夠不著。然后,我才開始吃那半根麻花。從家一直吃到學校,二里地的距離,我精準的計算了吃法——踏進教室的那一刻,手里剛好剩下最后一口。我要讓所有同學參觀我吃那最后一口麻花的樣子,那是一種炫耀,也是一種遮蔽。最后一口,可以讓同學們把它想象成一整根麻花、或者是兩根。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半根。而后,我再也沒有吃過甜食。再后來,我的胃也很有志氣,漸漸與甜食意斷情絕。今天我的胃想在甜食這里再續前緣,它還在樓下的小吃鋪里逡巡。它等著我去買單,我要滿足它。因為我一直欠著胃一份甜食,我還口口聲聲四處宣揚我不愛甜食,那只是一種自尊罷了。
兩個小時后,房東的事初見端倪了。房東要在我的屋里大擺宴席。大魚大肉都來了,蟶子蜆子也來了,五顏六色的蔬菜也來了,煙酒也來了,塑料椅和大圓桌也來了。電飯鍋蹲在窗臺上,像要大便的樣子。這話十分不雅,但房東那口鍋,形象確實很差。我的屋子就那么大,用俺娘的話就是“屁大點的地方”。它們都來了,這屋子顯得擁擠不堪。那我也不走,這是我的床我的家。房東大呼小叫,用舌頭又把綠娘子和灰娘子圈攏到我的屋里。看來確實是出大事了,因為灰娘子都來了。灰娘子梳著一個門簾子一樣的齊劉海,把眉毛活生生埋掉。穿著露著腰溝的卡腰褲,平時一張嘴就是“啊呀媽呀”,是典型的東北小老娘們。她自己經營著一個服裝床子,她平時的造型就是背著一個大麻袋一樣的黑口袋,像作案一樣日夜不需要睡眠。房東一招呼,她就來了,眼睛瞪得溜圓,生怕跑了客源,這是職業的習慣。她從來不提孩子,不提丈夫,她只提褲子!提完了就使勁跺腳,然后再滿樓尋找能裝下她全身的鏡子,左照右照后,突然立定,乍呼呼地說上一句,啊呀媽呀我又瘦了,真鬧心。這種自賣自夸、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的毛病,也是職業病。綠娘子的情況比較特殊,別的女人離婚了,都是無家一身輕。她不是,她還帶個孩子。拖個油瓶子離婚,又住到像貧民窟一樣的女子宿舍里,很難炒出“再婚”這盤菜。她倒是有一口好鍋——她在銀行上班,這在我們女子宿舍就是高收入了。但是,她的長相很不吉利,臉如淺水池塘一樣,里面養著五官,一切都是走下坡路的樣子,成天哀怨著,饑渴著。不像白娘子的豆包臉那樣飽滿,也不像紅娘子的糖餅臉那樣平坦。綠娘子與灰娘子,也是我給起的芳名。綠娘子,我起名的靈感來自床單被罩。綠娘子特別喜歡一種草包一樣的綠格子床單被罩。在女子宿舍,由于每個人的地盤實在有限,換個床單被罩,就像裝修一樣。綠娘子裝修完畢的時候,拖著她那個小油瓶,各屋奔走相告,然后我們紛紛去她的床前瞻仰祝賀并使勁摸索,盡量找出適合的贊辭。晚上,她就與她的孩子,一齊裹在這草包里,過一種離婚落草的日子。
我開始裝睡,眼睛一閉,任耳朵遭罪。太陽快下山了,翠翠還沒有回來。白娘子破天荒脫了衣服,只穿吊帶。當然這些信息都是我聽來的,我離她們太近了,每一種聲音都能盡收耳底,一個屁聲也不曾落下。她們吃飯的聲音,吧唧吧唧的大嘴片子,像挑釁一樣,仿佛在一遍遍地問——餓不餓?饞不饞?想不想吃?開始她們說話,主語是“我”——我家是我先出的軌,怎么啦?誰規定就不許女人先出軌了?這是白娘子的聲音。接下來是綠娘子——我家的冰箱、電視、凡是值錢的,都讓他賣了,我們娘倆是啥雞巴毛都沒有!我就剩那個小雞巴孩了!綠娘子帶頭罵人了,導致她們談話的主語全變了,變成了“他媽的”。他媽的我有時真想一刀殺了他——紅娘子又在摸腳,因為我聽到了她把手伸向桌子底下的聲音。他媽的我都麻木了,我天天上貨睡大通鋪,男人摸我這里,我都沒反應了!累啊——這是灰娘子的聲音。他媽的我真想爬起來把桌子掀了——這是我想說的。接下來演的是戰爭片。啤酒瓶子像手榴彈一樣,乒地一聲接一聲,弄得全屋鬼哭狼嚎。我假裝說夢話,又翻個了身。我不能一聲不出,我怕她們把我忘了,倘若最后全都喝瘋了,把我當男人打成肉餅,那也是白挨揍。我翻的那個身,技術含量很高,因為我做出了電影慢鏡頭的特技效果。我總是做夢,對這樣的表演非常拿手。我弄明白了,這就是傳說中的離婚沙龍。房東忙活了一下午,把淚水汗水全滴上,炒了這一大桌子離婚宴。她還要做總結性的發言——咱們女人不容易,都說女人能頂半邊天,現在咱就頂個破鍋,過這缺牙露齒的日子。那也得好好活,男人那雞巴玩意兒,有的是!一抓一大把!來喝酒……她們總是對準男人的命根子說事,又用香煙點燃與乳房有關的話題。半根煙過后,她們開始談房事,各種版本爭相登場。房事是脫衣舞,墮胎是舞下囚,婦科病是什么?我不想聽了。我不得不起床,我說我去趟廁所。然后我就再也沒有回來……
很晚很晚,翠翠回來了。我從廁所聽見她細碎明朗的腳步向我走來,我的天亮了!我的屋里已是煙霧彌漫,她們全部醉倒了,只有啤酒瓶子沒醉,無奈地直著脖子在桌子上硬挺著——我沮喪地向她敘述這一天一夜的遭遇。我混沌困倦的身心,急需換一個環境。我覺得我中病毒了,整個人死機了癱瘓了,急需翠翠來殺毒。翠翠一邊開窗一邊放煙,哈西得勒,這樣下去可不行!這多影響咱們以后戀愛結婚生孩子,這是多大的陰影!咱們換個房間吧!翠翠比我小,但在決定大事的時候,我比她小。也是因為有她,我才學會去做那個“小”。一直以來我總是裝大,太累了。一個人如果總是硬撐著,早晚得把心弦掙斷。以前,我打針吃藥找她,打雷害怕了也找她,想打牙祭解解饞也是找她。今天打發這群女鬼畫皮還得靠她!她連夜尋找房間,最后南征北調,好歹周旋出兩張床,我和她連夜搬了過去。我們兩個睡對床,我和她終于過上了人的日子。從此,我再也不想離開翠翠這個芳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