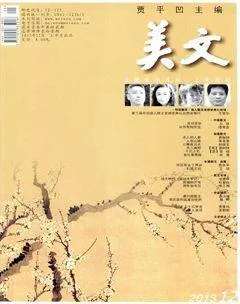殺人的人參

費振鐘
作家、歷史文化學者。1958年出生,江蘇興化人。現供職于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要著作有《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懸壺外談》等。
我祖父在世常說的一句話是,為醫不可以藥試人;我父親在世時常說的一句話是,為醫不用貴重藥。聽祖父說話,還在我十多歲初讀醫書時,聽父親說話,已在我成年終于并沒有做醫師后。這兩句話,都大有深意,只是小時候不夠懂,到能懂時又無意于醫學了。我祖父和我父親,雖然只是聲名不出鄉里的鄉村醫師,卻也自能秉承中國醫學一以貫之的倫理規范,說他們份屬醇醫,也不算標榜。
話說,徐大椿在蘇州吳江做醫師,他的醫學聲譽從江南遠遠傳到北方京城,以至在第二次入京給皇室治病時,年老體弱,鞍馬勞頓,不幸逝世京門。好在大師的著作差不多已經完成,一生的醫學志業到此也可以作個總結了。所以,他為自己做了一副對聯:滿山芳草仙人藥,一徑清風處士墳。作為遺言,隨他的棺櫬返回故土洄溪。
18世紀中期,繼葉天士和薛生白之后,徐大椿是中國江南又一座醫學高峰。當時文壇領袖袁枚,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見證了徐大椿醫學的高深與卓越,在為徐大椿所作的傳記里,袁枚關于這位醫師的評價超過了一般醫學專業范疇,而是從醫學的倫理意義上給予高度認定。按照袁枚的期許,徐大椿的醫學在“存活蒼生”的倫理目標上具有更高的歷史和人道價值。
作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儒醫,徐大椿一生持有“為人生”的醫學理想,這與他放棄入仕、隱于醫道的個人選擇有關,卻也正與中國醫學最寶貴的精神一脈相傳。他原是兼有文學和其他多種才藝的人,但生在文字獄時代,其關注生民的政治愿望,最易切近的轉向是醫學,正是醫學能夠讓他表達一種道義自覺。
考諸徐大椿留存的醫學專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論》《神農本草經百種錄》《醫貫砭》《蘭臺軌范》《傷寒類方》等十多種,但這些醫學教科書,除了他在書前的自敘外,似乎很難直接說明徐大椿追求“活人之術”的醫學境界,因此,重視細節的前皇家太史袁枚,對當日僅看到徐大椿幾則醫案,卻未能完整閱讀這位醫學大家的全部記錄,也深表遺憾。
《洄溪醫案》一卷本,起初只有手抄本,由徐大椿的弟子金復村記錄和保存,直到清咸豐五年(1855年),才正式由王士雄刻版成書,這已在徐大椿去世80多年后了。19世紀后,徐大椿的醫學影響還有多大,沒有這方面的資料確定,但在中國醫學仍然遵循它的最高法則的時代,徐氏的醫學實績仍然為人景仰和高度信任。同為醫師的王士雄《洄溪醫案》出版序言里說:“余讀之如獲鴻寶,雖秘本而方藥不甚詳,然其穿穴膏肓,神施鬼設之伎,足以垂予鑒而活蒼生。”如同當年袁枚期待的那樣,在《洄溪醫案》中,徐大椿通過他的記錄,建立了自己足以傳世的醫學形象。但在我讀來,這個形象恰恰并非依賴徐大椿的高超的個人技術,不是像袁枚所說“奇方異術”,也不是王士雄說的那種“神施鬼設之伎”,而是從一種從疾病的對話關系中體現出來的倫理品格。《洄溪醫案》一百多個案例所記,其所顯示出來的精華光亮之處,不在對那些疑難疾病的診治,而在于對疾病所持的醫學立場以及人生擔當。知道這一點,就理解徐大椿書寫醫案時,為什么并不詳細記錄方藥,他之所重,別有取義。
這就要說到“殺人的人參”了。我讀《洄溪醫案》,印象最深的是首篇以“中風”為主題的六份案例。作者的記錄,似乎一開始便有意設構一組相似的疾病,對這類疾病使用人參藥可能產生的醫學傷害進行討論。借助于這一疾病現象群的讀解,徐大椿集中表達了自己關于人參方的嚴正立場。顯而易見,反對人參作為必服的“補藥”,是他需要申明的重要醫學觀點。根據徐大椿的個人觀察,在使用人參為主藥治療的病人那里,往往導致疾病加重,甚至造成死亡。作為確鑿的事實,他有充分理由,質疑和批判行之已久的“人參方”產生的謬誤。作為一位以“生人”為職責的醫師,他對“執一馭萬”的時醫們,使用人參“殺人無數”的醫學現象,既義形于色、憤激難平,又充滿了醫道不存的歷史悲傷。
在“人參”使用問題,徐大椿的拒絕,與17、18世紀醫學上的“古典派”和“溫補”學派的對立密切相關。古典派承繼和發揚傷寒知識傳統,溫補派則以明代趙獻可為代表,以溫補類方藥對待所有疾病,所謂“執一二溫補之方,通治萬人之病”。古典派與溫補派,可以歸結為身體與疾病關系界定的差異,起初趙獻可等人據南方人體質弱而倡導溫補,但是不久這個學派便使醫學陷入了一種倫理危機。從兩方面簡要地說,首先“溫補派”的治療方法,無論什么樣的疾病,均以人參方治療,這就為“以藥試病”的庸醫們大開方便之門。當時眾多醫師,相信人參對于疾病的身體有絕對的補能作用,夸大的人參方療效,掩蓋了他們醫學能力的貧乏,不加分辯地使用人參方治病,成為醫學上最惡性的“以藥試病”,以至造成病人頻繁的死亡,卻無需負醫學責任;第二,人參為貴重之藥,當時醫師以此藥迎合社會需求,形成了一種特殊醫學消費時尚,至于人參是否能夠正確用于疾病治療,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病人,尤其是富有錢財的病人,肯花重金吃此貴重藥物,于是當日醫學便不以“生人”,而是漁利為目的。這兩方面,都涉及醫學倫理的人道核心,無論醫學技術還是醫學目標,一旦偏離人道,都是對醫學倫理的敗壞。
當徐大椿在他的時代,看到“人參”使用導致醫學倫理如此墮落,他不得不用“人參破家殺生”的驚悚之語,來表達他的不滿和憂憤。完成于1757年的醫學論文集《醫學源流論》里,徐大椿在上卷第三十九篇《人參論》寫道:“天下之害人者,有破其家未必殺其生者,有殺其生未必破其家者。先破其家而后殺其生者,人參也!”與現實的憂憤相比,徐大椿對醫學未來,更持悲觀之見,因為他面對的不僅僅由“溫補”帶來的醫學價值的暫時迷失,而是中國醫學人道傳統的歷史性中斷。作為一個保守主義醫學家,對醫學展示的未來,如他在《醫學源流論》序言里所言,醫學“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為之振興,視為下業,逡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并亡,惄然傷懷,恐自今以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人參”之害,只不過是在眼前呈示了醫學慘痛的景象。
悲觀者往往具有特殊的敏感和歷史預見性,他們憂郁的目光所見,醫學不停地復制著昔日倫理的頹敗。20世紀以后,當現代西方醫學代替了中國醫學,無論西方醫學與中國醫學有多么不同,時間方過百年,你看今天的醫學不是仍然繼續著徐大椿的遭遇嗎?甚至情形比那時更黯淡無望。當我們在某個著名醫院看到這樣的標語:“熱烈祝賀我院住院病人突破某某萬!”你對醫學還會有什么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