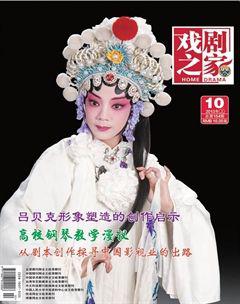戲曲表演中的“意”與“象”
胡小青
我們常常把中國戲曲的表演規定成“虛擬化”、“程式化”,這種認同是對的,但是如果把中國戲曲表演表述得更為準確,那就是“意”和“象”,正所謂“立象盡意”。這也是中國戲曲表演的美學情調。
“立象盡意”強調的是“神似”,即超然于事物的具體表象之外,著重抒發和表達創作主體內在的正直感情與知覺感慨。中國戲曲藝術家們也更多地認為,在簡潔的戲曲舞臺上,心靈應該是自由的馳騁;在戲曲藝苑天地里,藝術應該是超越自然的。它以寫意為主、就連“虛擬化”、“程式化”也都是圍繞著這種美學情調來進行的。所以,戲曲表演講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它表現在處理主客觀關系上,可以遠離現實。為了達到抒情目的,表達理想愿望,表演者可以把超現實的內容呈現在舞臺上,讓故事在虛構與現實中交替進行。在鬼魂伸冤、清官斷案、神仙相助、皇帝調停、因果報應、首尾圓合等表演中體現出這種“意”和“象”。
這種“立象盡意”,表意重主觀的戲曲特點也直接影響到戲曲的結構形式。我們以元雜劇為例,元雜劇四折一楔子,正是這一模式的具體體現。第一折矛盾的發生,第二折矛盾的發展,第三折矛盾的高潮,第四折矛盾結局。楔子的作用,放在開頭是鋪墊,放在劇中是過渡,為的是戲劇情節發展得更充暢。人物為事而存在,其作用主要是通過唱詞表演,把一個故事完整地敘述一遍,而作家也特別注意經營劇本結構的緊湊集中,在引人入勝的故事講述中,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如《竇娥冤》實為喊冤,但并不直接喊,而是通過三樁誓愿,通過再現把作者的主觀情感喊出來,觀眾也從三樁誓愿中發現、明白竇娥的冤情之重。具體來看,為了寫意,戲曲在結構方法上往往從控制情緒的角度來結構故事。
“意”和“象”把戲曲的表演歸結到一種獨特的戲劇表演體系,這表現在:第一,人物的表演完全不必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那樣,以內心體驗為主,而是用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一舉手、一投足,寫意和虛擬結合,亦真亦假,創造出一種情境,一種情調,使人們感到置身其中盡情入理;第二,即使是非表演也能營造出抬腿千萬里、揮手百萬兵的氣勢,使觀眾感受到場面的浩大、壯觀,把觀眾帶到一種意境當中,感到身臨其境;第三,傳情達意,收放有度。戲曲演員即使是哭和笑,都有自己的表現手法,不必是真哭真笑,而使觀眾感到真。另外,服、化、道以及臉譜都是寫意的。
“意”和“象”在刻畫現實和虛幻的人物上,也有獨特的手法,例如《牡丹亭》中杜麗娘的“夢”,最具有代表性,作為大家閨秀的杜麗娘在父母的“關心”、“愛護”之下,身陷閨閣,但作為一個日漸成熟的女性,她渴望得到愛情。面對明媚春光,她禁不住發出“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坦”的感嘆,發出“可惜妾身顏色如花,豈料命如一葉乎”的抱怨,她的愛,她的情,在現實中都不可能實現,只能在夢中實現。作者構思她的夢并沒有滯留在那“畫眉深淺入時無”的兒女纏綿中,而是“將奴抱去牡丹亭畔,芍藥欄邊,共成云雨之歡,兩情初合,真是千般愛惜,萬種溫存”。她和柳夢梅確是在夢中相見,一往情深。杜麗娘的夢離奇荒誕卻合乎情理,虛幻卻又易為人接受,雖然假卻給人以真實感。在現實與虛幻的強烈對比中否定現實,十分傳神地突現了杜麗娘的內心世界,使觀眾為之嘆息。中國戲曲為了表現作者的主觀情感,如此把人物內心的隱秘加以外形化的結構形式俯拾即是。
如果回顧戲曲的產生歷史,這種寫意戲曲在實踐中也是有所依據的。戲曲形成于宋元時期,當時由于說唱藝術的發展,出現了以抒情為主的劇詩,用韻、散交織的詩,用組織完善的音樂結構,創造了“剖析式敘述體”——劇詩的意象模式。這種模式改變過去單純以敘述人的口吻的形式出現。我們可以從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王實甫《西廂記》中選張生出場為例,兩相對比,加以體會。
我們理解和掌握中國戲曲表演的“意”與“象”,對于傳承中國戲曲表演的獨特規律,拓展戲曲表演的新路,展示中國戲曲的獨特魅力,使中國戲曲的美學性情調為更多的觀眾所接受,是大有益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