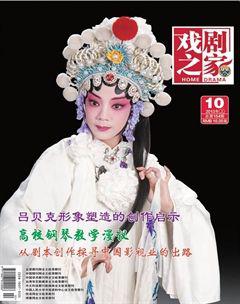不著一字 盡得風流
李舒嫻
我是一名青年錫劇演員。2011年,常州市委宣傳部、市文廣新局和北京好風好雨文化藝術公司聯手,共同打造原創交響錫劇《天涯歌女》。劇組決定由我扮演劇中女主人公周璇。接到任務時我只覺得心里忐忑不安,對自己能不能在舞臺上塑造好周璇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化名人缺乏足夠的底氣。這時,劇組請來本劇的藝術顧問、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劉秀榮老師,親臨排練場進行指導,給了我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正由于劉秀榮老師不辭辛勞的言傳身教和深入淺出的點化引導,使我逐步找到了創造角色的門徑,更得到了一次中國戲曲表演藝術精髓的熏陶。
一招一式當以人物為本
過去,我也參演過錫劇現代戲,在創造角色時遇到的最大的困惑是怎樣把戲曲的傳統程式和塑造現當代人物有機結合起來,往往感到差之一分,成了“話劇+唱”;增之一寸,又缺乏現代審美感。關鍵何在呢?
記得排“天涯放歌”一場,是一段戲中戲,表現周璇在攝影棚里拍電影《馬路天使》時的情景。劇中在拍周璇唱電影插曲《天涯歌女》:“家山北望淚沾襟……”時,導演不滿意地讓她停下,用日寇侵華的國仇家恨啟發周璇。周璇頓悟,有一句臺詞:“導演,再來一遍!”我邊說邊豎起一個戲曲的蘭花指。排到這里,劉老師叫停了,她讓我不要用蘭花指,就豎起一個食指沉著地說:“再來一遍!”我一琢磨:“對呀,劇中人剛聽導演講了東北同胞離鄉背井浪跡天涯的苦難遭遇,又聯想到自己三歲被賣無家可歸的凄涼身世,這時把蘭花指用在悲情中的周璇身上,感覺與人物此時此地的心情不符。”
在排第四場“勞燕分飛”時,表現被繁華鬧市謠諑紛起所困、和丈夫嚴華出現感情裂痕的周璇,到故鄉常州尋親。在一段載歌載舞的借景抒情后,驀然與遠道而來尋找周璇的嚴華邂逅。我先用了一個戲曲里的“起范兒”,接著撲向嚴華,頭微微顫動。這是戲曲里表現親人久別重逢的常用套路。劉老師讓我不要按現成套路走,要按特定情境中的人物內心走,不要“起范兒”,不要搖頭。當周璇突遇嚴華,先有一停頓,接著徑直撲向嚴華,兩眼凝視著丈夫,像一尊雕塑,一字一句地說臺詞:“你聽說了嗎?你相信嗎?”這樣的表演看似含蓄,但與前面的載歌載舞形成強烈對比,更使人物此刻復雜的心理充滿了張力。
第五場“港地思鄉”,周璇有一大段唱《聽舊歌不由我心潮激蕩》,開始我一邊站著唱,一邊還不停“之”字型走動,覺得唯有這樣才能體現人物“心潮激蕩”。劉老師給我分析說:“此時在香港的周璇已到而立之年了,不是剛進明月歌舞社的小姑娘,也不是紅極一時的青春偶像,這時的周璇心思重重,個人感情又不順,像盛開的花一樣萎頓下來。這段戲應該表現周璇成熟、沉穩的一面,要讓她靜下來,坐著唱,靜下來的戲最感人。”劉老師為我設計了坐著的三個動作,一是坐著的周璇一只手托著腮;二是把托著腮的手慢慢搭在另一只手的胳膊處;三是再把這只手移過來扶著梳妝臺,另一只手垂放在膝蓋上。三個動作把而立之年的周璇和前面幾場戲的年齡差距拉開了,更把周璇孤立無助、心力交瘁的神態逼真地表現出來,得到觀眾的同情和憐憫。劉老師舉重若輕,一下子抓住戲眼,創造了一個感人的戲劇情境。
我在排練過程中逐步領悟到,劉秀榮老師作為京劇表演藝術大家,諳熟京劇表演的各路傳統程式,但她絕不囿于程式,不拘泥于現成的表演套路,而是通過不斷創新賦予程式以新的生命,新的境界。這種創新的源泉來自于塑造人物性格、表現人物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其實,戲曲藝術傳統的表演程式都是在創造各種各樣藝術形象中形成的,又是為創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服務的,如果程式離開了塑造戲劇人物,離開了創造特定的戲劇情境,充其量只是技術,不是藝術。
一言一行彰顯高尚藝德
如果說我在《天涯歌女》中的表演得到了有關專家的認可和觀眾的喜愛,或者說通過《天涯歌女》使我在錫劇表演方面有所進步,我都打心眼里感謝劉秀榮老師。劉老師不僅在表演藝術上悉心對我進行指導,更以她無比敬業的品格和無私提攜新人的藝德時時感動著我、激勵著我。劉老師在常州指導期間,正值江南“秋老虎”肆虐,她不知多流了多少汗水;她的腿上有舊傷,走樓梯十分不方便,團里的排練場在頂樓,又沒有電梯,她硬是咬著牙,一回回拾級登樓;每天排練結束,我們都累得巴不得早早休息,可是劉老師每晚都要備課到深夜,最晚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劉老師為了輔導《天涯歌女》,在北京家中還和她愛人、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張春孝先生一起,反復推敲,并一塊兒演示;《天涯歌女》在北京保利劇院演出,正值寒流來襲,劉秀榮老師偕張春孝老師雙雙冒著嚴寒前來劇場觀看,第二天一早就給劇組打來電話,把他倆連夜交換的對《天涯歌女》的加工提高建議告訴我們,大家都十分感動……。這一切都傾注了老一輩藝術家對民族戲曲的執著和熱愛,對弘揚民族文化的期望和囑托。我不僅從劉老師那里學到許多戲曲表演技巧,更學到她作為一位戲曲表演藝術大家的高尚藝德。我暗暗立志,一定要牢記劉老師的教誨,謙虛謹慎,刻苦用功,為祖國戲曲事業貢獻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