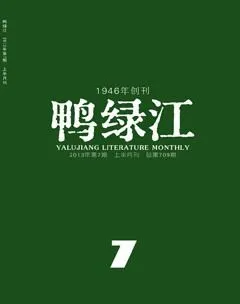走在靈魂的刀鋒之上
張艷梅,1971年生,文學博士,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學科帶頭人,山東省作協(xié)特約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已在《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理論與批評》等期刊發(fā)表論文一百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項,山東省社科基金重點課題兩項。出版《海派市民小說與現(xiàn)代倫理敘事》《生態(tài)批評》《文化倫理視閾下的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研究》等著作多部。
鬼金是一個獨特的寫作者,說獨特,并不是因為他吊車司機的身份,而是因為他呈現(xiàn)給我們的文學形態(tài)。他以文字的方式反復和世界較量。我常常想,一個人能夠每時每刻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靈魂的存在,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就像我曾在寫給一個女作家的信中說:我們內(nèi)心有一條筆直的道路,無法隨意拐彎,所以靈魂難免會一次次撞向?qū)γ娴膲Ρ凇Wx鬼金的小說,有尖銳的疼痛以及無法釋懷的悲傷。我知道,不是小說中人物命運的悲劇走向,也不是現(xiàn)實人生的巨大局限,是來自寫作者鬼金內(nèi)心的掙扎,一次再次地打動了我。多少人的生活岑寂如死灰,心靈凋落如枯木,無論繁華,還是困頓,都在實存的層面掩埋了自己。鬼金不肯,他靈魂的火焰和塵世的冰山長久地對峙,既考驗他自己的信念,也拷問每一個讀到他文字的人。
實際上鬼金小說近兩年才逐漸進入大眾視野,作品不多,大都有著鮮明的個人烙印。鬼金試圖用不同于他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去建構一個斬釘截鐵而又泥沙俱下的世界。小說中,他反復寫到草泥湖,不太像一個具體的地理空間,更近乎一個象征性的存在。他喜歡寫魚,很大的魚;還有鳥,很小的鳥。吊車、小鹿、大象、石頭、冰山和暴風雨……這些寓言化的做法,不斷強化著他和世界之間的關聯(lián),也不斷加深了他與世界之間的裂隙。一切都可以是虛構,穿越虛構又在不斷迫近某種真實。他一再地寫到父親的死亡和女友的出走與失蹤。這種懸置的生活,與禁閉的靈魂相互對視,是一種不肯妥協(xié)、不肯認輸?shù)淖藨B(tài),也是一種無家可歸、無處皈依的茫然。
面對他的小說世界,我常常想,那涉渡之舟究竟在哪里?
一、生命詩學——禁閉與突圍:我們都是時代的孤兒
翻檢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大致的代際差異:50年代出生的作家執(zhí)著于社會和歷史,60年代出生的作家執(zhí)著于個人和他人,70年代出生的作家執(zhí)著于自我的物質(zhì)與精神,80年代出生的作家則不再有恒定的文化立場和精神軌跡。洪治剛在《代際視野中的“70后”作家論》中指出,70后作家“更多地膺服于創(chuàng)作主體的自我感受與藝術知覺,不可以追其作品內(nèi)部的意義建構,也不崇尚縱橫捭闔式的宏大敘事,只是對各種邊緣性的平凡生活保持著異常敏捷的藝術感知力”。【1】作為“70后”寫作者中的一個,鬼金的文學世界里既有“70后”那個群體的共性,也有屬于他自己的文學個性。鬼金小說有著或多或少的自敘傳色彩,當然不是成長經(jīng)歷那種,而是深藏的精神烙印。總體上看,他的文學傳承是西方的,是現(xiàn)代主義的,孤獨的氣質(zhì)里有著先鋒的印記。朱河,一個穿越理想與現(xiàn)實,穿越精神與物質(zhì),穿越生存與死亡的小人物,一個對生活有疑問的主人公,他有著打破舊世界的渴望,又有著破壞一切的暴力傾向,甚至對親人也會產(chǎn)生殘殺的念頭。灰茫中的暴力,絕望中的反抗,這就是草泥湖的噩夢人生。鬼金在努力探索并呈現(xiàn)人生的迷霧和陰影,現(xiàn)實本身就是無邊的圍困,多少人無路可走,多少人最終選擇從高處墜落?與生活的緊張,與時代的對抗,是無法和解的內(nèi)在靈魂的沖突。鬼金一再寫到女主人公的出走和失蹤,顯然絕非偶然,那么,是情感的緩釋心靈的救贖,還是絕望之后的放棄與逃避?
精神與文化的廢墟
“我的心已為惡夢纏繞,我要仰面朝天躺下,讓黑暗充做我的睡房。”——波德萊爾《一日終了》這句詩的引用,讓我們看到了鬼金筆下那些帶有普泛性的被禁閉的心靈,黑暗是沉睡的外衣,噩夢本身就是一種困境,精神的、靈魂的困境。《追隨天梯的旅程》中,朱河在書店門上看到一張白紙,上面寫著:精神已死,書屋關閉。朱河平時常常來這家書店買書,喜歡那些現(xiàn)代派的詩歌和現(xiàn)代派小說。在一個凄冷的凌晨,朱河看到書屋主人刀手的留言:精神已死,書屋關閉。這是時代的最大預言。不僅小鎮(zhèn)是一個精神荒蕪的世界,書籍對小鎮(zhèn)上的人來說簡直就是廢紙,對于我們的時代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這是一個精神荒蕪的時代,文化信仰和精神追求早已坍塌成一地廢墟。
從存在主義和象征主義視角來看,《卡爾里海的女人》是一篇有意味的小說。小說中那個重病的女子,就像卡爾里海的女神,雖然生命將逝,卻平靜安詳,滿懷悲憫地注視著親人以及陌生人對她的敵視和禁閉。而那個懵懂的少年,在異鄉(xiāng)曠遠的海邊,對這個美麗的女子產(chǎn)生了朦朧的情感,生命最初的萌動是青澀無果的情懷。最終少年回到城市,成長,結婚,老去,女子不知所終。直至生死臨界,昔年重來,飄飄魂魄終于再續(xù)前緣。讀《卡爾里海的女人》,容易讓人想起村上春樹的《海邊的卡夫卡》,田村卡夫卡獨特的成長經(jīng)歷使他在深深的孤獨中學會尋找精神世界里的一個虛幻人物對話,其實就是在和自己的內(nèi)心對話。鬼金筆下的少年也是一個不確定的人物,雖然作者沒有展開他個人的成長,只是把海邊那段獨特的經(jīng)歷作為籠罩他一生的一束光和一道傷痕,但是這光與愛卻讓我們洞悉了他人生的全部真相。小說中孩子們關于生死的對話不乏恐懼,而成年人對那個女子的厭棄和暴力,形成了少年與塵世的第一次斷裂。他渴望一種精神庇護,大海和女子以精神同構的方式成為他的感情寄托。這種來自女性和大自然的永恒之愛,無疑是一種象征,鬼金以此反觀塵世的冷漠和荒蕪,在主人公自省的同時,飽含著對人生的批判。
暴力和絕望的追問
“帝國燒烤” 是一個物欲場。瘋狂的喊叫里充滿了暴力血腥,鴿子、人、模擬的槍聲、閃爍的刀光、飄落的羽毛、強權的肆意凌辱、弱者的抽刀反抗,朱河面對的世界就是這樣,仿佛整個世界就是一個你死我活的狩獵場。他閱讀,寫作,夢想的空間很龐大,也因此更加痛苦,“現(xiàn)實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枷鎖,讓他不得不屈服于這個枷鎖。也許,一個理想主義者是注定要痛苦的。”這個人物在鬼金小說中最具有代表性,軋鋼廠的現(xiàn)實生存和個人的精神生活如此割裂,如此對立,而小說的主人公們就在這兩個世界穿行、游走、折磨。最終整個人像一只大鳥從二十幾米的高空墜落下來。他的肉體還活著,靈魂卻好像出門旅游去了。小妖最終狠心揪掉了那些管子。窗外,那更高的天空真的有一架梯子可以超越塵世的一切折磨嗎?“追隨天梯的旅程”是以死亡為起點的,其實是靈魂的出走再也沒有回歸的路途。這個小說很決絕很徹底,沒有留下任何幻想。
比照餐館和軋鋼廠此類公共空間,窗子后面的私人生活則更像是精神圍城。《神秘鳥》這個小說同樣帶有魔幻色彩。一只小鳥落在窗臺上、骨灰盒上、朱河頭上、屋頂上,是一個女人的化身,也是主人公靈魂的化身。鬼金喜歡寫鳥,筆墨背后呼之欲出的是飛翔與突圍的渴望。失蹤的肖蘭蘭是根本未曾出場的女主人公,小說里,這個隱藏的人物如一只鳥落在了老齊母親的骨灰盒上,落在了朱河的頭頂。小說開頭就寫朱河一個人坐在窗臺上看見那只鳥,覺得那只鳥好像發(fā)出了一個人的聲音,在呼喊他。他在窗臺上站起來,模仿著飛翔的姿勢……小說結尾寫對面樓的孩子手舉著彈弓把一個彈子射過來,正好打在那只鳥的頭上。砰的一聲悶響,只見血花飛濺。那個頭已經(jīng)模糊不堪。孩子打鳥只是一個游戲,而朱河因為絕望,惡念叢生很想殺了那個孩子。滿篇都是絕望漫漶的情緒,就像為了一頭小鹿,死了四個人,小說《草泥湖殺人事件》為我們呈現(xiàn)了什么?人性善惡在冰冷的死亡面前,如何評價?小鳥小鹿都是象征物,美好生活和純潔性靈,對照無比殘忍的暴力和死亡,帶給我們不絕如縷的追問。
鬼金小說多半以內(nèi)在的精神探尋超越了生活的表象,模糊了真實和夢境的界限。讀到《時代的孤兒》中“我一個人坐在我爸朱河墳墓的旁邊,天黑了,夜深了,我覺得肚子嘰哩咕嚕地叫起來”,那個孩子內(nèi)心的絕望瞬間湮沒了我,而小說的復調(diào)敘事和對罪與罰的討論,也都讓我思之良久。鬼金對生命存在的感覺和思考,超出了很多同時代的人。在《我們?nèi)タ创笙蟀伞分校卫蚶蛞辉僖笕游飯@看大象。這個愿望簡直成了人生的一個儀式和全部意義所在。段莉莉因為包養(yǎng)她的男人欠了她三萬塊錢,有了謀殺動機,一個處在犯罪邊緣的女孩,如何自我救贖?去看大象是對現(xiàn)實生活的輕微抗拒,也隱含著一種追:到底要怎樣面對生活。其實朱河原本喜歡那種微小的動物,比如鳥、螞蟻、魚什么的。微小得可以像一個人靈魂的動物。后來他開始喜歡大象,大象是世界的另一種構型吧。大象和冰山一樣,在鬼金小說中,都屬于巨大的象征之物。鬼金引用了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他躺倒在燒焦的征衣上,周圍是黑色的歲月,悠悠無窮。或許對主人公而言,人生并沒有那么黑,也沒有那么絕望,只不過是因為想看到大象的愿望最終落空,就像等待的戈多永遠也不會真的到來一樣。最終段莉莉離開了失蹤了。在黑暗的旋渦里,朱河感覺到那個形體仍舊存在。最后的短信和結尾接近黑色幽默了,荒誕,不確定,有各種可能性。不是解脫,也不是答案。小說中兩個人反復提到那本小說《獨自上升》,應該是解開這篇小說主旨的密碼。
超越與拯救的可能
人生是孤獨的,而孤獨往往是彼此靈魂溝通的重要介質(zhì)。面對艱險的圍困,孤獨的隔絕,《卡爾里海的女人》中的少年向那女子伸出了愛的雙手。雖然那段感情并沒有變成現(xiàn)實的溫暖,卻引導少年完成了生命最初的裂變,也賦予女子活下去的勇氣和信心。對少年來說,生活剛剛展開,溫情和殘酷,疾病和美麗,禁錮和自由,糾結在一起,是白紙一樣的人生突然面對這一切的拷問,在心靈的田野探索和理解情感的意義。在茫茫的大海面前,每個敏感的心靈都會產(chǎn)生內(nèi)在的孤獨感。生活的波濤把兩個人沖到世界的邊緣,在那個被封閉的小房子前,他們成為拯救彼此的精神方舟。卡爾里海是什么?是能給孤獨者以慰藉的心靈棲居地,還是人類靈魂中最后一片純潔的水域?女人在冰冷的墻壁上所畫的飛魚無疑象征著自由。對生命的追問,對情感的的渴求,對自由的向往,都在女人筆下飛翔。作者寫出了人類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病態(tài),以及對圣潔情感和自由精神的渴求:“一切自由都是柵欄圍起來的不自由下的產(chǎn)物。”這或許是這篇小說帶給我們的超越情感自身的思考吧。
在《目光之遠》中,超越還是以想象的飛翔抵達的:“它們以慢的形式推進著,就像刀子,在某一個虛構的想象中,在推進,推進,直到劃開皮膚,呈現(xiàn)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紅色,破裂的血管,凸現(xiàn)著。這些要感謝慢,感謝速度,更多浸入內(nèi)心感受。感受和過程是重要的。慢是重要的。在慢的基礎上,我們才可能飛。是可能。目光愈拉愈遠。”“目光像兩道彩虹,連接著他與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讓他幻想著飛行,然后是抵達,成為外面世界的一分子。”《目光之遠》中患嚴重小兒麻痹的朱河本身也是一種寓言化的表達。他的病態(tài)心理,他的生活渴求,他對妹妹的復雜情感,他的飛翔,他的回歸,都隱喻了人類的某種存在狀態(tài)。被關在輪椅上的這個孩子,只能用目光行走。他的世界就是目光之遠。他的目光常常喜歡把他帶到那塊石頭那邊,還有就是草泥湖那邊。目光所及的世界,就是他能走到的世界。被禁閉在輪椅上的朱河不相信上帝。沒有任何信仰,在這個世界上,究竟什么力量能讓一個殘缺的身體恢復健全,能讓一個殘缺的心靈重回愛中? 孩子們的斗毆中,那個瓶子突然調(diào)轉(zhuǎn)了方向,飛回到那個扔空瓶子的孩子的臉上,“啪”一聲,就像撞到了巖石上,尖銳的碎玻璃鑲嵌在他的臉上。這個細節(jié)非常有力量,甚至稱得上震撼,朱河的超能力當然是一種幻覺,然而在想象中,他憑借意識的延展,實現(xiàn)了內(nèi)心對世界的報復。
二、生命倫理——喜悅與悲傷:誰經(jīng)歷過天真年代
什么樣的作家是好作家?什么樣的小說是好小說?是同悲同喜還是能慈能悲?是悲憫眾生還是決不寬恕?面對冷漠而強大的現(xiàn)實,混亂而迷惘的情感,錯位而斷裂的欲求,生存的荒誕感,心靈的分裂感,鬼金始終在試圖建構屬于自己的秘密的情感通道,連結內(nèi)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把生存實景和生命倫理合二為一,嘗試著尋找一種純真的生命感覺,所以他寫下了屬于他個人的《天真年代》和《天真之歌》。他的小說大都從庸常的世俗生活出發(fā),以情緒的起伏和意識的流動推演情節(jié),然后敘事突兀一個轉(zhuǎn)身,千里平疇就斷裂成萬仞絕壁。鬼金擅長講述個人經(jīng)歷的生命故事,通過個人化的生命敘事,隱現(xiàn)鋒利的生命感覺,這種生命感覺在敘事中呈示為獨特的個人命運。劉小楓說,倫理學家堅持“每個人都是一個深淵,當人們往下看的時候,會覺得頭暈目眩”(畢希納);“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細審視,都有屬于自己的秘密與夢想”(基斯洛夫斯基)。敘事倫理學在個別人的生命破碎中呢喃,與個人生命的悖論深淵廝守在一起。【2】對于鬼金來說,他的確不是從個人世界推及整個世界,尋找普遍答案,而是執(zhí)著于一個人的生活際遇。想搞清楚一個人的生命感覺曾經(jīng)怎樣和可能怎樣。那些喜悅和悲傷,愛和恨,暗和光,由何而來,又有何意義。而這,正是鬼金寫作的獨特價值吧。
疼痛與孤絕的境遇
鬼金的小說大都具有先鋒色彩和孤獨氣質(zhì),在講故事的同時滿懷憂傷地揭穿生命本質(zhì)。他所寫的悲劇不是外在生存的不幸,而是作為一個人的整體的、本質(zhì)上的、永恒的、無法擺脫和超越的悲劇意味。也許鬼金本來就是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對一座冰山的幻想》充滿了神秘、魔幻和焦慮感。小說寫一個叫鬼金的男人路上撿了個女孩叫小寂,同住一室許多天,女孩最終被人帶走,鬼金空留對冰山的無限懷想。顯然,主人公是個孤獨而缺乏行動力的人,耽于幻想常常意味著某種自閉,打開了心靈的窗子,卻關上了通往現(xiàn)實的某一扇門。主人公身上的時代幻想癥和生命虛無感,均屬都市精神漫游者的譜系。冰山,火焰,一個隱喻,一個象征,小寂曾經(jīng)說過:“抱著我,緊緊地抱著我,你的懷里是我最溫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對于我來說都是冰山。就這樣抱著我,讓我像冰塊一樣融化……”也許當小寂一層層揭開腿上的紗布,鬼金也為我們一層一層揭開了生活的面紗,無比疼痛,還帶著時代的血色和精神的撕裂感。
鬼金筆下的感情世界是殘缺的,他不肯給我們一絲慰藉,甚至一句謊話也沒有。他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基本上都處于孤獨狀態(tài),而且是絕對的孤獨。血淋淋的生存掙扎里,有外在的疼痛,更豐富的是內(nèi)心的磨礪。《天真之歌》中,陳佑項和小蓓相愛,莫名其妙地小蓓走了,陳佑項回憶著和小蓓生活的一年里的每一個細節(jié)。那些微小的細節(jié),讓他溫暖而又受傷。兩個人是在一次廠團委舉辦的聯(lián)誼會上認識的。在于小偉葬禮上重逢,開始了一年多的同居生活,然后小蓓悄悄地無聲無息地離開。主人公自稱身體里住著黑暗的神。他是軋鋼廠的囚徒,而黑暗的神是他身體的囚徒。就像一顆不死的種子,時刻準備著在他個人的身體里復活。一場胃病,一段感情,一份回憶,在作者筆下波瀾壯闊,浩大無邊,是愛,更是痛苦和絕望。那么,流離失所的人,何處才能安放自己的靈魂?小蓓是陳佑項等待的戈多嗎?對于陳佑項來說,他等待的戈多會來嗎?明天會更美好嗎?陳佑項說自己是那個走鋼索的人,小蓓就像那根鋼索,“沒有你,我會從空中墜落”。“我睜開眼睛。不,即使在睡眠中,我的眼睛也是張開的。我不明白這是為什么。無論白天黑夜,它都顯示黑暗。黑暗里涌起喧囂。沒有光汩汩流出,沒有。在生活的門縫里,我陷入難以拯救的低潮。我在我的絕處,在窄窄的門縫里,我看著我愛的人們給生活注以完全不同的涵義。”鬼金寫出了一個人的精神彷徨和內(nèi)心掙扎,寫出了靈魂深處的孤獨與疼痛,黑暗的生命境遇,永恒的精神求索,正如魯迅沉郁冷峻的自我解剖一樣。
我們都是有病的人
鬼金對發(fā)掘人的精神病態(tài)有種奇怪的迷戀,但又不是特別頹廢。他的小說沒有青春的亮色,沒有情愛的繾綣,有的只是生活的噩夢和夢的破碎,在生命的深淵里眺望自己。反抗也有,卻不會落實到很具體的行動上,倒是那種令人困擾而又迷惑的精神意緒里,不期然地就照見了一代人生命的暗影和舊夢。對于那個理想主義年代,70后群體大多經(jīng)歷了青春的狂熱癥,而對于90年代這個讓理想主義者無所適從的年代,這一代人更像有病的人。人生的失意和苦痛,憂傷和躁動,那些曾經(jīng)色彩繽紛的生命記憶日漸凋零頹廢,陰影和夢想,都充滿了孤獨哀苦的調(diào)子,鬼金以非現(xiàn)實的手法對內(nèi)心情緒世界的準確把握和精彩呈現(xiàn),帶給讀者意外的震動。意識流的運用很嫻熟,無邊的黑色世界,恐怖的生活幻象,暗示出人的內(nèi)在生命的秘密。神秘的暗示,奇妙的感應,把瞬間的情緒化作沉重的隱喻,以病態(tài)的個體表征病態(tài)的社會人生。開闊的現(xiàn)實時空,幽深的精神隧道,靈魂的寂寞和痛苦,纏繞在一起,找不到通往彼岸世界的橋梁。沒有外力的救贖,內(nèi)在世界不斷淪陷,鬼金嚴肅而真誠地告誡:我們,都是有病的人。
有些時候,大約就是一個細節(jié),打動了鬼金,他就會把這種稍縱即逝的情緒變成一篇小說,呈現(xiàn)一些細節(jié)的力量往往比整個故事走向更有意義。《春愁》這篇小說的主題還是精神性存在的追問。“如果這個世界上我還有一個靈魂的居所的話——那就是文字。”對現(xiàn)實生活的無力感,對技術專制時代的依賴感,對主觀世界的厭倦感,對心靈世界的絕望感,其實都是一種病態(tài)的折射。小說中一個寫了一半的小說,因為電腦文檔壞了,打不開,內(nèi)心非常焦慮。修電腦的過程始終伴隨著這種焦灼感。公共汽車上的女子,脖子上的老虎墜子,講述的冰山故事,都隱含著一種奇異的生命意味。究竟是幻覺,還是真相?如何才能找到拯救自我的藥方?鬼金其實沒有給我們?nèi)魏翁摶玫臉酚^。那個女人從丟失的那個小說文檔中,讀出來一句話:你是一個春天的病人。還有《目光之遠》里的朱河,因為疾病,看世界的角度和眼光都發(fā)生了變化,疾病讓他深陷黑暗,而鬼金更深的意寓恐怕在于,夜晚就像是一頭龐大的野獸,我們都是黑暗的一部分。《天真年代》中神秘的水底世界是個靈魂的救濟所,一朵花的前世今生是健康生命的象征。楊懷講述的故事和朱河講述的故事,不斷重疊和分裂。古麗遭受的暴力侵犯很平常,朱河拯救的念頭也非出于生命自覺,最終古麗失蹤,朱河跳湖,只是把絕望的生命感向前又推進了一步。小說結尾還是幻境:“又一聲開天辟地般的驚雷響過之后。湖面上出現(xiàn)了一個巨大的水花。瞬間,只是一個瞬間,在楊懷眨眼睛的瞬間。古麗水滴般地蒸發(fā)了。朱河也不見了。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雨滴像堅硬的彈子,把整個湖面砸得千瘡百孔。雨一直下,下到天黑。軋鋼廠家屬樓的燈光慢慢地亮起來了,射過來的一部分光,能看見草泥湖上黝亮而細碎的波紋。”千瘡百孔的時代,回響著千瘡百孔的情感,在生命倫理敘事中,鬼金超越了現(xiàn)實生活的全部界限,為我們打開了那個隱秘的世界。《卡爾里海的女人》中的那個女人是個真正的病人,鬼金卻把她看成是健全完整的世界的象征,而周圍冷漠的人們才是深陷病態(tài)的世界。少年并不是一個絕對主義者,只能說在穿越生存迷霧中,他曾經(jīng)在斷崖之下找到了心靈的貝殼,而女子把那貝殼戴在頭頂,也就意味著這是二人共同的心靈信仰。村里人的戒備、冷漠和敵視,反襯出兩個外來者內(nèi)心的力量。最終少年還是回到城市生活中,過著正常人的日子,平靜的一生中隨處可見那個解不開的心結和無限追憶的往事。面對有病的人世,在各自的生活中,這兩個人依舊是孤獨者。
三、生命哲學——生存還是死亡:除非靈魂拍手作歌
生死追問是屬于全人類的,作家無疑首先要有人類視野,要真正站在人的立場上寫作,千花競放萬水奔流,最終落下來也還是人。鬼金在小說中反復寫到死亡,有的是從死亡開始寫起,有些是寫到死亡戛然而止。出走和死亡,究竟意味著什么?世界是有限的,歷史可能是循環(huán)的,生死從來都是一個人的兩種存在狀態(tài)。肉體的死亡或許剛好意味著靈魂的自由。從身體中解放出來,靈魂可以拍手作歌。鬼金對于不存在的那個世界有著狂熱而執(zhí)迷的熱情。完全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幾乎不會去背負不屬于自己生命里的那些負擔,即使是屬于自己的,也不愿意面對。鬼金讓他筆下的人物一半活在尖利冷硬的現(xiàn)實之境,一半飛翔在虛空的想象世界。所以生存和死亡的界限就模糊了,總覺得是鬼金心懷柔軟一種有意為之的成全。
死亡與新生
《除非靈魂拍手作歌》從朱河的夢寫起:無數(shù)的鳥在天空上飛。天空看上去有些昏暗,太陽隱藏在云朵之中,像一只幽深的獨眼。一個男孩看著天空中的那只獨眼,手做手槍的形狀,對著獨眼,“啪”地開了一槍。瞬間,紅色的血液彌漫著,淋漓著,在天空中,像垂下來的布匹,連接著天和地。這個意象帶有明顯的暴力傾向,或者說人物內(nèi)心的隱含的暴力以夢境的方式呈現(xiàn),比起寫實更具有震撼力。夢中的暴力,對太陽的反抗,都是活著的態(tài)度,以及死亡的巨大覆蓋力量。父親因為要討個說話而犯病,最終死亡。其實看起來這死亡沒有多大意義。鬼金以父親和小鳥的相伴,以自我替代性地為父親完成一次性愛,作為生命的隱喻,小說中,鬼金引用了葉芝的《駛向拜占庭》中的詩句:“一個衰退的老人只是個廢物,是件破外衣支在一根木棍上,除非靈魂拍手作歌,為了它的,皮囊的每個裂綻唱得更響亮。”鳥和父親同時死亡,意味著過去的世界和虛幻的理想同時消失,留下來的只能是回歸,回到實存的層面,直面生命的悲苦與歡欣,所以小說結尾懷孕的女友提出結婚要求,朱河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還有一篇《垂直日光》也是個告別死亡、奔向新生的故事,這種故事在鬼金那里實在不多。李志在書店里和女友的日常生活,更像一幅素描,線條清晰,色彩淺淡。這樣一種平淡而且平靜的生活,被禿頂男人和弟弟李丙毀掉了。弟弟殺了人,李志是幫兇,弟弟判了死刑,李志入獄。出獄后,李志滿懷懺悔回到了藍城,費盡周折偷出了弟弟的尸體。掩埋弟弟一段令人感動,這在鬼金筆下也不多見,鬼金不是一個愿意在文字中表達情感的人。他內(nèi)心對塵世的愛恨都融入到他筆下的死生契闊了。這個小說結尾寫道:“李志邊培著土邊說李丙你終于入土為安了,你這回在土里要好好地活著,好好地做人。遠處山里面的一聲炮響,驚醒了他。李志揉了揉眼睛,看著那個土包說,李丙你一個人就在這山上好好地待著吧,哥如果有時間的話會來看你的。李志不想再回到藍城了,他掏出那個司機給他的名片,看了看上面的地址,向那個方向跑去。”這幾乎算得上新生了。鬼金小說對于死亡的超越不多,沉湎的卻不少。當然沉湎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哲學立場。
死亡然后永遠沉寂
草泥湖在鬼金筆下日日夜夜上演著生死劇。《草泥湖殺人事件》是個比較極端的小說。木匠劉木勝救一頭小鹿,與飯店老板李廣德的兒子爭執(zhí),孩子掉進冰洞死了。女兒湘繡為贖罪被迫跟了李廣德,最后也跳湖死了。劉木勝一怒砍死了李廣德:他的斧子沒砍在木頭上,而是鑲嵌在李廣德頭上的時候,他聽見斧頭和骨骼碰撞的聲音。他看見血從斧頭的鑲嵌處流淌出來,像一根顫動的紅色橡皮筋。他心里熊熊燃燒的火焰,在斧頭鑲嵌進李廣德頭部的時候就熄滅了。那咣的一聲過后,他憤怒的門一下子就關上了。斧刃的鋒芒瞬間蹦出來,白得刺眼,而且發(fā)出嘩然的聲音,巨大的白光猶如冬天的湖面……死亡最終讓一切平靜,這篇小說顯文本是現(xiàn)實關懷,隱文本是生命反思。一頭小鹿,四條人命,如何衡量善的價值和意義?
《她們在電話的另一邊》也是從死亡寫起的。南芬打電話給朱河的時候,他正在殯儀館。朱河正被一片哭聲和悲傷流動的氣氛籠罩著。悲傷浮動,猶如死者頭上燃燒的香燭的煙氣。那煙氣猶如死者的靈魂,繚繞著,慢慢地飄走。小說中有幾個細節(jié)。一個是電話,母親說父親釣到了一條二十多斤的大鯉魚。一個是朱河和沈陽的虛擬對話。一個是朱河和童小乙靈前的虛擬性愛。這幾個細節(jié)都頗耐人尋味。在《神秘鳥》《一條魚的葬禮》中,鬼金也寫了一條很大的鯉魚。總覺得大魚是天地間某種生命密碼的象征。最終,朱河沒有跟著去火葬場。他看著車隊緩慢地開走,看見童小乙爬上靈車,那雙棕色的小牛皮鞋一閃,他心里隱隱地覺得童小乙現(xiàn)在屬于那個死者。在他離開殯儀館的路上的時候,突然接到童小乙的短信,當他企圖打開短信的時候,手機沒電了,一片黑屏。朱河的心顫了一下,他想:“童小乙的短信說什么呢?”小說是個開放式的結尾,沒有給出任何答案。沒有任何色彩和聲響,人生就此一片黑屏。
靈魂在生死之外
什么是靈魂,靈魂敘事有什么意義和價值,這個問題似乎不少人問過。鬼金喜歡寫夢境,似乎在夢里一切皆有可能,在夢里可以超越一切阻隔、界限和對立,獲得內(nèi)在的緩釋和自由。夢是回到永逝的時間之流的一種手段,也是超越時空超越生死的一種狀態(tài),鬼金會自覺地在小說里反復探討靈魂是什么。“父親是一個有靈魂的人嗎?自己是一個有靈魂的人?”他在《除非靈魂拍手作歌》中寫到了一個夢:朱河看見一座森林,所有的樹木都在熊熊的火焰中舞蹈,彌漫著一股樹脂的清香。在火焰之上的天幕,突然裂開一道縫隙,一架軟梯晃晃悠悠從上面垂掛下來。軟梯的背景是飄飄揚揚的雪花落下。軟梯還在向下垂掛著……軟梯慢慢上升。天幕合上了。一切萬籟俱寂。這時候,從天幕里,伸出兩個巨大的橋臂,那是他在軋鋼廠開的吊車。只見父親兩手抓著吊鉤,從深淵般的黑暗中被吊起來。這個夢境顯然寫的是天國,天梯是靈魂抵達天國的通途,是生命的延伸和另外一種存在形式。
那么靈魂是如何存在的?鬼金為什么執(zhí)著地追問這個在唯物主義者那里根本不存在的問題?《她們在電話的另一邊》開篇,鬼金再次正面談到他對靈魂的理解。“也許靈魂的離去也需要時間,需要一個過程。面對死,靈魂無處逃遁。必須離去。肉體因為疾病,或者別的某一種原因,它面對來勢兇猛的死亡,迅疾地,被拒絕在肉體之外。在死亡面前,肉體成為物,即將腐爛,竟已散發(fā)出腐爛的氣息。”“在那一刻,死者的靈魂是能看見的。如果死者的靈魂是喜歡熱鬧的,也許它會浮動在人群之中,甚至會躲到某一個人牌的后面看,然后再看看別人的牌,它也許會表現(xiàn)出焦灼,為某一個人打出一張臭牌惋惜;也許會焦灼地伸出它的手指,推倒一張它已經(jīng)看出來胡了的牌……如果是一個喜歡安靜的靈魂,也許它已經(jīng)走出窗外,追趕著天空上的云朵,向更寧靜的地方飄去,比如:云的城堡。肉體衰亡,大勢已去。沒有靈魂的肉體即將成為灰燼,成為物,被這個世界遺忘。”這一段話寫出了鬼金對于生死的深刻感悟,這種感悟超越了實存層面的關懷,而且以靈魂關懷的方式,抵達了生命哲學的高度。
四、生命美學——先鋒敘事:生活就是對一座冰山的幻想嗎
小說的創(chuàng)作手法已經(jīng)有太多人窮盡,包括結構、人物、語言等等,敘事學的研究已經(jīng)在諸多方面跨越了學科的界限。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不同作家那里得到一些嶄新的印象。閱讀探究鬼金的小說,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的先鋒意識不在于情節(jié)的虛構與想象,也不在于人物命運的云譎波詭,是一種貫穿其中的精神之流,讓讀者不能從容地沉湎于故事情節(jié)。在這里,我們不探討文學以外的表達,有時候,我覺得鬼金的虛構是一種冒險,他可以模糊虛構和真實的界限,以一種仿真的敘述延伸世界的觸角。是心靈的釋放,還是對世界禁閉的反抗?生存的詩性表達非常艱難,每向前一步都面臨絕壁,荊棘叢生,鮮血橫流,他內(nèi)心也有畏懼吧?或者遲疑?所以那些花鳥魚蟲就成了他靈魂的另一種存在形態(tài),他專注地凝視著它們,就像看著黑暗中的自己,飛走了,吃掉了,或者殘忍地死去,讓人覺得壓抑。是的,讀鬼金的小說,讓人心里很難受,世界起了一萬種震動,還是心中生出一萬個難題?
對世界充滿了隱蔽的排斥感
鬼金小說呈現(xiàn)的生存狀態(tài)無疑是底層的,盡管沒有人把他的小說看成是底層寫作。對底層生活的態(tài)度,其實是一代人對時代的態(tài)度。鬼金對生活的質(zhì)疑本身就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這一烙印既是個人的,也是整體的;既是對外在生活的質(zhì)疑,更是對人的存在的本質(zhì)的質(zhì)疑。這種70后作家的寫作,有一種雙重“遺忘”的傾向。首先,他是現(xiàn)實中存在的那種無力也無法參與全球化進程,無力也無法分享市場的利益的看不見的階層。這些階層的存在提出了與年輕的70后作家潮流完全不同的問題。在70后作家尋找個人與全球化直接聯(lián)結的點的時候,這些階層所凸顯的卻是有關社群的團結和社會的公正性的問題。其次,他們的文本中沒有中國的“革命”的存在,革命的歷史似乎從來沒有“在場”,革命對于70年代人來說,已經(jīng)沒有組織起記憶的可能和必要。【3】市場和革命的喧囂,都不屬于70后作家,所以,他們更專注于自己的內(nèi)心,在生命和靈魂層面不斷掘進,呈現(xiàn)出獨特而偏執(zhí)的美學自覺。從這一意義上看,鬼金因為自身處境,比起大都市里生活優(yōu)裕的寫作者有著更直接的抵達。
鬼金小說的主人公大多游走在生活的邊緣或者世界的外部,很少真正進入到生活和世界的內(nèi)心,這種游離感和模糊性,強化了某種力量和世界的緊張,隨時可能斷裂。他也沒有去著意于刻畫人物,那些主人公幾乎就是一個人,只是投身不同的生活時空,世界如此壯觀又如此猥瑣,心靈如此豐饒又如此荒涼,鬼金以自己的方式抵達了某種真實。是不是也有救贖呢?總體感覺是絕望的,如同一把鋒利的刀子,一面刺穿生存的假象,一面刺痛自己的靈魂,和世界相連的那根細線,似乎隨時都會斷掉。對待自己塑造的人物,鬼金的美學態(tài)度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生活在底層的小人物,面對生活的壓力和絕望不斷抗爭,精神超拔,而現(xiàn)實沉重灰暗,那僅有的亮光如何照亮整個世界?他用靈魂的鐘聲叩響時代的大門,有點陰森的涼意彌漫,以幽靈的姿態(tài)凝視自己的生活,一地死灰的燃燒,細若游絲的纏繞,靈魂彷徨于模糊的光亮處,憑借個人的審美直覺,鬼金呈現(xiàn)了屬于他個人的生命感覺和態(tài)度。小說中的生存很沉重,靈魂很輕逸,凝滯和飄忽成為他小說最重要的交錯纏雜的美學風格。
鬼金小說充滿了敘事的張力和迷霧
鬼金喜歡虛構,夢境和幻覺交織纏繞在一起,在藝術鍛造上,探索自己的審美趣味和品格。富有詩意的語言,飽含著內(nèi)在的緊張。《卡爾里海的女人》中少年的一生壓縮折疊,只有在海邊那一個時間點凝滯,不斷放大,一段朦朧情感隨之漫漶,傷感而迷茫的氣息之中,有著抵達靈魂的至死不渝的力量。細節(jié)的處理很謹慎,少年去撿海螺殼那段稱得上山呼海嘯驚心動魄;也有大片的色彩渲染,隨意中蘊藏著劇烈的人物心理動蕩。卡爾里海的女人從海螺殼里聽到了大海的聲音,那是人生的內(nèi)在力量,以及生的悲劇性和愛的永恒向往。少年不是反抗世界的強者,他只是在尋找靈魂的路上,遇到了那個渴望救贖的女子。“在審美上對于變化的偏嗜,是70后作家大都迷戀奇觀化的敘事,極盡所能地渲染光怪陸離的都市新貌,慣于在極端化情境中呈現(xiàn)人性的激烈沖突,表面的煽情和內(nèi)在的冷漠的融合暴露了創(chuàng)作主體的分裂狀態(tài)。”【4】對于鬼金來說,某種意義上的分裂也是存在的。一種不算圓熟的敘事,但是有著獨特的味道和明確的自覺,詭秘的氣氛,壓抑的冷色調(diào),荒謬錯位的命運感,玄想和冥思,探討存在的困境,迫近生命存在的真實,是一種終極問題的追溯。其實70后作家普遍鐘情于個人日常生活敘事,細膩幽微,精致圓潤,如滕肖瀾、朱文穎、盛可以等女作家,也有徐則臣、張楚、弋舟等作家在日常生活之外有更深邃的精神追問,而鬼金是不多的對敘事藝術有著執(zhí)著的探索熱情的年輕作家。現(xiàn)實世界、心理世界和想象世界的三位一體,形構了復雜而又奇特的異度空間。我常常想,鬼金是否也和其他70后作家一樣試圖重建一種日常敘事美學,一種生命詩學,一種尷尬的歷史縫隙里的細碎呼吸呢?還是說他超越了?因為自身的禁閉,而獲得了精神的超越?鬼金正在形成個人化的敘事風格,冷峻而凌厲。他發(fā)現(xiàn)存在的溝壑,然后跳過;他建構奇異的世界,然后拆解。他沉迷于這種敘事上的往復和旋轉(zhuǎn),起伏于生活和精神的渦流,在半空中俯視人生。
總之,在眾多年輕寫作者中,鬼金是一位非常有個性的作家。他深邃的生命感受力和文字表現(xiàn)力,往往可以洞穿生活的表象,寫出那些被壓抑和禁閉的生存境遇,并且憑借語言和思考的魔力,獲得心靈和思想的自由。正如很多人說起的那樣,他身處的環(huán)境,他的職業(yè),本身就帶有嚴肅的象征意味。懸置、封閉、沉重,沒有絲毫詩意,然而文學給了他突圍的方向和可能,他在文字的詩意世界里尋找、思考、自救和救贖。文學于他,是光,是溫暖,是信仰,更是一次漫長的靈魂苦旅,他以自己的方式愛著這個世界的美好和柔軟,恨著這個世界的冷漠和殘忍。“囚徒困境”,給了他現(xiàn)實的壓力,也賦予他想象的翅膀。穿越黑暗,孤獨和靈魂生死與共。當然,對他來說,如何克服意識的封閉、凌空的生活感覺、過于偏執(zhí)的技巧追求,更從容地表達,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洪治剛.重構日常生活的詩學空間——代際視野中的“70后”作家論.把脈70后.何銳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2
【2】劉小楓.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
【3】張頤武.迷亂閱讀:對“70后”作家的再思考.把脈70后.何銳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65
【4】黃發(fā)有.70后與媒體風尚.把脈70后.何銳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79
責任編輯 陳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