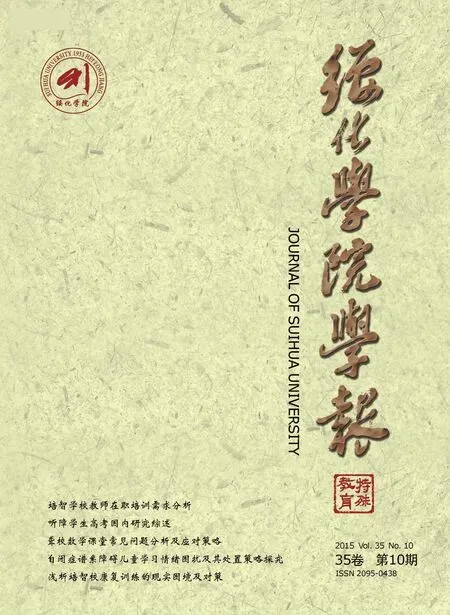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早期發(fā)展探究
賈振峰 呂 梅 劉靜 徐冬梅
(綏化學(xué)院外國(guó)語學(xué)院 黑龍江綏化 152061)
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早期發(fā)展探究
賈振峰 呂 梅 劉靜 徐冬梅
(綏化學(xué)院外國(guó)語學(xué)院 黑龍江綏化 152061)
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以美國(guó)手語為工具形象地反映客觀現(xiàn)實(shí)的藝術(shù)作品創(chuàng)作,形式多樣。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的整個(gè)早期階段作品主要包括了聾人用書面英語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作品,從英語翻譯成手語的戲劇作品以及世代相傳的手語民間傳說、故事等。但由于受到聾人教育曲折發(fā)展的影響,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環(huán)境在早期發(fā)生了曲折變化。以1880年意大利米蘭會(huì)議為標(biāo)志,大致分為1817年到1880年美國(guó)聾人教育的手語教學(xué)期,以及1880年到1957年美國(guó)聾人教育的口語教學(xué)期兩個(gè)階段。
美國(guó)手語;手語作品;早期發(fā)展
高爾基說:“語言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第一要素。”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學(xué)創(chuàng)作[1]。所有語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學(xué),文學(xué)使得人們的思想和體驗(yàn)得以傳遞。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是指以美國(guó)手語為工具形象地反映客觀現(xiàn)實(shí)的藝術(shù)作品創(chuàng)作,形式多樣,包括手語詩、手語歌和手語故事等。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也包含了從其他形式翻譯成手語的作品,但更多是指美國(guó)手語原創(chuàng)的藝術(shù)作品。而美國(guó)聾人作品創(chuàng)作是指與美國(guó)聾人相關(guān)的、以任何語言形式為工具形象地反映客觀現(xiàn)實(shí)的藝術(shù)作品創(chuàng)作。而聾人作品創(chuàng)作不僅包含了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而且也涵蓋了與聾人相關(guān)的非手語創(chuàng)作。
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的整個(gè)早期階段作品主要包括了聾人用書面英語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作品,從英語翻譯成手語的戲劇作品以及世代相傳的手語民間傳說、故事等。但由于受到聾人教育曲折發(fā)展的影響,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所以以1880年意大利米蘭會(huì)議為標(biāo)志,大致分為1817年到1880年美國(guó)聾人教育的手語教學(xué)期,以及1880年到1957年美國(guó)聾人教育的口語教學(xué)期兩個(gè)階段。
一、手語教學(xué)期的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發(fā)展
手語教學(xué)期的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處于自然發(fā)展?fàn)顟B(tài),同聾人教育一樣都處于起步階段,聾人學(xué)校大量涌現(xiàn),聾人獲得了更多的教育機(jī)會(huì),雙語能力不斷提升。除了世代相傳的民間手語傳說、故事,他們也進(jìn)行大量英語書面語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在手語教學(xué)時(shí)期,使用“手語溝通教學(xué)法”的聾人學(xué)校得到了蓬勃發(fā)展。康涅狄格聾啞人教習(xí)所(即哈特福德學(xué)校)的教師,以及從這里畢業(yè)的大量學(xué)生分別去往了全美不同地方,傳播手語教學(xué),使得美國(guó)手語得到了廣泛傳播。同時(shí)繼哈特福德學(xué)校后,大量的聾人學(xué)校相繼在紐約州、肯塔基州、弗吉尼亞州、印第安納州、賓夕法尼亞、俄亥俄以及魁北克成立[2]。許多聾人開始從事教師和管理人員工作。這些學(xué)生精通美國(guó)手語和英語,真正具備了跨聾人和“聽人”社會(huì)的雙語溝通能力。此外,1864年哈特福德學(xué)校創(chuàng)立者托馬斯·霍普金斯·加勞德特的兒子愛德華·加勞德特在華盛頓特區(qū)成立國(guó)立聾啞學(xué)院,后來改稱為加勞德特學(xué)院(也就是現(xiàn)在的加勞德特大學(xué))。加勞德特大學(xué)是目前世界唯一一所聾人文科院校,也是美國(guó)聯(lián)邦政府資助的院校之一。聾人學(xué)校的建立極大的促進(jìn)了美國(guó)手語在整個(gè)美國(guó)范圍內(nèi)的迅速發(fā)展,與此同時(shí)美國(guó)手語中非純粹功利性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開始產(chǎn)生。
早期美國(guó)手語的母語者之間流傳著豐富的民間傳說和歷史,他們利用了手語特有的構(gòu)型和運(yùn)動(dòng)特征創(chuàng)作和傳播了大量的詩歌、軼事和故事[3]。但是這些十九世紀(jì)的民間傳說無法形成文本記錄,因此這些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只是為聾人社團(tuán)和少數(shù)懂手語的“聽人”所欣賞,無法在“聽人”社會(huì)廣泛傳播。伴隨聾人教育的蓬勃發(fā)展,聾人對(duì)自身雙語自信的提升,以及他們與“聽人”社會(huì)溝通的加強(qiáng),聾人逐漸開始使用書面英語進(jìn)行詩歌和散文創(chuàng)作,借此向更廣泛的受眾表達(dá)自己的想法。例如,十九世紀(jì)中葉,國(guó)立聾啞學(xué)院的學(xué)生已經(jīng)開始學(xué)習(xí)、創(chuàng)作書面詩歌。加勞德特當(dāng)時(shí)就指出這些學(xué)生中一大部分人會(huì)成為著名的詩人[4]。他們這些聾人作家都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例如,1827年,詹姆斯·納克成為第一個(gè)在美國(guó)出版詩集的聾人[5]。他相繼出版了四本詩集。1835年約翰·伯內(nèi)特出版了一本半自傳式的聾人故事書,名為《聾啞人傳奇及其他》。1855年,約翰·雅克布斯·弗盧努瓦出版了《法院大樓里的公牛:?jiǎn)讨蝸喼萁芸诉d縣雅克布斯的一個(gè)恐怖故事》[6]。
詩歌創(chuàng)作成為這一時(shí)期聾人創(chuàng)作最活躍的形式。杰克·甘農(nóng)在他的《美國(guó)聾人社團(tuán)歷史》中說,“對(duì)于一些人來說可能看起來很奇怪,大部分聾人作家的作品都是詩歌”[5]。1884年愛德華·加勞德特寫了一篇題為“聾人詩歌”的文章,發(fā)表在《哈潑斯》雜志,后來在《美國(guó)聾人史冊(cè)》中再次出版。加勞德特總共在文章中介紹了19名來自不同國(guó)家的聾啞詩人,向人們展示了全世界范圍內(nèi)聾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成就,解釋聾人在聽力缺失的情況下是如何感受詩歌格律的,希望“聽人”社會(huì)更多的人能認(rèn)識(shí)和了解這些聾人文學(xué)作家[4]。加勞德特在文章中并沒有對(duì)這些作品進(jìn)行文學(xué)批評(píng),只是展示了一個(gè)“獨(dú)特群體的人”所創(chuàng)作的各種各樣的詩歌,盡管這些詩歌并不為文學(xué)世界所關(guān)注。例如,文章中重點(diǎn)記述了出生于1813年的杰出作家約翰·卡林,宣稱卡林是當(dāng)時(shí)世界上唯一一名先天聾啞詩人。卡林在賓夕法尼亞學(xué)院接受了四年的聾啞人教育,同時(shí)對(duì)詩歌創(chuàng)作有著深入的研究,30多年一直堅(jiān)持詩歌創(chuàng)作和出版,還曾在國(guó)立聾啞學(xué)院創(chuàng)建開幕式上發(fā)表演講,被授予了該學(xué)院第一個(gè)榮譽(yù)碩士學(xué)位[4]。卡林的詩“致螢火蟲”是當(dāng)時(shí)流行的華麗感傷詩歌代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兩本致力于聾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雜志:一本是1871年在華盛頓特區(qū)出版的《寂靜世界》,它是第一本聾人文學(xué)雜志[5]。第二本《雨滴》主要刊登面向聾兒的原創(chuàng)故事和改編的著名寓言、童話等。這本雜志歷時(shí)一年就破產(chǎn)了,但雜志中刊登的故事結(jié)集出版成故事書后,大受人們的歡迎[5]。
二、口語教學(xué)期的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發(fā)展
口語教學(xué)期以米蘭會(huì)議為標(biāo)志,會(huì)議否定了已取得的手語教學(xué)成就,口語教學(xué)法成為聾校的唯一教學(xué)方式,手語被人為限制,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發(fā)展環(huán)境惡化。這一階段的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作品內(nèi)容和創(chuàng)作目的都與反映手語受到桎梏有關(guān)。
隨著聾人教育在全球范圍內(nèi)關(guān)于“手語溝通教學(xué)法”和“口語溝通教學(xué)法”之間孰優(yōu)孰劣的沖突愈演愈烈,手語逐漸被限制使用,給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發(fā)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以來,愛德華·加勞德特在美國(guó)倡導(dǎo)手語教學(xué),認(rèn)為只有手語教育才能讓聾人具備雙語能力,也只有這樣聾人才能具備生產(chǎn)能力,為社會(huì)做出貢獻(xiàn)。美國(guó)手語教學(xué)多年來取得的成功有力地支持了他的這一看法。相反,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則極力主張口語教學(xué)。他指出聾人需要融入整個(gè)大社會(huì)環(huán)境,就必須學(xué)習(xí)口語和唇讀,手語只會(huì)使聾人與社會(huì)大環(huán)境漸行漸遠(yuǎn)。1880年,在意大利米蘭舉行的國(guó)際聾人教師會(huì)議上否定了法國(guó)和美國(guó)手語教學(xué)取得的成就,確立了口語教學(xué)法的地位,聾人教育的發(fā)展方向才徹底改變。這個(gè)會(huì)議標(biāo)志著美國(guó)聾人教育口語教學(xué)期的開始。口語教學(xué)法地位的提升導(dǎo)致了全美聾人學(xué)校的巨變,大批聾啞人教師和管理者被解雇,聾生們只能在“聽人”老師們?nèi)諒?fù)一日的口語教育中學(xué)習(xí)說話,手語被排除在課堂之外,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
但這些困難并沒有完全阻礙美國(guó)手語在聾兒和成年聾人中間的使用,手語依然非常受他們的歡迎,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和表演也沒有停止。例如,霍華德·霍夫斯特是當(dāng)時(shí)一個(gè)非常有名的說書人和教師,他的父母都是聾啞人,從小就教他學(xué)習(xí)手語[5]。阿爾伯特·巴林是一名畫家、作家和演員,他在1930年出版了一本影響巨大的書《聾啞人的怒吼》,這本書揭示了那個(gè)手語被排斥的時(shí)期,聾人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和痛苦[6]。1938至1940年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出版社出版的雜志《聾人文摘》,刊登眾多聾人的詩作、藝術(shù)作品以及個(gè)人自傳等。此外,全美聾人協(xié)會(huì)擔(dān)心隨著口語教學(xué)在聾人學(xué)校的不斷推廣,手語不久將會(huì)消亡。為了保存手語,他們?cè)?913年至1920年進(jìn)行了一個(gè)錄像攝制工作,連續(xù)七年拍攝了各種聾人不同的手語錄像,其中包括喬治·沃迪茨1913年所做的美國(guó)手語演講《保存手語》,約翰·霍奇基斯回憶他自己在哈特福德的經(jīng)歷的演講《老哈特福德的記憶》[7]。這些錄像也成為保存下來的有關(guān)二十世紀(jì)早期美國(guó)手語的唯一影像資料。
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從萌芽,經(jīng)歷了手語教學(xué)期和口語教學(xué)期的曲折發(fā)展。美國(guó)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在手語教學(xué)期間自然發(fā)展,同當(dāng)時(shí)的聾教育一樣剛剛起步,聾人各項(xiàng)事業(yè)都在萌芽階段,大量涌現(xiàn),這一時(shí)期的創(chuàng)作以手手相傳和英語書面創(chuàng)作為主。后來,米蘭會(huì)議召開,手語教學(xué)被否認(rèn),口語教學(xué)盛極一時(shí)。雖然這一時(shí)期手語作品創(chuàng)作受到了極大限制,然而這些阻礙并沒能夠隔斷人們對(duì)手語的熱愛,手語創(chuàng)作依然沒有停息過。總之,手語創(chuàng)作作為手語語言的一種藝術(shù)反應(yīng),符合語言發(fā)展規(guī)律和聾人社會(huì)發(fā)展需求,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
[1]王力.語言與文學(xué)[J].暨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81(1):3-8.
[2]Baker,Charlotte,andCarolPadden.AmericanSignLanguage:A Look at its History,Structure,and Community[M].Silver Springs,MD:T.J.Publishers,1978:3.
[3]Lane,Harlan.WhentheMindHears:AHistoryoftheDeaf [M].NewYork:RandomHouse,1984:247.
[4]Gallaudet,E.M.ThePoetryoftheDeaf[J].AmericanAnnals oftheDeaf,1884(29):201-210.
[5]Gannon,Jack.Deaf Heritage:A Narrative History of Deaf America[M].SilverSprings,MD:NationalAssociation of the Deaf,1981:67-254.
[6]Batson,andEugeneBergman,eds.AngelsandOutcasts:An AnthologyofDeafCharactersinLiterature[M].3rded.Washington,DC:GallaudetUP,1987:229-387.
[7]Frishberg,Nancy.SignersofTales:TheCasefortheLiterary Status of an Unwritten Language[J].Sign Language Studies,1988(59):149-170.
[責(zé)任編輯 劉金榮]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SL Works
Jia Zhenfeng Lv Mei Liu Jing Xu Dongmei
(Suihua University,Suihua,Hei Longjiang 152061)
Th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works creation,as a tool for the American Sign Language,reflects the objective reality,which is the artistic creation,and has a variety of forms.American sign language works of the early stage work includes the use of literature creation of written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sign language drama and passing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of sign language folk legends and stories etc..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deaf education,American Sign Language work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occurred inflection.In 1880 in Milan,Italy,the meeting,as a symbol,divided two periods:from 1817 to 1880 is regarded as American deaf education of sign language teaching period,and from 1880 to 1957 is regarded as American deaf education of spoken English teaching period.
ASL;sign language literature;early development
G760
A
2095-0438(2015)10-0031-03
2015-05-01
賈振峰(1982-),男,天津武清人,綏化學(xué)院外國(guó)語學(xué)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語言與文化。
2014年黑龍江省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規(guī)劃年度項(xiàng)目“中美聾人手語詩歌的語言學(xué)研究”(14E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