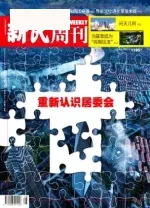扎爾達里:穆沙拉夫第二?
周戎

平靜多日的巴基斯坦政壇再度出現了跌宕起伏。上周,巴最高法院宣布廢除穆沙拉夫于2007年10月5日公布的《全國和解令》(大赦令),剛剛當選不到16個月的總統扎爾達里面臨空前的執政危機。輿論普遍認為,巴最高法院幾乎要將其從總統寶座上掀翻了。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全國和解令》危及扎爾達里的政治生命
2007年10月5日,時任總統穆沙拉夫在美國的壓力下,與時任人民黨主席的貝·布托達成了秘密協議,根據協議,穆沙拉夫宣布了《全國和解令》,宣布8000多名涉及各種司法案件的政治家免于刑事起訴。如此一來,這些人就可堂而皇之地參加總統和國會選舉。在這些受益者中,現任總統扎爾達里和他父親名列其中,另外,現任國防部長、內政部長等一大批高官也在名單中,扎爾達里就是憑著這個大赦令,在貝·布托遇害后,順利贏得了選民對貝·布托之死的同情選票,當選為總統的。
而當時穆沙拉夫總統的《全國和解令》,并未得到最高法院的贊同,因為時任首席大法官的伊夫提卡爾·喬杜里已被穆沙拉夫免職,因此,《全國和解令》在一定意義上講,始終缺乏法律效力。
扎爾達里當選總統后,始終不愿恢復喬杜里大法官的職務,這倒不是因為扎爾達里同情穆沙拉夫,而是因為扎爾達里本人與喬杜里大法官之間也有解不開的結。
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扎爾達里曾因涉嫌貪污受賄鋃鐺入獄,喬杜里大法官被扎爾達里認為是“落井下石”之人。扎爾達里十分擔心喬杜里一旦復職會馬上推翻《全國和解令》,要知道,沒有《全國和解令》,也就沒有扎爾達里當選總統這一幕。于是,扎爾達里采用拖延戰術,遲遲不給喬杜里復職。
到了2009年3月,喬杜里大法官的支持者得到了反對黨領導人巴穆斯林聯盟(謝里夫派)的支持,而謝里夫與喬杜里一起發動了向首都進軍的“長征”,將近15萬首席大法官的支持者從巴各大城市浩浩蕩蕩地向首都開進,眼看局勢難以控制,扎爾達里也有些亂了陣腳,在其顧問勸說下,立即宣布讓喬杜里復職,這才化解了總統與首席大法官之間的激烈沖突。
復職后的喬杜里躊躇滿志,開始積極推動最高法院推翻《全國和解令》。鑒于巴基斯坦三權分立的體制,扎爾達里總統也曾幻想通過國民議會和參議院的立法機構,試圖使《全國和解令》合法,但遭到國會多數議員拒絕。
隨著9月份的到來,距離《全國和解令》失效的最后期限越來越近,而扎爾達里已無可奈何,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曾被起訴的貪污賄賂案件有可能被重新審理,自己在瑞士銀行的6000萬美元的存款也有可能被迫“吐出來”。
不僅如此,司法界正在爭論,扎爾達里是否真正擁有總統豁免權。一種意見認為,扎爾達里是現任總統,理應享受司法豁免權;而另一種意見認為,扎爾達里的當選是因為剛剛被廢棄的《全國和解令》的“寬恕”,既然《全國和解令》都作廢了,那么根據此令進行的總統大選也應不合法,因此,總統不應擁有司法豁免權。
“倒扎”內幕
其實,雖然表面上扎爾達里遭到最高法院“彈劾”,但實際上是扎本人得罪了巴基斯坦最大的權勢集團——軍隊。另外,扎爾達里的民眾支持率也過低。在他就任總統后,有四件事遭到普遍質疑。
首先是首席大法官喬杜里被延遲復職,巴民眾認為首席大法官是巴廉政的象征,許多民眾甚至把巴未來前途寄托在喬杜里身上,所以此事激起了巴民眾尤其是司法律師界的強烈反感。
其次是《全國和解令》,扎爾達里一心希望《全國和解令》成為合法法令,因此開始寄希望于議會通過,未果后,又希望首席大法官“開恩”,再次碰壁。而巴內閣的多數高官都涉嫌貪污腐敗甚至政治謀殺案件,一旦《全國和解令》成為非法,那么這些人也將重新面對司法起訴,而民眾認為扎爾達里的百般阻撓實際上是在包庇腐敗,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再次,扎爾達里同意美國提出的克里-魯格援助巴基斯坦法案,而這項法案的多數條款,被認為是嚴重干涉巴內政,遭到軍隊的強烈反對和民眾的極大憤怒。
最后是巴基斯坦的反恐軍事行動。扎爾達里與軍隊之間出現了嚴重分歧,扎基本上秉承美國“旨意”,而巴軍隊的反恐則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時間表進行的,在軍隊全力反恐并作出重大犧牲的時候,扎爾達里基本上是在國外訪問和逗留,每年他的出訪時間已占全年的四分之一。
這四件事的確損害了扎爾達里的威信,引發了巴輿論界和陸軍的嚴重不滿。另外,扎爾達里始終沒有兌現自己的政治承諾。他有一句名言:“政治承諾不是《可蘭經》,不必完全遵守。”一年多來,巴經濟沒有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國內食品、燃料價格飛漲,停電頻繁,甚至出現了食糖和面粉等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而恐怖襲擊尤其是自殺性恐怖襲擊,已對巴社會政治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民眾不滿情緒的加深也刺激了軍隊和司法界,使得扎爾達里總統的政治威信驟降,《全國和解令》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廢止的。
扎爾達里寶座不保?
盡管扎爾達里面臨巨大的政權危機,但尚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巴報紙做了這樣的分析:“人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內訌頻仍,但卻有一個較好的傳統,就是當其他政敵開始‘侵權時,他們可以迅速捐棄前嫌,團結一致。”
在《全國和解令》公布后,反對派立即開始“逼宮”,謝里夫的發言人明確無誤地“勸退”扎爾達里,稱“為了人民黨的利益,也為了扎爾達里個人的政治聲譽,總統還是引咎辭職,體面下臺吧”。
而巴內政部和移民局的某些人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不準許現任《全國和解令》受益者黑名單上榜上有名的國防部長穆赫塔爾出境訪華。追隨扎爾達里的巴總理基拉尼立即反擊,宣布解除對穆赫塔爾無理的移民局和內政部官員的職務。
另外,人民黨議員不斷發表談話說,“如果要扎爾達里辭職,那么謝里夫兄弟也應辭職,因為他們所涉及的腐敗案件更大,而他們也是《全國和解令》的間接受益者,沒有《全國和解令》,謝里夫還在沙特阿拉伯流放哪”,等等。
唇亡齒寒。謝里夫大概認識到,扎爾達里一旦倒臺,最高法院的下一個目標就一定是自己,因此決定還是不要把事情做得過分,穆盟領袖納瓦茲·謝里夫的弟弟、旁遮普省首席部長沙巴斯·謝里夫已于20日與基拉尼總理達成協議,保證“兩黨之間絕不相互攻訐。”而實際上,如果沒有謝里夫的推動,倒扎運動很難成功。
此外,盡管最高法院有起訴巴基斯坦內閣成員的權力,但此次《全國和解令》的受益者背景錯綜復雜,不僅涉及人民黨,而且牽扯到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兩個最主要大省的上千名政治家,波及面過大,司法程序也會相應延長。因此,真要追究扎爾達里總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軍隊方面,目前巴基斯坦陸軍也不具備發動政變的條件。美國堅持主張,任何巴基斯坦的政權變動都必須經過合乎憲法和司法的程序,而巴陸軍因為美國軍事援助的掣肘,其倒扎行動不得不經常“看美國眼色”。而只要沒有軍事政變的壓力,扎爾達里依舊在政治上有回旋余地。
美國雖然對扎爾達里的“愛護”不及對穆沙拉夫,但美國也不愿輕易改變巴基斯坦現狀,因為白宮不希望因為巴政局動蕩而削弱該國的反恐軍事行動。對于扎爾達里,美國是能拉盡量拉,避免巴政局出現重大動蕩。
作為扎爾達里總統本人,也開始注重自己的形象。他首先取悅軍隊,然后采取了團結全黨、以退為進的戰術,先是交出“核按鈕”和任命內閣成員的權力,旋即準備交出任命軍隊首腦、解散議會和罷免總理的權力,這樣就部分滿足了軍隊要求扎爾達里讓權的目標。再次,扎爾達里正推進鞏固人民黨內部的團結,決心通過黨的力量與最高法院對抗。而今后數月,扎爾達里能否“衛冕”成功,將成為巴政壇的最大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