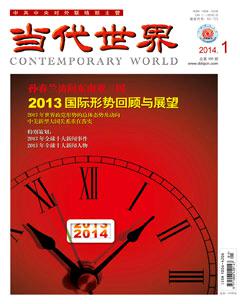2013年世界政黨形勢的總體態勢及動向
魏偉

2013年,世界政黨形勢總體穩定,但穩中有變,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復雜性較前突出。全球近60個國家舉行總統或議會選舉,選情基本平穩,政權過渡有序。西方國家政治生態持續嬗變,傳統政黨壓力上升。轉型國家政治重建曲折反復,在“變”與“亂”中艱難前行。新興市場國家各種矛盾積聚釋放,發展治理困境突出。多數發展中國家政局趨穩,個別國家遭遇民主陣痛。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政權穩固,進一步完善自身建設、推進國家發展。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未消、各國經濟低迷不振的形勢下,各國執政黨狠抓經濟民生問題,改革創新意識增強。
世界政黨形勢的突出動向
一、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難解,政黨政治格局加速演變
美國極化政治進一步發展,嚴重阻礙經濟、社會議程推進。總統奧巴馬利用美經濟數據向好、復蘇勢頭顯現之機,積極推動以經濟、教育、住房、稅制改革及落實醫保為五大支柱的長期發展戰略,努力為第二任期和民主黨留下政治遺產,但共和黨出于中期選舉考慮和政治理念差異,加大對民主黨政府的牽制。兩黨惡斗不僅使奧巴馬的控槍法案被否、綜合移民政策改革受挫、醫保法案實施遇阻,而且導致政府非主要部門停擺。這反映出美極化政治加劇,國內保守勢力上升,社會分裂及政府失能的現實。
歐洲右翼政黨繼續占優,左翼力量小幅上升,政黨政治“碎片化”現象突出。受歐債危機持續影響,歐洲民眾反當局情緒加劇,牽動政黨政治格局。在意大利、德國大選中,民意進一步分散,使大黨不強、小黨不弱的態勢更加明顯,兩國一度陷入組閣僵局。意中左和中右聯盟分獲眾、參兩院多數,無一獲得單獨組閣資格;德聯盟黨保持優勢,自民黨被淘汰出局,社民黨實力繼續走弱,無法組建傳統的“黑黃”或“紅綠”政府。兩國朝野經長時間激烈博弈,最終均組建大聯合政府。然而,意識形態存在明顯差異、又是主要競爭對手的黨派為執政需要而勉強“湊合”在一起,必將影響政府的執政效能和政局穩定。法國社會黨、希臘新民主黨等國執政黨因經濟、社會改革路徑難以取得社會共識而面臨巨大壓力。英國保守黨地方選舉失利,目前民調支持率仍低于工黨。在中東歐國家,選民對右翼執政黨的不滿上升,給左翼政黨帶來機遇。左翼力量在黑山、斯洛文尼亞、阿爾巴尼亞、捷克等國取得政權。
與此同時,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影響持續上升,攪動一些國家傳統政黨政治。英國獨立黨、德國“反歐元黨”、法國“國民陣線”、意大利“五星運動”、捷克AN02011I黨等在各類選舉中表現“搶眼”,加劇了政治分化和社會保守傾向。日本、澳大利亞右翼政黨全面得勢,政策調整值得關注。日首相、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在經濟上力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緩慢增長;政治外交上堅持保守立場,在“修正”歷史認識、擺脫戰后體制束縛、強化軍力等方面謀求更大突破,迎合了趨于保守的選民支持。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以較大優勢獲勝,一舉終結日本“扭曲國會”局面,可能會在右傾化道路上越走越遠。澳大利亞聯盟黨抓住工黨執政績效不彰、內斗不止、選民厭倦等弱點,大打“求變”牌,強調只有“新政府”才能帶領澳走上“新道路”,在聯邦大選中以絕對優勢取勝,著手“修正”工黨政府的政策。
二、轉型國家西式變革“水土不服”,政局持續動蕩,轉型發展遭遇困境
一是西亞北非地區伊斯蘭政治力量上升勢頭受挫,政治版圖重塑。埃及伊斯蘭政黨上臺后加緊推行“宗教治國”理念,推進社會伊斯蘭化,打壓世俗力量,進一步激化了教俗矛盾;實施激進的“百日經濟改造”計劃,不僅未能扭轉經濟頹勢反而導致經濟惡化,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抗議活動。反對派乘機與軍方聯手廢黜執政僅一年的穆爾西政權。過渡政府拋出“政治路線圖計劃”,啟動政治過渡進程。埃政局逆轉產生強烈的外溢效應,重挫地區伊斯蘭政治力量的上升勢頭,引發地區主要力量新博弈。突尼斯兩位反對派領導人相繼遇害,演化成政治危機。世俗反對派受埃及“二次革命”鼓勵,加緊整合力量,成立“全國拯救陣線”,試圖推翻復興運動主導的制憲大會。目前,反對黨“突尼斯呼聲”的民意支持已超過執政的復興運動,突政治格局或將重洗。摩洛哥世俗政黨獨立黨退出執政聯盟,引發摩政府執政危機,迫使伊斯蘭政黨公發黨主導的政府改組。在新政府中公發黨的權重下降,力量遭到削弱。利比亞伊斯蘭政黨公正與建設黨炮制《政治隔離法》,從法律上將大批前政府官員排除在新政權外,引起世俗政黨強烈不滿,教俗爭斗烈度上升,干擾政治過渡進程。敘利亞政局復雜演進,內有巴沙爾政權與反對派尖銳對峙,外有美俄激烈較量。巴沙爾政權攜戰場優勢積極推動化武危機向于己有利的方向發展,處境暫有改觀,但內戰陰影不散。
二是部分獨聯體國家政局時有波動,政治轉型面臨較大不確定性。摩爾多瓦政局激烈動蕩,執政聯盟發生內訌,反對黨摩共趁勢介入,導致總理、議長易人,內閣重組。烏克蘭地區黨政府宣布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引起民眾不滿,導致烏發生2004年“顏色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集會活動及暴力沖突。反對派積極參與并逼迫總統辭職。烏政局深度發酵,考驗亞努科維奇及地區黨的控局能力。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執政當局為舒緩政權壓力,繼續推進適度民主。哈首次舉行地方行政長官選舉,擴大地方職權,同時,轉變態度,加大對非政府組織的扶持力度,積極引導非政府組織為政府所用。土總統履行《政黨法》要求,辭去執政黨民主黨主席職務,鼓勵多黨公平競爭,積極展示民主姿態和全民領袖形象。
三、新興市場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矛盾上升,執政黨壓力空前加大
受國際金融危機傳導輻射和自身經濟結構影響,一些新興國家的經濟形勢持續惡化,政府改革乏力,民眾生活受到沖擊,頻繁爆發街頭運動、社會騷亂甚至暴力沖突,執政黨的威信受損。巴西發生20年來最嚴重的抗議示威活動,由反對公車漲價等民生訴求迅速演變為反對執政當局的政治事件。勞工黨雖然迅速應對,推出一攬子改革措施,加大對民生的關注,但仍難以挽回民眾信心。羅塞芙總統的支持率由57%暴跌至30%,連任之路充滿變數。土耳其正發黨政府因強行推動加濟公園改造計劃,與民爭利,激起民憤,引發多年罕見的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和嚴重騷亂,反對黨推波助瀾,正發黨面臨強大壓力,不得不軟化態度呼應民意,逐漸平息事態。但土社會進一步分裂,世俗和保守勢力的對立加劇,未來正發黨的執政將受到更多制約。俄羅斯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上半年甚至出現“停滯”狀態,嚴重制約普京總統的“強國富民”戰略,民眾信心下降,抗議活動時有發生。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雖贏得地方選舉但優勢縮小。為打造更堅實的政治基礎和強有力的政權體系,普京將臨時性競選聯盟“全俄人民陣線”改組成常設性全俄組織“人民陣線—為了俄羅斯”,并出任最高領導人。南非政局總體穩定,經濟增長乏力加劇社會問題,失業率高企、勞資糾紛升溫、罷工不斷,民心向背和力量格局出現微妙變化,主要反對黨民盟影響上升,非國大的執政優勢未來將遭到蠶食。印度經濟出現滯脹跡象,國大黨政府應對無力,加之腐敗案件頻發,受到反對派和民間組織的猛烈攻擊,各項改革舉措難以推進,影響2014年的競選形勢。
四、發展中國家政黨形勢發展不平衡,區域化特點突出
部分亞洲國家政局波動較大,政黨格局面臨調整。蒙古、柬埔寨、馬來西亞、尼泊爾、巴基斯坦、不丹等國順利舉行大選,政治版圖明顯變化。蒙民主黨總統成功連任,并在歷史上首次獨攬總統、議會、政府、首都四大權力,執政地位穩固。這有利于該黨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政局穩定。柬人民黨、馬國陣雖贏得選舉,但執政優勢嚴重削弱,反對黨坐大并與之形成鼎立之勢,加速力量格局的多元化發展。巴基斯坦和不丹經歷政壇大換血,兩國反對派強勢回歸。尼泊爾傳統政治勢力大會黨和尼共(聯)在第二屆制憲會議選舉中重新崛起。聯合尼共(毛)無法接受由第一大黨滑落至第三的選舉結果,聲稱抵制計票并拒絕加入制憲會議,尼政治進程遭遇新困境。此外,一些國家亂象重現,政局變數增多。緬甸“鞏發黨”繼續推進全方位改革,但步子過快、一些動作過猛,引發許多問題,民族宗教沖突愈演愈烈。民盟著眼下屆大選力促修憲,加緊與政府角力,政局不確定性上升。泰國陷入民主怪圈,朝野圍繞修憲搶權、赦免他信展開新一輪激烈博弈,反對派再次掀起大規模抗議浪潮,迫使為泰黨政府解散國會,局勢如何發展尚待觀察。孟加拉國朝野就“何種政治力量”主導下屆大選等問題爭執不下,政局失控風險加大。菲律賓“政治分肥”丑聞持續發酵,政治社會穩定受到沖擊。
黑非洲國家政黨政治趨于平穩,但動蕩因素仍存。2013年,黑非洲有肯尼亞、馬里、津巴布韋、多哥、幾內亞、盧旺達、喀麥隆、吉布提、赤道幾內亞、馬達加斯加等十多個國家舉行大選,選情總體平穩有序,均未發生嚴重動蕩,“逢選必亂”現象繼續得到緩解。與此同時,一些國家朝野斗爭加劇,政局穩定性十分脆弱。津巴布韋、肯尼亞等國選前氣氛緊張,選后出現爭議。馬里叛亂被平息,聯盟黨候選人凱塔當選新總統,暫時穩住政局。中非發生軍事政變,博齊澤政權被推翻。馬達加斯加總統選舉由于候選人和選舉日期存在爭議陷入僵局。幾內亞立法選舉引發沖突并數度推遲。尼日利亞主要反對黨合并,與執政的人民黨形成對壘態勢,人民黨的壓力上升。
拉美左翼陣營地位穩固,一些國家執政黨的壓力大增。格林納達、巴巴多斯、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巴拉圭舉行大選,政權交接平穩。其中,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均以高票蟬聯執政,智利中左翼聯盟候選人巴切萊特在總統選舉中獲勝,進一步鞏固和壯大了左翼陣營。同時,拉美左翼也面臨著新形勢和困難。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病逝,委重新舉行總統大選,查韋斯欽定接班人馬杜羅僅以微弱優勢勝出,反對派實力上升,初具挑戰統社黨政權的能力。委政局變化對拉美左翼帶來一定負面影響,左翼不但失去了旗幟性人物,也可能因來自委的外援減少而面臨執政困難。但總體看,拉美左翼占優的格局在短期內不會改變。阿根廷執政聯盟勝利陣線強行通過“司法民主化”系列提案,并試圖通過新《媒體法》,加強對司法和媒體的控制,遭到反對派強力抵制,引發民意反彈,加之經濟社會問題突出,執政聯盟在國會中期選舉中雖保住第一大黨地位,但優勢大幅收窄,施政前景不明朗。
五、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主抓政權建設和經濟民生,進一步鞏固政權根基
2013年以來,朝、越、老、古四黨面臨的內外形勢更趨復雜,挑戰和壓力有所上升,著眼維穩防變,四黨更加重視黨的自身建設,強化黨的領導地位。朝鮮勞動黨加快向金正恩時代過渡,調整執政方式,逐步構筑“以黨治國”的執政體系。大幅進行人事調整,以反黨反國家等罪名清除黨內二號人物張成澤,完善權力架構。提出將“經濟建設與核武建設并進路線”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增強黨和國家抵御風險能力。越南共產黨進一步改進工作作風,開展自上而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嚴懲黨內消極腐敗現象,通過自我完善密切黨群關系。同時,考慮黨的未來發展,加強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位的規劃。在曾經引發激烈交鋒的修憲問題上,越共頂住內外壓力堅守政治底線,重申堅持黨的領導、土地全民所有、國有企業主導地位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遏制黨內自由主義傾向進一步發展,嚴防敵對勢力借機顛覆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老撾人革黨開展“堅強善于全面領導的黨組織”建設活動,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提高黨組織的作用,并通過頒發黨證,進一步加強對黨員干部的管理。古巴共產黨加快啟動新老交替進程,迪亞斯·卡內爾當選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以“二把手”身份正式亮相,成為勞爾的接班人選。
此外,四黨積極回應人民期待,下大力氣促經濟、謀發展。朝黨積極探索發展道路,更加重視經濟民生。強調“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是當前朝黨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加快推進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變革”,在維系計劃經濟框架的同時,引入一些市場經濟要素,繼續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逐步提高人民生活質量。越共針對經濟增長疲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繼續實施穩宏觀、控通脹、調結構等舉措,積極發展人力資源,加快推進公共投資、金融系統和國企重組,確保民生不受重大沖擊。老黨穩步落實七五規劃,努力平衡政府宏觀調控和遵循市場規律的關系,推動經濟平穩增長,注重將發展成果惠及人民,扶貧工作取得新進展。古共推出一系列新舉措,繼續推進經濟社會模式更新,放寬對國有經濟的管控和對個體經濟的限制,努力促進經濟發展,集中解決所面臨的復雜問題。
幾點看法
一、制度性缺陷影響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健康發展
西方國家持續多年的經濟困難已嚴重“毒化”了政治、社會氛圍。傳統政黨輪番上場尋找治愈危機的“藥方”,右翼政黨強調減支降赤、左翼政黨突出經濟轉型,甚至左、右翼政黨跨越界限調整政策,但成效寥寥,始終無法得到選民“喝彩”。相反,一些新興政黨和極端政黨則利用選舉制度的設計弊端,吸引渴望政壇新風的選民支持,在大選中脫穎而出。政治人物越走極端路線越容易成名的現象,助長政客強硬有余、妥協精神不足,導致一些國家黨爭升溫,干擾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普通民眾更多地顧及眼前利益,社會訴求日益多元,選票分散,客觀上使有利于國家長遠發展的重要改革難以形成社會共識,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脫困”進程。美國極化政治加劇和歐洲反體制、反權威、反主流的民粹主義進一步膨脹都說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存在問題。
二、政治生態深刻演變導致部分發展中國家政局持續震蕩
首先,新世紀以來,政治民主化加速了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對發展中國家產生深刻影響。許多發展中國家超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倉促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和政黨體制,黨派林立,爭斗不止。一些國家轉型后局勢更加惡化,民眾懷念以前,新舊政治力量在“變”與“亂”中激烈較量,政壇亂象不斷。其次,西方國家憑借優勢地位加緊向發展中國家推銷民主價值觀、進行勢力滲透,打壓異己政權,扶持政治代理人,攪亂一些國家政壇,加劇其政治對立和社會分裂。第三,民主政治動搖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威權基礎。民眾的民主意識覺醒,對執政當局不再盲從,不僅通過選票表達利益訴求,而且越來越頻繁地利用街頭運動進行抗爭,從而加重了國家的政局動蕩。埃及、泰國、尼泊爾、烏克蘭等國朝野理念和政策分歧難以調和,民眾立場尖銳對立,使國家陷入反復動蕩的惡性循環中。
三、經濟民生問題牽動各國政黨政治的發展變化
經濟和民生問題關系到一個國家執政黨的業績,關系到民心向背和政黨的命運。在國際金融危機持續發酵,世界經濟普遍低迷的大背景下,經濟和民生問題對各國政壇的影響更為突出。在歐債危機重災區的南歐和西歐地區,民眾雖不滿右翼執政黨實施緊縮政策對自身生活造成的沖擊,但仍從傳統理念出發不看好左翼政黨的經濟治理能力,加之法國社會黨政府執政表現差強人意,導致政治風向繼續偏向右翼。在中東歐地區,右翼政黨“鐵腕”執政,強力推行經濟緊縮政策,經濟形勢未見明顯好轉,民眾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換“莊”求變訴求成為社會主流,給左翼政黨上臺提供了機遇。在拉美地區,左翼執政黨始終高舉社會公正大旗,積極捍衛中下層民眾利益,雖然經濟形勢不佳,但仍能以民生為重,短期內政權無虞,繼續保持地區主導地位。
四、改革仍是一些國家執政黨擺脫困境的必經之道
面對復雜難解的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許多國家執政黨深刻反思、積極變革,力圖以變革促發展,以變革謀出路。西方國家執政黨為緩解壓力,抓緊調整發展戰略,平衡緊縮與發展的關系,加快財政金融領域改革,積極打造“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愛爾蘭、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少數國家執政黨開始超越既有思維,嘗試從制度角度反思政治和社會問題,立足根本尋找脫困之道,效果待評估,動向值得關注。發展中國家執政黨注重汲取西方國家陷入困境、西亞北非持續動蕩的深刻教訓,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總體看,一些國家處在內部政局動蕩、外部干擾不斷的環境中,改革之路并不平坦,甚至充滿風險。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
(責任編輯: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