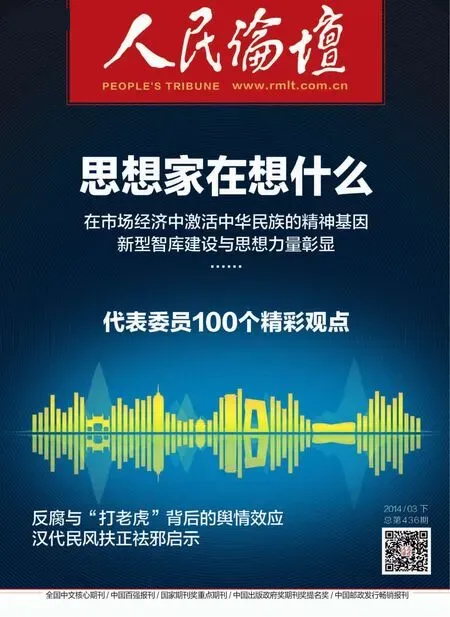思想創新機制中國迅速崛起的思想密鑰
思想創新機制中國迅速崛起的思想密鑰
胡鞍鋼
思想人物之胡鞍鋼
隨著全球化的持續深入和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年輕的中國智庫群體已經與全球智庫一道,進入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創新、大角逐、大發展時代
中國最大的創新:“中國之路”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大規模創新、集體創新、加速創新、不斷創新的時代。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為什么會迅速崛起?這正是源于中國的創新。那么,人們還會再進一步問道:中國最大的創新是什么呢?這就是開拓了“中國之路”。
所謂“中國之路”,就是鄧小平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會議上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之路”,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不照搬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模式,反對教條主義,也不盲目照搬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模式。盡管當時要求學習西方現代化,借鑒西方的經驗與教訓,但更要超越西方現代化,獨辟蹊徑,探索和開拓中國道路。鄧小平提出的是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也不同于其他所謂“非西方國家”(如印度)的現代化道路。從那時到現在,我們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創造出了大國迅速崛起的世界奇跡,也走出社會主義國家富強的“人間正道”。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將“中國之路”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推選語
他是中國國情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和學術帶頭人之一。對中國政治群體及其產生機制的獨創性研究,表明了他對中國國情理解的超前性。他站在國情研究的理論角度指出了中國領導人的政治堅定、團結統一、堅強有力、奮發有為是來自于實踐的鍛煉,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什么是中國改革的創新?筆者結合中國改革開放實踐,把創新定義為“創造新的社會價值的(各類)活動”。這個定義有三個要點:一是能夠創造新的價值,而不是已有的價值;二是所創造的價值主要是社會價值,具有正外部性;三是與創新有關的各種活動,以技術創新為例,不僅僅是技術創新本身,還包括與之相關的創新資金的融資和投入、新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有效保護、技術創新的示范應用和推廣等活動。這是一個廣義的創新定義,因為中國的改革是世界最大規模人口的創新實踐,并沒有先例;中國的改革也是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創造世界最大社會價值的創新活動,同樣沒有先例。
中國創新的主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新,特別中央領導集體的創新;二是中國人民的創新,包括工人、農民的創新,企業家、創業者的創新,科學家、工程師的創新,以及無數人才的創新。由此構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宏觀創新與微觀創新、國家創新與社會創新的有機結合,這就大大超越于僅有企業家創新和科學家創新的西方資本主義,從而顯示了社會主義的獨特優越性,使得中國不僅成功地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還成功地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
中國思想創新機制
中國最重要的創新機制在于思想創新、觀念創新。這包括幾方面的含義:一是“實事求是”,誠如毛澤東所言,“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按照中國國情辦事,避免脫離中國實際情況,超越發展階段。二是“解放思想”,誠如鄧小平所言,“就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觀念創新要提倡新思想、新主意、新觀念和新理念,并廣泛地擴散、傳播和應用,從而解放人們的思想,發揮人們的潛力,形成人們的創造力。三是“不斷創新、與時俱進”。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言,“過去有許多做法和經驗已經不適用了,要根據新的實踐要求,重新學習,不斷創新,與時俱進”。后來江澤民又將“不斷創新”進一步豐富為“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體制創新、科技創新”,胡錦濤同志又將“求真務實”寫入黨章,因此,“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
中國改革的過程還是一個“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循環往復過程。因制度創新、市場創新和技術創新變為觀念創新,又因觀念創新而變為制度創新、市場創新和技術創新。
這種“解放思想”的基本原理可以用“Ideas增長模型”解釋,其中Ideas包括觀念、主意、知識、經驗、智慧、思想及理論創新等多方面的內容。由于Ideas是一個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特性的投入,我們把它稱之為“無形要素投入”或“軟投入”,以區別于資本、勞動、資源等“有形要素投入”或“硬投入”。“軟投入”與增長成正比,即使在“硬投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軟投入”仍然可以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正如我們在比較改革前后的經濟增長率差異及其來源時發現,改革時期(1978年起,截至2010年)比計劃經濟時期(1952 —1978年)經濟增速高出了3-4個百分點,但是資本和勞動投入增長率并沒有多大變化,重要的原因是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率由負變正,達到3%-4%的水平,而這一轉變正是由Ideas所發揮的“邊際報酬遞增”重要作用所帶來的,也深刻反映了“解放思想”的促進作用和長期紅利。
在中國,任何Ideas創新都會具有巨國規模效應。這是因為中國總人口規模大,其崛起也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崛起過程。例如美國1870年開始崛起時只有4020萬人,到1913年時為9000多萬人;1950年日本開始崛起時為8380萬人,到1973年時為1億多人; 而1978年中國開始崛起時總人口為9.6億人。同一種創新對不同規模的人口會有極大的邊際性差異,也反映了中國Ideas的規模效益。正是由于這種世界上任何國家
感 言
作為中國學者,我們應該自覺地意識到,我們不是一般意義的南方國家學者,更不是霸權意義的北方國家學者,而是一個擁有十幾億人民、走上社會主義大道、正在迅速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那么,我們的學術追求是什么?我們的學術責任是什么?我們的學術舞臺是什么?
我們的追求是“與中國興盛同行,與中國開放相伴,與中國變革俱進”;我們的宗旨是“知識為民、知識報國”;我們的理念是“急國家之所急,想國家之所想,還要想國家之所未想”。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應當成為國家未來的“瞭望者”,國家戰略的“謀劃者”,國家智庫的“擔當者”,國家治理的“監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看得更準。中國既是我們學術創新、學術思想的來源,更是我們實現學術追求、承擔學術責任的大舞臺、大天地,我們才能大有作為,大有希望,大有貢獻。
作為一個大學的思想庫,國情研究院的專長就是國情研究與國策研究。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中,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榜上有名,我本人也有幸被評選為人民論壇“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之一。我們作為當代中國學研究者和公共決策智庫,始終堅持“知識為民、知識報國”的理念,要持續地不斷地提供有益于當代中國發展的重要理論、思想和創意——這都是典型的“國家公益性知識”,正所謂“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學術圖名,不以知識牟利。我們正處在當代中國大變革、大發展的歷史時代,又擁有最大的學術舞臺,要能夠及時反映當代中國學這一新學科的前沿課題、最新成果和重要進展并將其及時轉化為公共決策知識,引領社會發展潮流,為中國對人類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具有正能量。
(人民論壇記者艾蕓采訪整理)
外界評價
“沒有任何一個中國思想者像他這樣準確地預測了國家發展的方向和速度。當他確定的時候,他會很勇敢地提出來。他更關注總體上正確,不糾纏于細枝末節的正誤。他很可能是當代中國最全面也是最具務實主義的經濟學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董事長約翰·桑頓教授對胡鞍鋼教授的評價
“胡鞍鋼作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學術思想家之一,通過全面的研究工具和嚴謹的分析,理論化地探討了中國的過去與現在,并由此推測出這個偉大國家的未來。”——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拉瑞·柏克教授評價道(Backer,2013)都難以比擬的規模效益,一個好的思想誕生于中國、作用于中國,就如同精神“原子彈”,可以發揮無比的威力,并且還可以轉化為物質“原子彈”(指強大的物質生產力)。
如何創新正確的思想和觀念?它們不是憑空產生的,至少有以下三個重要來源:
老觀念。新觀念相對老觀念是“新的”,但卻又“孕育于”、“發生于”老觀念。它是對老觀念的歷史學習、歷史記憶、歷史繼承、歷史再創新。凡是經過歷史篩選而留存下來的好的觀念,都可能成為歷史財富。一個國家或社會歷史越長,歷史財富就越豐富,后人可利用的歷史資源就越多。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路線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對1956年黨的八大路線的歷史記憶和歷史繼承,同時也是對“以階級斗爭為綱”“文化大革命”時期深刻教訓的歷史反省和歷史學習。從這個意義上看,無論是前人的寶貴經驗還是深刻教訓,都可能成為后人的歷史資源,成為后人創新正確思想觀念的基礎,讓后人實現“古為今用”。
外部觀念。新的觀念,還可能來源于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對外部觀念的獲取、消化、吸收、應用和再創新。一個社會越開放,獲得外部觀念就越多,產生新的觀念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1978年和1979年鄧小平先后訪問8個國家,接見外賓幾十次,許多重要的改革設想都是在對外交流中形成的。可以說,鄧小平是新中國思想最為開放、最為活躍的領導人,同時也是觀念創新最多的領導人。這非常符合充分利用現代化“后來者”的“后發優勢”要求,即學習現代化“先行者”的成功經驗,同時避免其失敗教訓,從而幫助后來者實現“洋為中用”。
社會實踐。無論是老觀念、外部觀念都是他人的、間接的觀念,新觀念最重要的來源還是直接的、親力親為的社會實踐。誠如毛澤東所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中國的改革是十幾億人民參與的改革,也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社會實踐,這本身就為新觀念的創生提供了認識來源。誠如鄧小平所講,“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了歷史的繼承,才能有創新;有了開放的學習,才能有更多的創新;有了廣泛的社會實踐,才能有更大的創新。中國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創新觀念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接受社會實踐檢驗的過程,誠如毛澤東所言:“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這樣,人們可以不斷地因成功而創新觀念,又可以不斷地因失敗而修正觀念,從而實現認識與實踐的統一,即“知行合一”。
“兩個大腦”比“一個大腦”好
與物質“原子彈”相比,精神“原子彈”是典型的公共產品或公共知識,任何人消費都不需要付費,任何人消費都不影響其他人消費。盡管生產精神“原子彈”的成本遠遠低于物質“原子彈”,但其收益和外部性卻可能遠遠高于物質原子彈。精神“原子彈”,是思想家個人創新和思想庫集體創新的結果。
什么是思想家?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所謂“思想家”是指研究思想、思維和思考模式并且形成思想體系的人。古今中外富有智慧的人,都可能成為思想家。
什么是思想庫?它是一種特殊的生產知識和思想的組織。它是由專家組成的、多學科的、專門為決策者在處理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問題出謀劃策,提供最佳理論、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機構。思想庫進行“創造性思維”,其成果是思想,是知識,用以強化決策者的決策能力,從而對決策產生有利影響。
思想的主體不僅有思想家,還有思想庫;不僅有分散的思想者“個人”,更包括那些有組織的更具思想體系和思想傳承的“集體”或“政黨”。因為,“個人”的思想創新過程因生命周期結束而中止,“集體”或“政黨”的思想創新過程卻能夠綿延不斷、與時俱進、持續發展。在中國,中國共產黨不僅是最大的政黨組織,還是最大的思想家組織,有著成千上萬的政治家、理論家、思想家,我們稱之為“黨的集體智慧”,還能夠通過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的決策有效地集中全黨全國的思想智慧,引領和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避免了社會主流思想因人事調整、思想者死亡、制度變遷而中斷或終止的可能。
如果將中國比作“東方巨人”,那么主導國家重大決策的、高度智慧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就是這個巨人的“內腦”,為“內腦”決策出謀劃策、建言獻策、提供思想產品的各類思想庫,
思想小傳
著作頗豐的國情研究開拓者
胡鞍鋼是中國國情研究專家和學術帶頭人,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發展與發展政策。
胡鞍鋼教授著作頗豐。1988年,《生存與發展》問世。在這部成名作中,胡鞍鋼系統地把人口、資源、環境、糧食等重大問題納入中國中長期發展體系中加以研究。針對當時經濟發展“急于求成”的指導思想,他指出,中國國情中的限制因素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將是一個不斷量變的積累進而部分質變的長期歷史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只能是也必須是堅持持久戰。胡鞍鋼還富有遠見地提出,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選擇西方傳統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只能獨辟蹊徑,根據中國國情,尋求一種新的長期發展模式,探索一種中國獨特的生產力發展方式。
1993年6月中旬,胡鞍鋼與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摘要在新華社內部發表后,再一次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關注,為1994年之后的中國財政稅制體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參考依據, 報告內容所建議的7項建議有多項先后被采納和實施。該項研究奠定了胡鞍鋼在學術界,特別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里無可爭議的地位。
2003年4月13日,胡鞍鋼執筆撰寫了《全面積極應對全球SARS危機》一文,上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這是較早向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遞交的有關如何處理SARS危機的報告,提出9點建議,后來也陸續被采納。
2011—2012年,相繼完成了《人間正道》《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中國:創新綠色發展》等一系列研究與著述。2012年,圍繞著黨的十八大主題,胡鞍鋼和他的團隊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先后寫了17篇國情報告,許多重要成果已吸收并反映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則是這個巨人的“外腦”。決策過程本質上是對信息和知識吸收、利用和再加工的過程。信息和知識是“投入”,決策結果是“產出”,沒有投入就沒有產出。即使最聰明的決策者也始終面臨“投入”不足即信息不對稱性的問題,這包括信息數量不足、信息質量不高、信息溝通不暢。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中央、國務院作為“內腦”不斷推動重大決策走向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在決策過程自覺集中全黨(擁有8500萬名黨員)的政治智慧,主動問計于人民(擁有13億人)的社會需求,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對稱性,不僅防止了重大決策失誤,并及時糾正了較小的決策失誤,使各項公共政策決策更具有代表性、包容性、靈活性和適應性,使經濟保持持續增長、宏觀經濟基本穩定,而且成功應對了各種危機,在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等“世界大考”中交出了高質量答卷,還為中國長遠發展做出前瞻性的戰略部署。
(人民論壇編輯部整理)
近年來,黨中央積極鼓勵科學界(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等)、高水平大學等“要深入開展政策研究,積極發揮思想庫和智囊團作用,努力為黨和國家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作出積極貢獻”。這就需要“外腦”更加科學化、專業化、職業化地輔助“內腦”,為決策層提供公共決策所需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知識;還需要“內腦”更好地借力于“外腦”,主動問計于科學界、學術界及社會公眾。中國的發展已經證明:擁有“兩個大腦”比只擁有少數決策者這一個“大腦”要好,前者更加發達、更加智慧,也更能夠在國際競爭中“以弱勝強”、“由弱到強”、“強而愈強”,穩固地立于不敗之地。
結 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智庫建設新時代
隨著全球化的持續深入和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年輕的中國智庫群體已經與全球智庫一道,進入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創新、大角逐、大發展時代。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項目發布的《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統計,2013年,全球共有智庫6826個,其中中國智庫數量為426個,占世界總數比重的6.2%,排名第二,第一名美國的智庫數量為1828個,占世界總數的26.8%。根據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發布的《2013年中國智庫報告》,中國智庫分為黨政軍智庫,社會科學院智庫,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四類;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智庫發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影響力、多元化和國際化是中國智庫發展的趨勢。該報告指出,國際化合作進一步加強,這將為中國智庫發展增添全球意識,海外著名智庫也可能介入中國國內政策制定過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國際化和全球化特征和趨勢更加明顯。參與智庫國際化合作的另一面是應對國際挑戰,參與國際競爭。這就對包括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在內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提出了更高更長遠的要求。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責編/艾蕓 劉建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