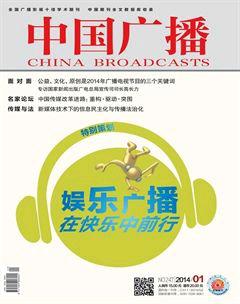英國監管報業是對過度“自由”的反彈
2014-01-20 18:57:59
中國廣播 2014年1期
關鍵詞:英國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10月底簽署一份“特許狀”,英國將據此成立官方報業監督機構,取代現有的自律體系,此外一個用于監察新監督機構、確保其獨立性的“認可委員會”將同時設立。英國報紙出現不少反對聲,有的宣稱英國持續了300年的新聞自由“走到盡頭”。
這一調整被認為是英國政府對不斷變化的媒體現實做出的反應。2011年《世界新聞報》發生的“竊聽門”,以及一些社交網站在倫敦騷亂中的表現,都刺激了英國社會圍繞“言論自由”及媒體道德出現前所未有的困惑的討論。
媒體在西方社會被普遍當成“第四權力”,在以往傳統社會里政府權力優勢明顯時,人們對“第四權力”給予了鼓勵為主、甚至放任的態度。然而進入互聯網時代,社會權力結構在嬗變,英國社會也面臨社會傳統力量與輿論力量之間的再平衡。
對媒體來說,永遠是言論自由越多越好,獲取信息的手段越不被限制越能搞到猛料。公眾通常會把這一切當成“大娛樂”,他們對媒體一旦朝著極端變化有可能傷害到社會及國家利益并不很敏感。英國大概意識到該國輿論界的一些動向對法律形成挑戰,“擦邊球”越來越多,因此成立官方監管機構雖然會引起一些抗議,但女王還是簽了“特許狀”。
媒體往往是一國各種力量中最活躍的,但怎樣讓媒體的正面作用發揮到最大,盡量避免輿論開放的負效果,只有相關國家自己才能有最真切的感受以及最準確的把握。這實際關系到一國重大利益,不可能讓外部力量越俎代庖。
英國“特許狀”提供了一個信息發達國家加強媒體監管的案例。以超越意識形態的實事求是態度觀察它,我們就有可能透過別人的問題,獲得對自己有價值的收獲。
(單仁平文,摘自2013年11月4日《環球時報》)
猜你喜歡
瘋狂英語·初中天地(2021年6期)2021-08-06 09:03:24
中國外匯(2019年21期)2019-05-21 03:04:06
少年漫畫(藝術創想)(2018年12期)2018-04-04 05:29:10
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25期)2016-07-01 09:54:15
環球時報(2012-03-24)2012-03-24 14:15:07
英語學習·新銳空間(2008年10期)2008-12-31 00:00:00
音像世界(2005年8期)2005-04-29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