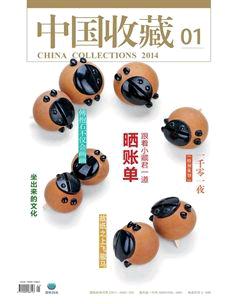漢字鼻祖
李玉


自從王懿榮于19世紀(jì)末在河南安陽小屯村發(fā)現(xiàn)最早的成批文字資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漢字已經(jīng)有3600年的歷史。
商代的文字已經(jīng)達(dá)到了很完善的程度,截至上世紀(jì)70年代,在殷墟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卜辭約有15萬片,可確認(rèn)的有5000多個(gè)單字,能夠認(rèn)識(shí)的單字有1732個(gè)。后人總結(jié)的“六書”,即象形、指事、會(huì)意、假借、形聲和轉(zhuǎn)注等六種構(gòu)成漢字的規(guī)則,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備。
由于甲骨文字已經(jīng)是相當(dāng)成熟的文字體系,中國(guó)的漢字似乎找到了祖源。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甲骨文字已經(jīng)是相當(dāng)成熟的文字體系,那么這種文字肯定有更早的雛形,這個(gè)文字的雛形是什么?又源自于哪里?
大體上可以說,漢字濫觴于新石器晚期至夏初,形成于殷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得到了繼承和發(fā)展。
數(shù)理模型分析認(rèn)為:在公元2世紀(jì),許慎編著中國(guó)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時(shí),漢字字?jǐn)?shù)為9353個(gè),這樣字匯增加2倍大約用了14個(gè)世紀(jì),增長(zhǎng)速度累加大約是每世紀(jì)10%;16個(gè)世紀(jì)后,康熙字典出版,包括42174個(gè)字目,以《說文解字》為基數(shù),字匯增長(zhǎng)4倍多,增長(zhǎng)速度累計(jì)每世紀(jì)是10%。如此倒推到公元前27世紀(jì)的新石器時(shí)代晚期,可以推測(cè)當(dāng)時(shí)的字匯數(shù)目是700個(gè)左右。這700個(gè)漢字,足以應(yīng)付日常工作。
漢字是華夏民族創(chuàng)造的,華夏民族正式形成應(yīng)該在新石器時(shí)代晚期和夏代初期。有關(guān)這一時(shí)期的歷史記載,特別是文字的起源,基本上是以后世的傳說和歷史神話為載體的,如黃帝時(shí)期造字的史官倉(cāng)頡造字時(shí),“天雨粟,鬼夜哭,龍亦潛”。雖然語焉不詳,但可窺見造字的時(shí)代是一定的,也就是新石器時(shí)代晚期。
自上世紀(jì)70年代至本世紀(jì)初,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對(duì)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進(jìn)行了多次發(fā)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根據(jù)發(fā)掘的遺跡的面積分布以及重要性來看,可以肯定這里應(yīng)該是最早華夏民族形成的地方,也可以稱為“最早的中國(guó)”。在陶寺遺址的扁壺上發(fā)現(xiàn)朱書“文”、“堯”二字,可以確認(rèn)為漢字的遠(yuǎn)祖。觀察這二字的字勢(shì)、筆畫,可以認(rèn)為是甲骨文的祖型。
華夏文明是中原當(dāng)?shù)匾约爸茉馕拿鞯暮铣审w,比如在陶寺遺址中,就可以觀察到來自東夷文明的鼉鼓、彩繪等,有著鮮明的東方痕跡。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設(shè)想——文字的產(chǎn)生是否也有可能有來自東方的因素呢?
回答是肯定的。
1960年春,在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公元前4100年至2500年)遭暴雨沖刷的河灘地發(fā)現(xiàn)三個(gè)釀酒器——大口尊。上部刻有圖像文字,即“錛”、“斧”和“日月山”。器物高52厘米,口徑30厘米。1969年這三件大口尊入選進(jìn)京及出國(guó)展覽,引起了巨大轟動(dòng)。古文字學(xué)界的專家紛紛予以關(guān)注,吉林大學(xué)教授、著名古文字學(xué)家于省吾先生在《文物》1973年3期上撰文《古文字若干問題》中,釋“日月山”為“旦”;故宮博物館原副院長(zhǎng)、著名古文字學(xué)家唐蘭先生1977年7月14日在《光明日?qǐng)?bào)》上發(fā)表《從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看我國(guó)最早文化年代》并詮釋“斧為鉞”、“錛為斤”;中國(guó)社科院考古專家、博導(dǎo)邵望平先生在《文物》1978年9期上發(fā)表題為《遠(yuǎn)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的文章。
到了1979年5月,山東省博物館和莒縣文物管理所,對(duì)以陵陽河遺址為中心的大朱家村、小朱家村等遺址聯(lián)合進(jìn)行發(fā)掘,成果豐富。陵陽河墓地的六號(hào)墓是大汶口文化時(shí)期最大最豐富的墓葬,隨葬品多達(dá)206件,大口尊和成套酒器一并出土。大口尊這樣的器物,諸城前寨,膠州的里岔、日照?qǐng)蛲醭呛桶不彰沙俏具t寺也有零星出土。
根據(jù)大口尊出土位置來看,可以得知墓主身份地位較高。由于在古代主管釀酒的是“酉長(zhǎng)”,亦即“酋長(zhǎng)”,而且根據(jù)詩(shī)經(jīng)來看,釀酒與祭祀是絕對(duì)不可分的。可見墓主即是部落領(lǐng)袖,也是祭祀長(zhǎng)。
一般認(rèn)為,文字是文明社會(huì)產(chǎn)生的標(biāo)志。文字作為高級(jí)精神的產(chǎn)物,其產(chǎn)生初期,只為少數(shù)高級(jí)貴族和祭司所掌握,是在情理之中的,也符合社會(huì)以及文字發(fā)展的規(guī)律。文字的發(fā)明和使用是人類告別野蠻社會(huì)、進(jìn)入文明時(shí)代的重要標(biāo)志。
古人由于認(rèn)識(shí)所限,對(duì)一系列自然現(xiàn)象無法解釋。出于對(duì)自然的敬畏,進(jìn)而轉(zhuǎn)向崇拜。為了與神靈進(jìn)行溝通,他們認(rèn)為在致幻狀態(tài)下是最為有效的(這一點(diǎn)可以在薩滿教中找到線索),而酒就是最好的致幻劑。于是喝酒宴饗,并在酒具上刻上表達(dá)自己心聲的圖像文字,以達(dá)上天,讓神靈和自己產(chǎn)生溝通,是再好不過的祈愿方法,文字因此產(chǎn)生了。這也是為什么最早文字總是在酒具上被發(fā)現(xiàn)的緣故。
陶文的刻劃是當(dāng)時(shí)人們?cè)诂F(xiàn)實(shí)生活中常年觀察事物,對(duì)自然景觀的描述,這種形象的符號(hào)本是“隨體詰詘”。就是線條隨自然客體外形的變化而變化,如模擬太陽外廓的“○”等,是“因形見義”的產(chǎn)物。陵陽河遺址等地出土的這類陶文,已經(jīng)有“形”可識(shí)、有“義”可辨。這就說明,文字在5000年之前,經(jīng)漫長(zhǎng)的發(fā)展時(shí)期臻于成熟。
從陶文刻在大口尊上的統(tǒng)一部位,字體工整嚴(yán)謹(jǐn)和當(dāng)時(shí)不同地點(diǎn)而發(fā)現(xiàn)相同的陶文來分析,它應(yīng)是繼先文字階段的結(jié)繩刻本、圖畫記事而進(jìn)入模擬物體形象概念的符號(hào),它是伴隨著實(shí)際生產(chǎn)應(yīng)用產(chǎn)生的,是向象形文字過渡的古文字,是文字祖型,也是中國(guó)最早的文字。